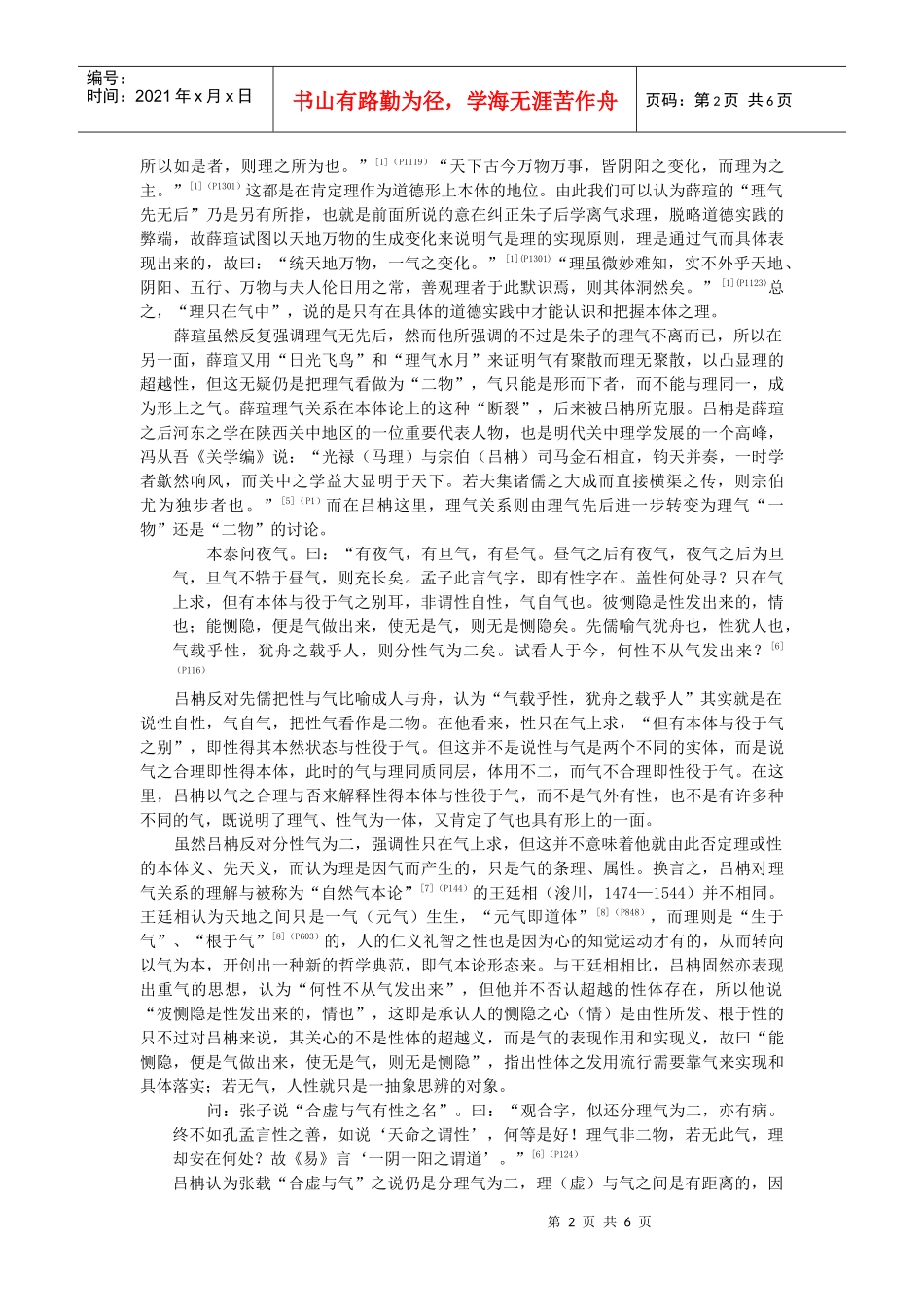第1页共6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页共6页从吕柟思想看关学对河东之学的发展1.王美凤2.米文科(1.西安文理学院历史系,陕西西安710065;2.宝鸡文理学院,陕西宝鸡721016)摘要:薛瑄的河东之学传承至吕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是对形上问题的兴趣减弱,理气关系由“理气无先后”转变为“理气一体”。二是关注的重心转入到日常事为上,工夫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体证形上本体。三是强调经学,主张明经修行,认为经要以实用、义理为主。吕柟思想上的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河东之学在明代中期的发展变化,同时亦构成了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关键词:吕柟;河东之学;关学;明代明代河东学派的创立始于明初的薛瑄(敬轩,1389-1464)。薛瑄在山西河津县讲学时,“四方学者云集”[1](P1655),范围遍及山西、陕西、河南等地,成为有明一代北方之学脉。薛瑄之学经过数传之后发展至陕西高陵的吕柟(泾野,1479—1542)①,遂在理论上出现了重要的转向。因此,比较吕柟与薛瑄思想上的异同,对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河东之学在明代中期的发展以及河东之学与关学的互动关系将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从“理气无先后”到“理气为一”理气“分合”是程朱理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朱子思想中,理气关系通常被表述为不离不杂,而具有二元论的倾向[2](P639-662)。朱子又认为理是一切具体事物及道德实践活动的超越根据,这样,“理先气后”就成了朱子本体论上的一个重要命题。然而朱子之后,其后学往往偏重对形上之理的讲求,而忽视理气关系中原本不离的一面,从而出现离气求理、不切实行的现象,如南宋末年的黄震(东发,1213—1280)就说:“文公既没,其学虽盛行,学者乃不于其切实而独于其高远。讲学舍《论语》不言,而必先大《易》;说《论语》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独讲一贯。”[3](卷82)这种现象随着程朱学的官方化而变得益发明显,学者日渐驰骛于词章训诂之中而忽视道德心性的修养,这显然构成了问题意识的起点。于是元明以来思想界逐渐开始对朱子理气观进行修正,而这种修正首先便体现在对气的重视上,强调“理在气中”,认为只有在具体的事为中才能把握理,薛瑄的“理气无先后”说即是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他说:窃谓理气不可分先后。盖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形虽未成,而所以为天地之气,则浑浑乎未尝间断止息,而理涵乎气之中也。及动而生阳,而天始分,则理乘是气之动而具于天之中;静而生阴,而地始分,则理乘是气之静而具于地之中。分天分地,而理无不在;一动一静,而理无不存,以至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理气二者盖无须臾之相离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后哉?[1](P1074)朱子的“理先气后”本不是讲宇宙生成论,认为理气在时间上有一个先后的顺序,而是一形上学的概念,意在凸显理的超越性和价值性,故朱子一面强调理气不离,一面又说“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4](P3)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4](P1)。而在上述引文中,薛瑄却从天地万物的生成过程来说明理气无先后、“理在气中”,这与朱子的思想看起来似乎有所间隔。但实际上,薛瑄并非不理解朱子挺立形上之理的用心而有意进行曲解,所以他又说:“理、气虽不可分先后,然气之①吕柟师从渭南的薛敬之(思庵,1435—1508),而薛敬之则学于秦州的周蕙(小泉),周蕙问学于兰州的段坚(容思,1419—1484)。段坚虽然不是薛瑄及门弟子,但他与薛瑄的两位门人凤翔的张杰(默斋,1421—1472)和河南的阎禹锡(字子與,1426—1476)相互往来论学,属于私淑而有得者。第2页共6页第1页共6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2页共6页所以如是者,则理之所为也。”[1](P1119)“天下古今万物万事,皆阴阳之变化,而理为之主。”[1](P1301)这都是在肯定理作为道德形上本体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薛瑄的“理气先无后”乃是另有所指,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意在纠正朱子后学离气求理,脱略道德实践的弊端,故薛瑄试图以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来说明气是理的实现原则,理是通过气而具体表现出来的,故曰:“统天地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