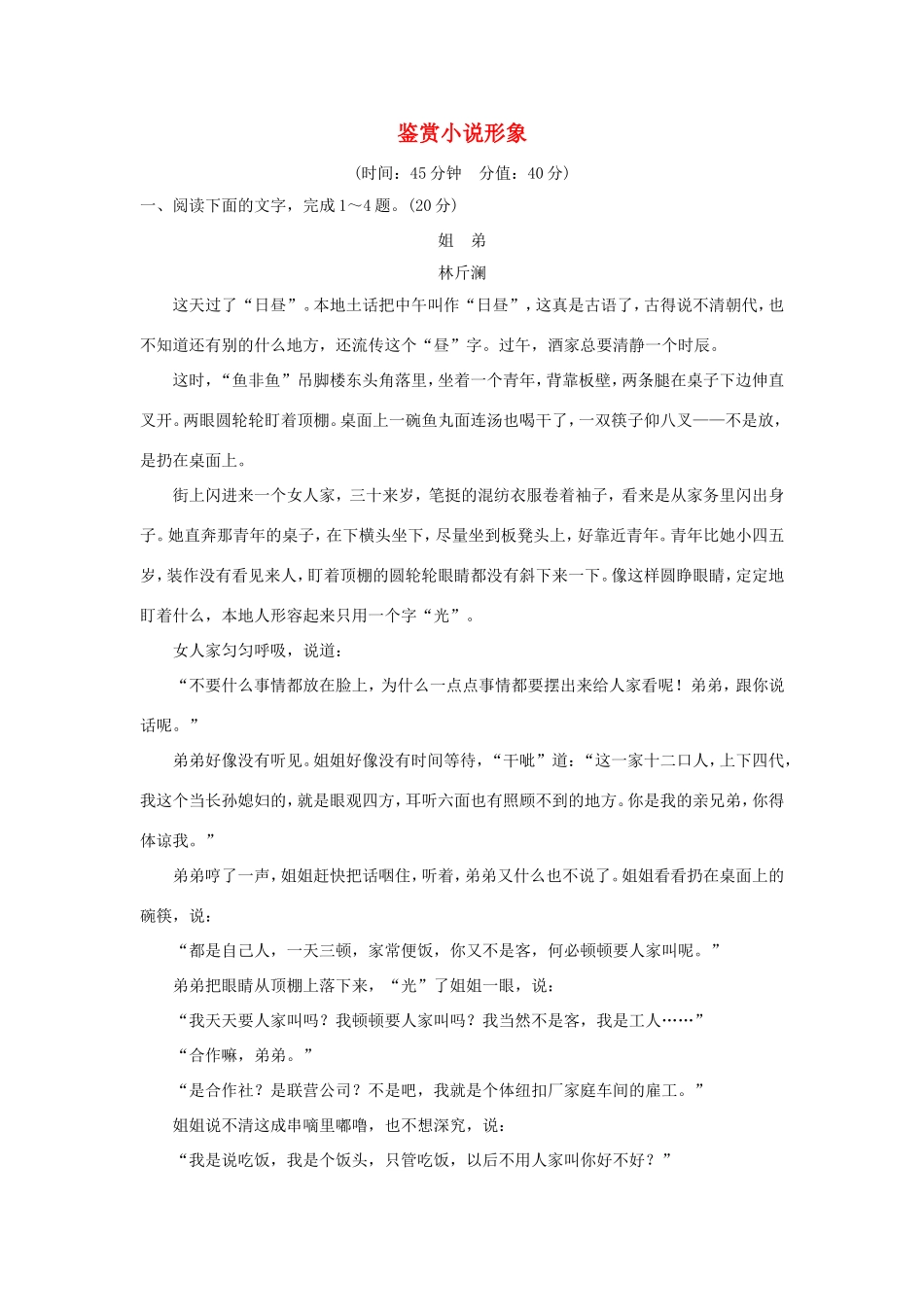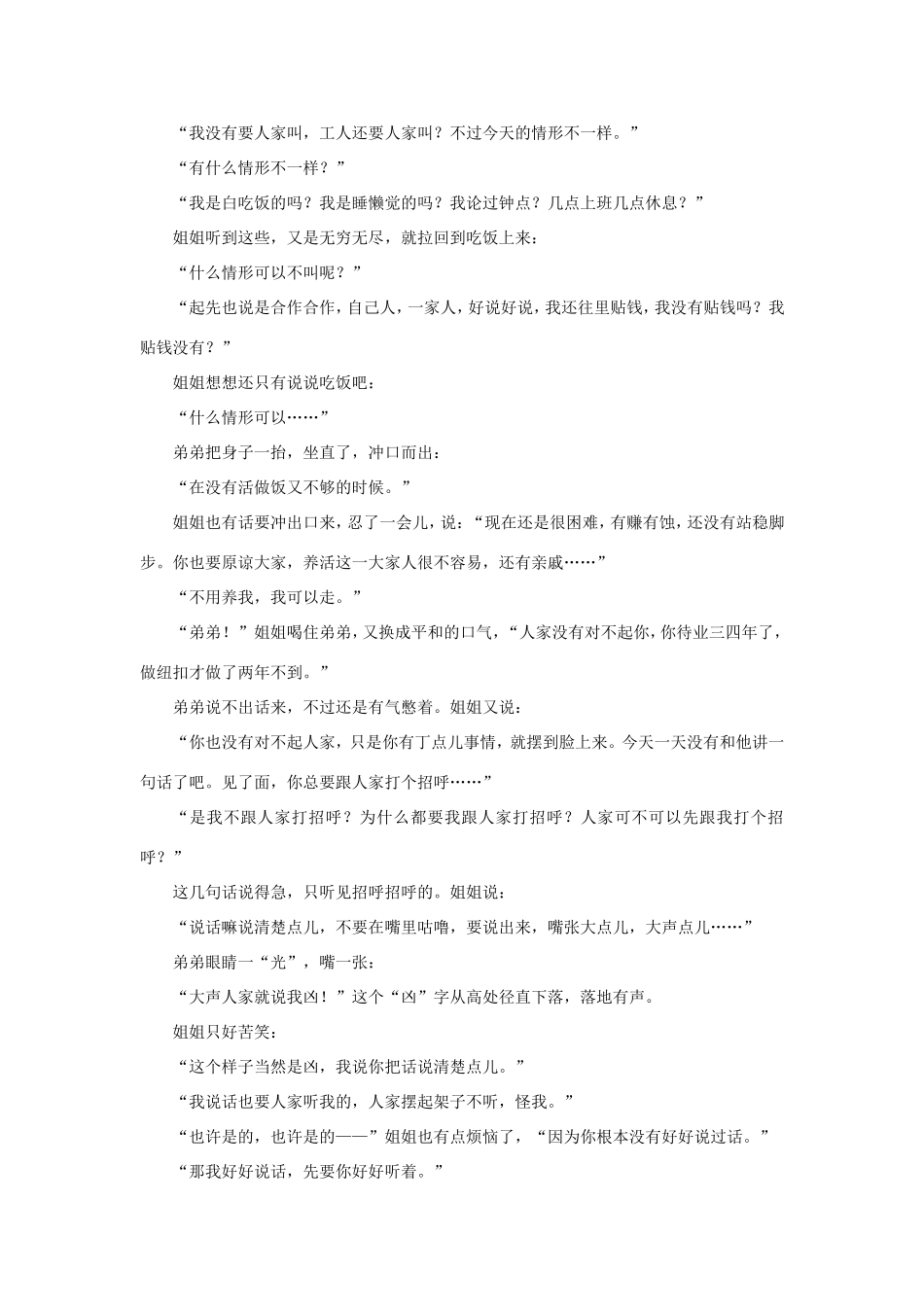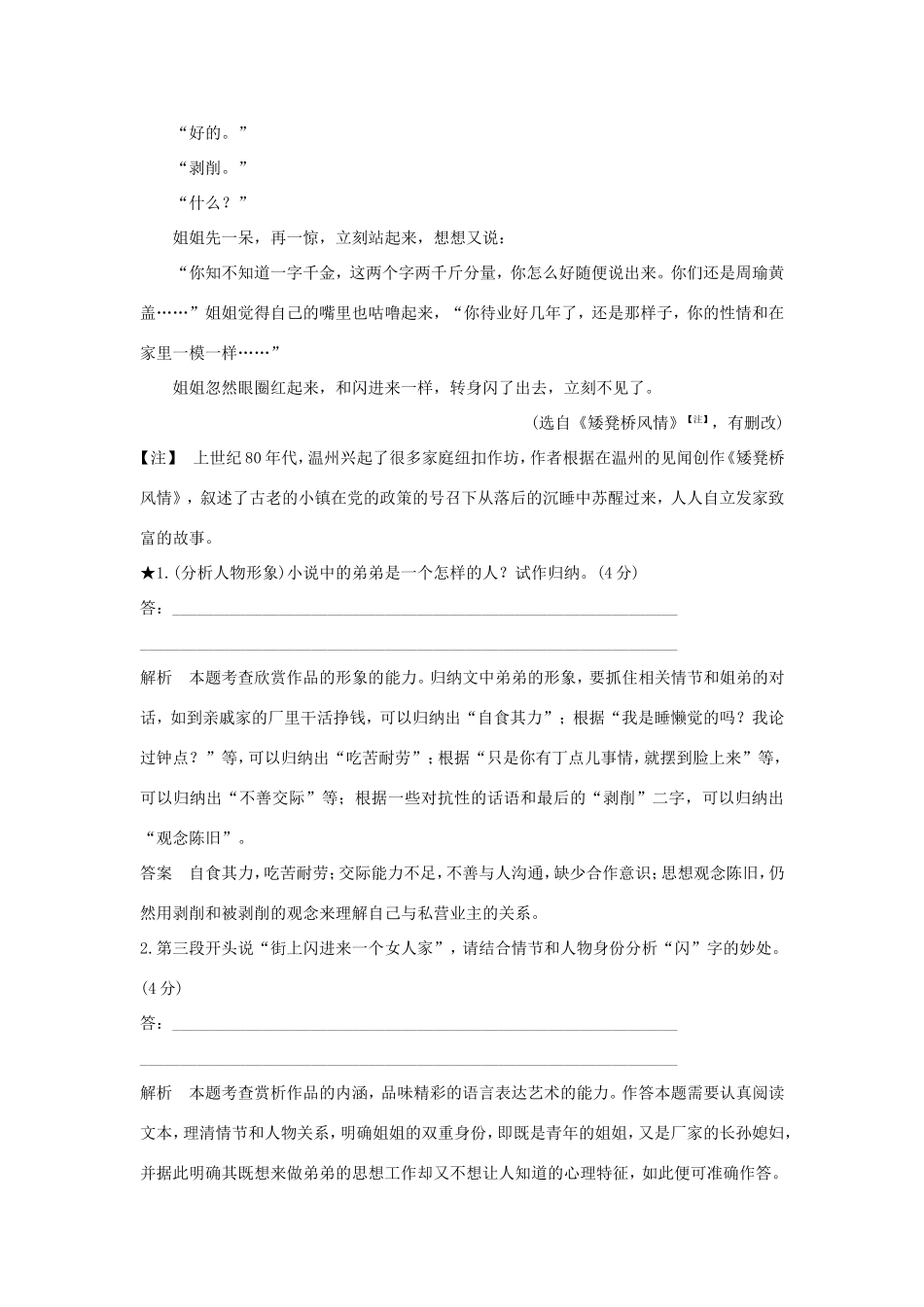鉴赏小说形象(时间:45分钟分值:40分)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0分)姐弟林斤澜这天过了“日昼”。本地土话把中午叫作“日昼”,这真是古语了,古得说不清朝代,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还流传这个“昼”字。过午,酒家总要清静一个时辰。这时,“鱼非鱼”吊脚楼东头角落里,坐着一个青年,背靠板壁,两条腿在桌子下边伸直叉开。两眼圆轮轮盯着顶棚。桌面上一碗鱼丸面连汤也喝干了,一双筷子仰八叉——不是放,是扔在桌面上。街上闪进来一个女人家,三十来岁,笔挺的混纺衣服卷着袖子,看来是从家务里闪出身子。她直奔那青年的桌子,在下横头坐下,尽量坐到板凳头上,好靠近青年。青年比她小四五岁,装作没有看见来人,盯着顶棚的圆轮轮眼睛都没有斜下来一下。像这样圆睁眼睛,定定地盯着什么,本地人形容起来只用一个字“光”。女人家匀匀呼吸,说道:“不要什么事情都放在脸上,为什么一点点事情都要摆出来给人家看呢!弟弟,跟你说话呢。”弟弟好像没有听见。姐姐好像没有时间等待,“干呲”道:“这一家十二口人,上下四代,我这个当长孙媳妇的,就是眼观四方,耳听六面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你是我的亲兄弟,你得体谅我。”弟弟哼了一声,姐姐赶快把话咽住,听着,弟弟又什么也不说了。姐姐看看扔在桌面上的碗筷,说:“都是自己人,一天三顿,家常便饭,你又不是客,何必顿顿要人家叫呢。”弟弟把眼睛从顶棚上落下来,“光”了姐姐一眼,说:“我天天要人家叫吗?我顿顿要人家叫吗?我当然不是客,我是工人……”“合作嘛,弟弟。”“是合作社?是联营公司?不是吧,我就是个体纽扣厂家庭车间的雇工。”姐姐说不清这成串嘀里嘟噜,也不想深究,说:“我是说吃饭,我是个饭头,只管吃饭,以后不用人家叫你好不好?”“我没有要人家叫,工人还要人家叫?不过今天的情形不一样。”“有什么情形不一样?”“我是白吃饭的吗?我是睡懒觉的吗?我论过钟点?几点上班几点休息?”姐姐听到这些,又是无穷无尽,就拉回到吃饭上来:“什么情形可以不叫呢?”“起先也说是合作合作,自己人,一家人,好说好说,我还往里贴钱,我没有贴钱吗?我贴钱没有?”姐姐想想还只有说说吃饭吧:“什么情形可以……”弟弟把身子一抬,坐直了,冲口而出:“在没有活做饭又不够的时候。”姐姐也有话要冲出口来,忍了一会儿,说:“现在还是很困难,有赚有蚀,还没有站稳脚步。你也要原谅大家,养活这一大家人很不容易,还有亲戚……”“不用养我,我可以走。”“弟弟!”姐姐喝住弟弟,又换成平和的口气,“人家没有对不起你,你待业三四年了,做纽扣才做了两年不到。”弟弟说不出话来,不过还是有气憋着。姐姐又说:“你也没有对不起人家,只是你有丁点儿事情,就摆到脸上来。今天一天没有和他讲一句话了吧。见了面,你总要跟人家打个招呼……”“是我不跟人家打招呼?为什么都要我跟人家打招呼?人家可不可以先跟我打个招呼?”这几句话说得急,只听见招呼招呼的。姐姐说:“说话嘛说清楚点儿,不要在嘴里咕噜,要说出来,嘴张大点儿,大声点儿……”弟弟眼睛一“光”,嘴一张:“大声人家就说我凶!”这个“凶”字从高处径直下落,落地有声。姐姐只好苦笑:“这个样子当然是凶,我说你把话说清楚点儿。”“我说话也要人家听我的,人家摆起架子不听,怪我。”“也许是的,也许是的——”姐姐也有点烦恼了,“因为你根本没有好好说过话。”“那我好好说话,先要你好好听着。”“好的。”“剥削。”“什么?”姐姐先一呆,再一惊,立刻站起来,想想又说:“你知不知道一字千金,这两个字两千斤分量,你怎么好随便说出来。你们还是周瑜黄盖……”姐姐觉得自己的嘴里也咕噜起来,“你待业好几年了,还是那样子,你的性情和在家里一模一样……”姐姐忽然眼圈红起来,和闪进来一样,转身闪了出去,立刻不见了。(选自《矮凳桥风情》【注】,有删改)【注】上世纪80年代,温州兴起了很多家庭纽扣作坊,作者根据在温州的见闻创作《矮凳桥风情》,叙述了古老的小镇在党的政策的号召下从落后的沉睡中苏醒过来,人人自立发家致富的故事。★1.(分析人物形象)小说中的弟弟是一个怎样的人?试作归纳。(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