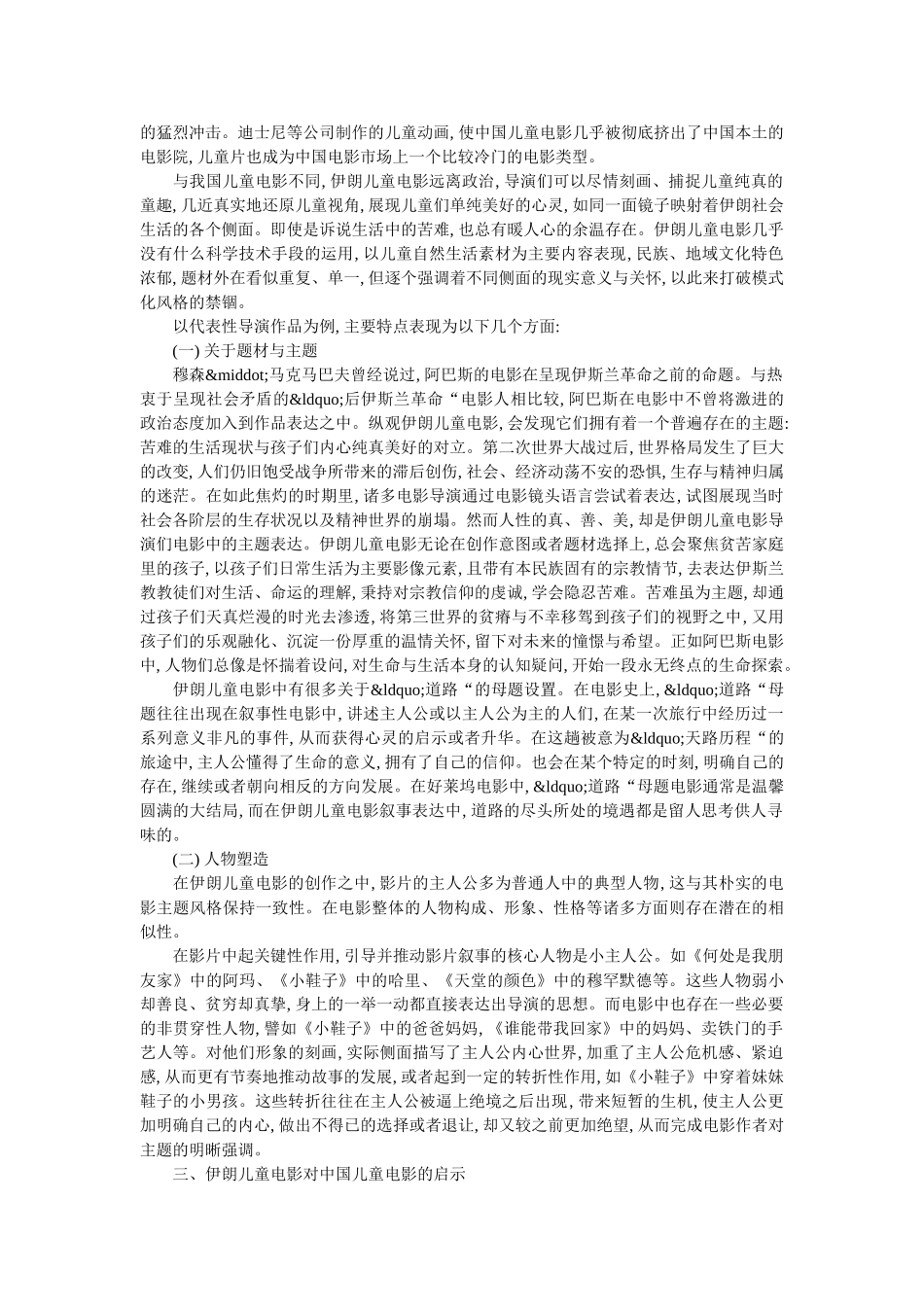伊朗儿童电影的特征及其借鉴意义伊朗儿童电影的特征及其借鉴意义本文关键词:伊朗,借鉴,特征,意义,儿童伊朗儿童电影的特征及其借鉴意义本文简介:摘要:近几十年里,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并不显着,且普遍存在题材单一、人物平面化、情节设置过于简单等问题。而在浓郁的民族、宗教、地域特点的渲染之下,伊朗涌现出大量优秀儿童电影,细微的刻画捕捉,触动观众内心深处最为质朴的情感,无疑成为了伊朗电影区别于他国电影的独特特征。本文借由学习研究伊朗儿童电影,来分析伊朗儿童电影的特征及其借鉴意义本文内容:摘要:近几十年里,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并不显着,且普遍存在题材单一、人物平面化、情节设置过于简单等问题。而在浓郁的民族、宗教、地域特点的渲染之下,伊朗涌现出大量优秀儿童电影,细微的刻画捕捉,触动观众内心深处最为质朴的情感,无疑成为了伊朗电影区别于他国电影的独特特征。本文借由学习研究伊朗儿童电影,来分析中国儿童电影发展现状的缺陷与不足,从而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关键词:伊朗;儿童电影;中国儿童电影;一、伊朗儿童电影的崛起《TheLorGirl》是伊朗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片。二战后,伊朗电影始终死气沉沉。在整个伊朗电影的发展中,宗教与政府始终扮演着严肃的角色,始终受到宗教人士的排斥与诋毁。伊斯兰宗教人士认为,电影亵渎了他们的神灵,是西方国家无神论的象征,颠覆了他们信奉的价值观。而伊朗的电影工业又必须完全依赖政府,因此被迫接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审查。在语言因素的弊端下,题材选择也同样狭窄受限,加之缺少可供推向国门之外的明星或者电影类型,伊朗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之中,发展极其缓慢。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电影正处于“新浪潮“的爆发之中,与此同时,伊朗一群极具开拓精神的艺术家们也开展了一场新浪潮运动,其中以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系的达鲁希·梅赫朱为代表。他们在运用电影语言制作高质量电影的同时,已经具有强烈的本土电影意识,开拓了伊朗乡土写实电影的先河。1969年梅赫朱的第二部影片《奶牛》便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由此获得世界影坛的关注。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79年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之后。由于当时严苛的电影审查制度的约束,譬如禁止暴力场面,不许涉及政治、宗教、性,女演员不得暴露皮肤等,电影制作方向牢牢控制在国家政府手中。以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为代表的一批导演们,在政府组建的“青少年智育协会“电影部进行电影的创作工作。他们在继承前辈们写实的电影风格特点之外,疏离了政治、宗教或者道德戒律的诠释,找寻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将镜头对准儿童。1987年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执导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在戛纳获奖引起轰动,因此伊朗电影最初给世界观众留下的印象便是伊朗的儿童电影。但众所周知,伊朗儿童电影虽以儿童为主人公,表达的内容意义却远在儿童电影范畴之上,涵盖着导演本身对生活、世界的思考。于是接连出现了如《小鞋子》《水缸》《谁能带我回家》《白气球》《天堂的颜色》《风中飘絮》《让风带着我飞》等众多优秀的儿童电影作品。导演们在本国宗教的束缚下,以儿童电影为载体,向世界观众展示了神秘古国伊朗的传统与风土人情,并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同时也填补了世界儿童电影单调的空白。二、伊朗儿童电影的特征我国儿童电影发展最初承载着寓教于乐的功能,整体选材上也偏重于较为宏大的叙事背景设置。二十世纪中期出现了如《小兵张嘎》《鸡毛信》《闪闪的红星》等具有时代标志性的国产儿童电影。但影片多为红色成长主题,叙事模式单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模式化创作有所改变,在题材选择与创作方法上加以创新,出现了《烛光里的微笑》《霹雳贝贝》《一个都不能少》等较为贴合儿童生活实际的影片。但它们很快销声匿迹,并受到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迪士尼等公司制作的儿童动画,使中国儿童电影几乎被彻底挤出了中国本土的电影院,儿童片也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上一个比较冷门的电影类型。与我国儿童电影不同,伊朗儿童电影远离政治,导演们可以尽情刻画、捕捉儿童纯真的童趣,几近真实地还原儿童视角,展现儿童们单纯美好的心灵,如同一面镜子映射着伊朗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即使是诉说生活中的苦难,也总有暖人心的余温存在。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