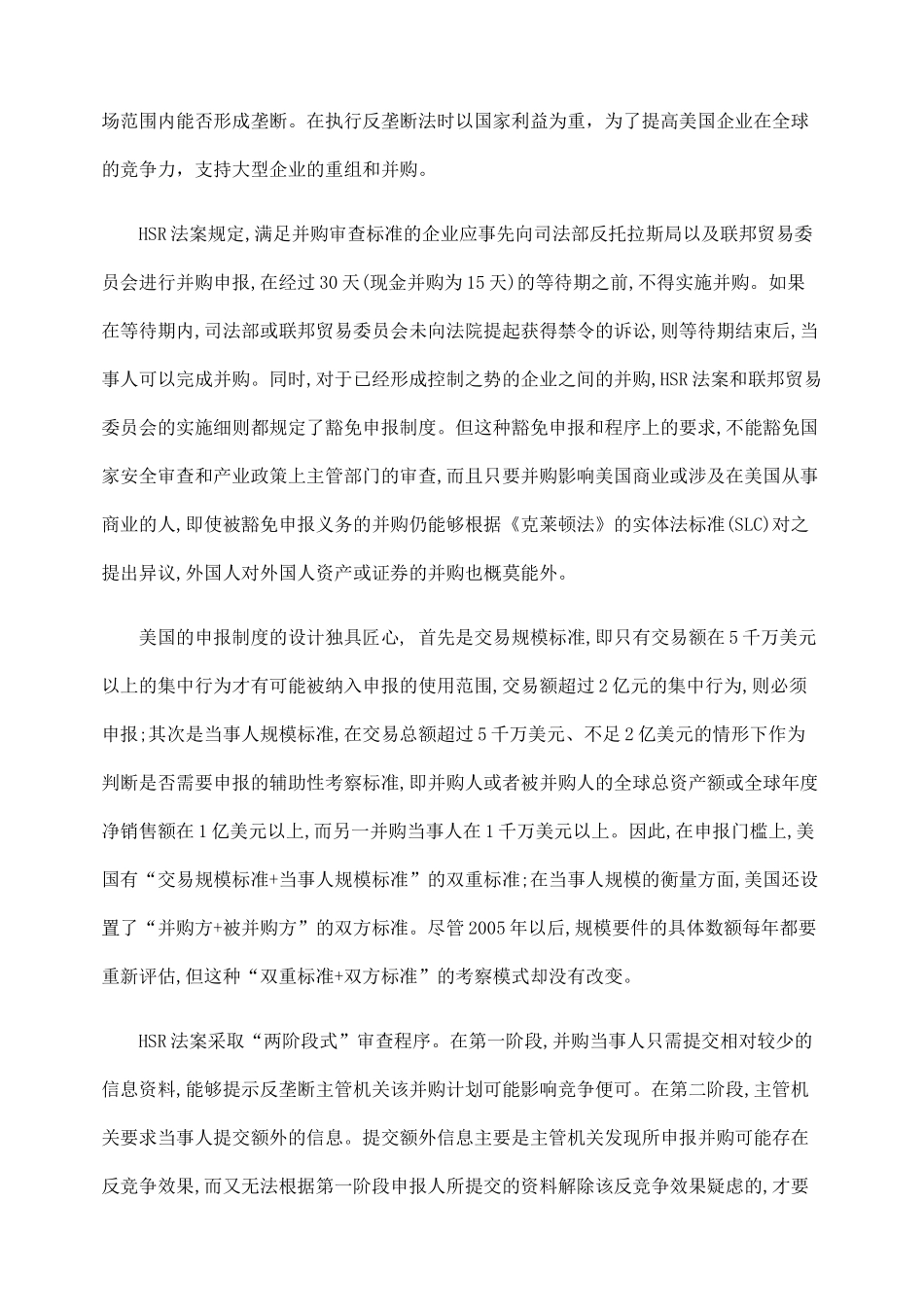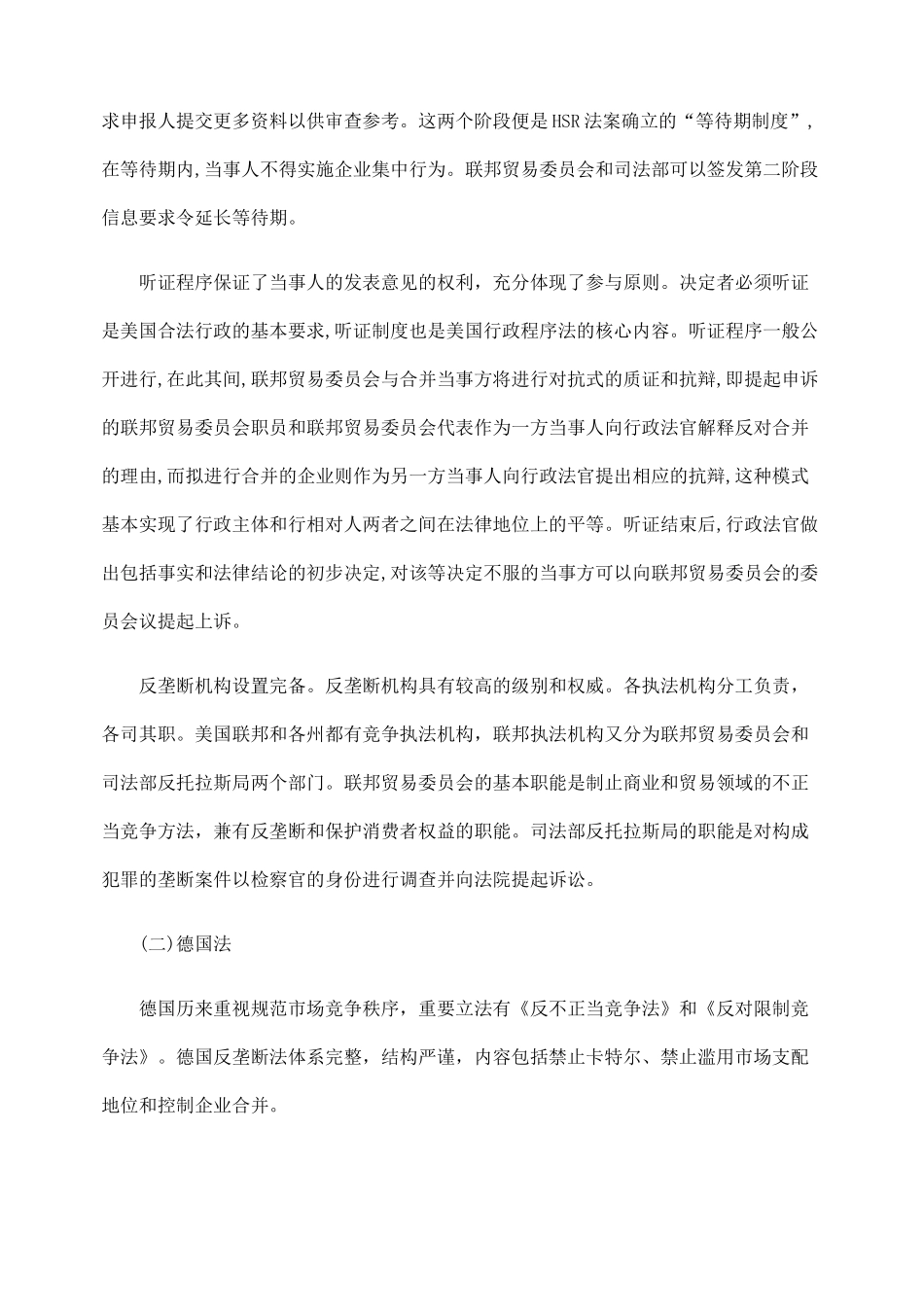我国外资并购反垄断法律问题研究一、国外关于外资并购反垄断的法律规定(一)美国法美国是最早对企业并购实施法律监管的国家。美国企业并购反垄断审查的法律依据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联邦立法,包括《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塞勒—克福弗反对并购法》《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垄断修订法》(Hart-Scott-RodinoAntitrustImprovementsActof1976,以下简称HSR法案)《反垄断程序的修订法令》,二是法院判例法,三是司法部颁布的《企业并购指南》。美国外资并购反垄断审查程序上颇有特色,比如说建立了事前申报制和申报豁免,两阶段审查制度,听证程序和反垄断机构设置。美国采取事前申报制度,即达到反垄断法规定规模的经营者在进行合并之前需向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申报,在获得批准后,即可进行合并。美国有关经营者集中申报豁免的法律规定非常复杂,《克莱顿法》第七条规定了有关申报豁免,由于美国是英美法系国家,对法条的理解还要结合案例来分析,例如著名的波音与麦道的合并案。合并后的波音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商,而且是美国市场唯一的供应商,占国内市场的份额几乎达百分之百。但是,美国政府不仅没有阻止波音兼并麦道,而且还促成了这一兼并活动。因为合并有利于维护美国的航空工业大国地位,而且波音公司不可能在开放的美国和世界市场上形成绝对垄断地位。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在监管企业购并时,不仅仅根据国内市场占有率来判断是否垄断,还要考虑在整个市场范围内能否形成垄断。在执行反垄断法时以国家利益为重,为了提高美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支持大型企业的重组和并购。HSR法案规定,满足并购审查标准的企业应事先向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以及联邦贸易委员会进行并购申报,在经过30天(现金并购为15天)的等待期之前,不得实施并购。如果在等待期内,司法部或联邦贸易委员会未向法院提起获得禁令的诉讼,则等待期结束后,当事人可以完成并购。同时,对于已经形成控制之势的企业之间的并购,HSR法案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实施细则都规定了豁免申报制度。但这种豁免申报和程序上的要求,不能豁免国家安全审查和产业政策上主管部门的审查,而且只要并购影响美国商业或涉及在美国从事商业的人,即使被豁免申报义务的并购仍能够根据《克莱顿法》的实体法标准(SLC)对之提出异议,外国人对外国人资产或证券的并购也概莫能外。美国的申报制度的设计独具匠心,首先是交易规模标准,即只有交易额在5千万美元以上的集中行为才有可能被纳入申报的使用范围,交易额超过2亿元的集中行为,则必须申报;其次是当事人规模标准,在交易总额超过5千万美元、不足2亿美元的情形下作为判断是否需要申报的辅助性考察标准,即并购人或者被并购人的全球总资产额或全球年度净销售额在1亿美元以上,而另一并购当事人在1千万美元以上。因此,在申报门槛上,美国有“交易规模标准+当事人规模标准”的双重标准;在当事人规模的衡量方面,美国还设置了“并购方+被并购方”的双方标准。尽管2005年以后,规模要件的具体数额每年都要重新评估,但这种“双重标准+双方标准”的考察模式却没有改变。HSR法案采取“两阶段式”审查程序。在第一阶段,并购当事人只需提交相对较少的信息资料,能够提示反垄断主管机关该并购计划可能影响竞争便可。在第二阶段,主管机关要求当事人提交额外的信息。提交额外信息主要是主管机关发现所申报并购可能存在反竞争效果,而又无法根据第一阶段申报人所提交的资料解除该反竞争效果疑虑的,才要求申报人提交更多资料以供审查参考。这两个阶段便是HSR法案确立的“等待期制度”,在等待期内,当事人不得实施企业集中行为。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可以签发第二阶段信息要求令延长等待期。听证程序保证了当事人的发表意见的权利,充分体现了参与原则。决定者必须听证是美国合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听证制度也是美国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听证程序一般公开进行,在此其间,联邦贸易委员会与合并当事方将进行对抗式的质证和抗辩,即提起申诉的联邦贸易委员会职员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代表作为一方当事人向行政法官解释反对合并的理由,而拟进行合并的企业则作为另一方当事人向行政法官提出相应的抗辩,这种模式基本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