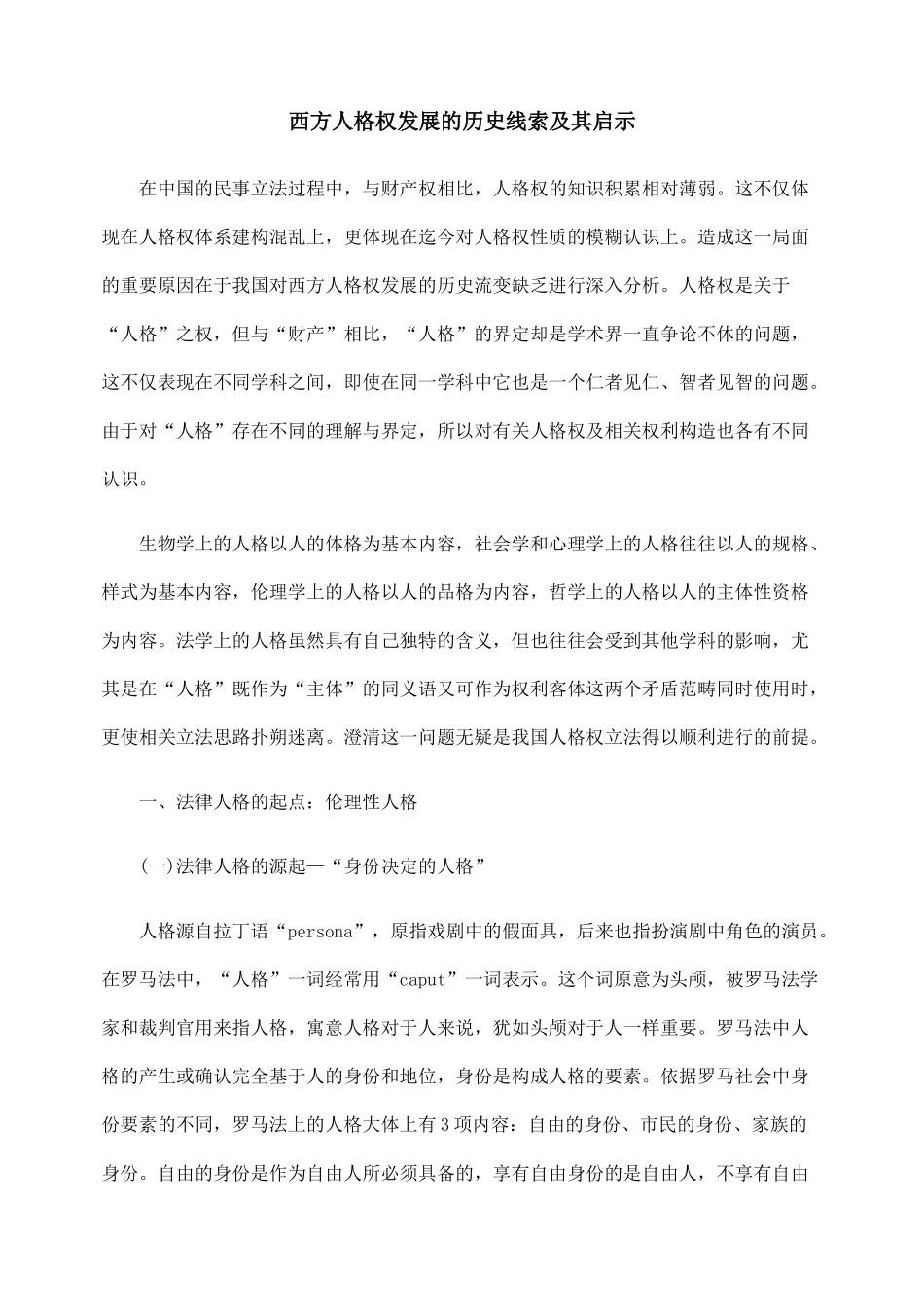西方人格权发展的历史线索及其启示在中国的民事立法过程中,与财产权相比,人格权的知识积累相对薄弱。这不仅体现在人格权体系建构混乱上,更体现在迄今对人格权性质的模糊认识上。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对西方人格权发展的历史流变缺乏进行深入分析。人格权是关于“人格”之权,但与“财产”相比,“人格”的界定却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不同学科之间,即使在同一学科中它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由于对“人格”存在不同的理解与界定,所以对有关人格权及相关权利构造也各有不同认识。生物学上的人格以人的体格为基本内容,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人格往往以人的规格、样式为基本内容,伦理学上的人格以人的品格为内容,哲学上的人格以人的主体性资格为内容。法学上的人格虽然具有自己独特的含义,但也往往会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尤其是在“人格”既作为“主体”的同义语又可作为权利客体这两个矛盾范畴同时使用时,更使相关立法思路扑朔迷离。澄清这一问题无疑是我国人格权立法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一、法律人格的起点:伦理性人格(一)法律人格的源起—“身份决定的人格”人格源自拉丁语“persona”,原指戏剧中的假面具,后来也指扮演剧中角色的演员。在罗马法中,“人格”一词经常用“caput”一词表示。这个词原意为头颅,被罗马法学家和裁判官用来指人格,寓意人格对于人来说,犹如头颅对于人一样重要。罗马法中人格的产生或确认完全基于人的身份和地位,身份是构成人格的要素。依据罗马社会中身份要素的不同,罗马法上的人格大体上有3项内容:自由的身份、市民的身份、家族的身份。自由的身份是作为自由人所必须具备的,享有自由身份的是自由人,不享有自由身份的就是奴隶,自由人分为生来自由人和解放自由人,前者享有某些政治国家赋予的特权,具有公法性;市民的身份是公私混合的,专属于罗马市民,包括投票权、担任官职权、申诉权、婚姻权和交易权、遗嘱能力、诉讼权、氏族成员权、宗教权等;家族的身份是私法性的,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只有这三种身份同时具备,方能使一个自然人取得完全的法律人格;只具有其中一种或两种身份的人就是不具有充分人格的人;三种身份均不享有者则无人格可言,故也不能成为民事权利的主体。若其中某项权利丧失或变化,相应地会有人格减等。罗马法中的身份都是纵向性的:自由人、市民的身份表现的是国家与主体间的宏观纵向关系,国家通过这两种身份赋予承受者特权;家族的身份表现的是微观纵向关系,因为罗马的家庭相当于一个主权单位,家父对其属员享有生杀予夺权。总之,罗马法将人格完全视为一种产生于身份而又反过来体现身份、延续身份的制度,是公私法兼容、人格与身份并列、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合为一体的概念,带有强烈的身份性与等级性,这使得近代私法意义上的人格无法在人法上得以确立。至日耳曼封建社会,人格制度仍具有鲜明的等级森严的身份制特征。人依其性别、身份、所属职业团体和宗教的差异而不同,分为4个等级:普通自由人、少数贵族阶级、半自由人及奴隶。在家庭内部,各成员间地位亦非平等关系。虽然当时影响广泛的基督教确立了人类尊严的思想,教会法在对罗马法的解释中也注入了更多平等和个人自由意志的理念,但对人类的尊重仅仅限于宗教和道德意义,封建身份制决定了世俗和法律上的平等人格无法形成。故总体而言,18世纪以前的社会是一个身份制社会,人们在私法上的地位主要由其在社会中的身份所决定,人格实质上为身份人格。(二)法律人格的发展—启蒙思想中的伦理人格公元11至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两次大的精神洗礼,即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运动。此后人文主义兴起,明确指出要以人为中心,颂扬人的权威、人的价值、人的高贵和人的伟大。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追求现世的幸福和自由,且人所追求的个人幸福是出于“天赋人性”。人文主义者提倡“人权”,反对“神权”,主张自由平等。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勃兴,人格与人的伦理性开始产生密切的联系,自然法的伟大旋律也重新在欧洲大陆激荡,对政治、法律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价值成为了人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