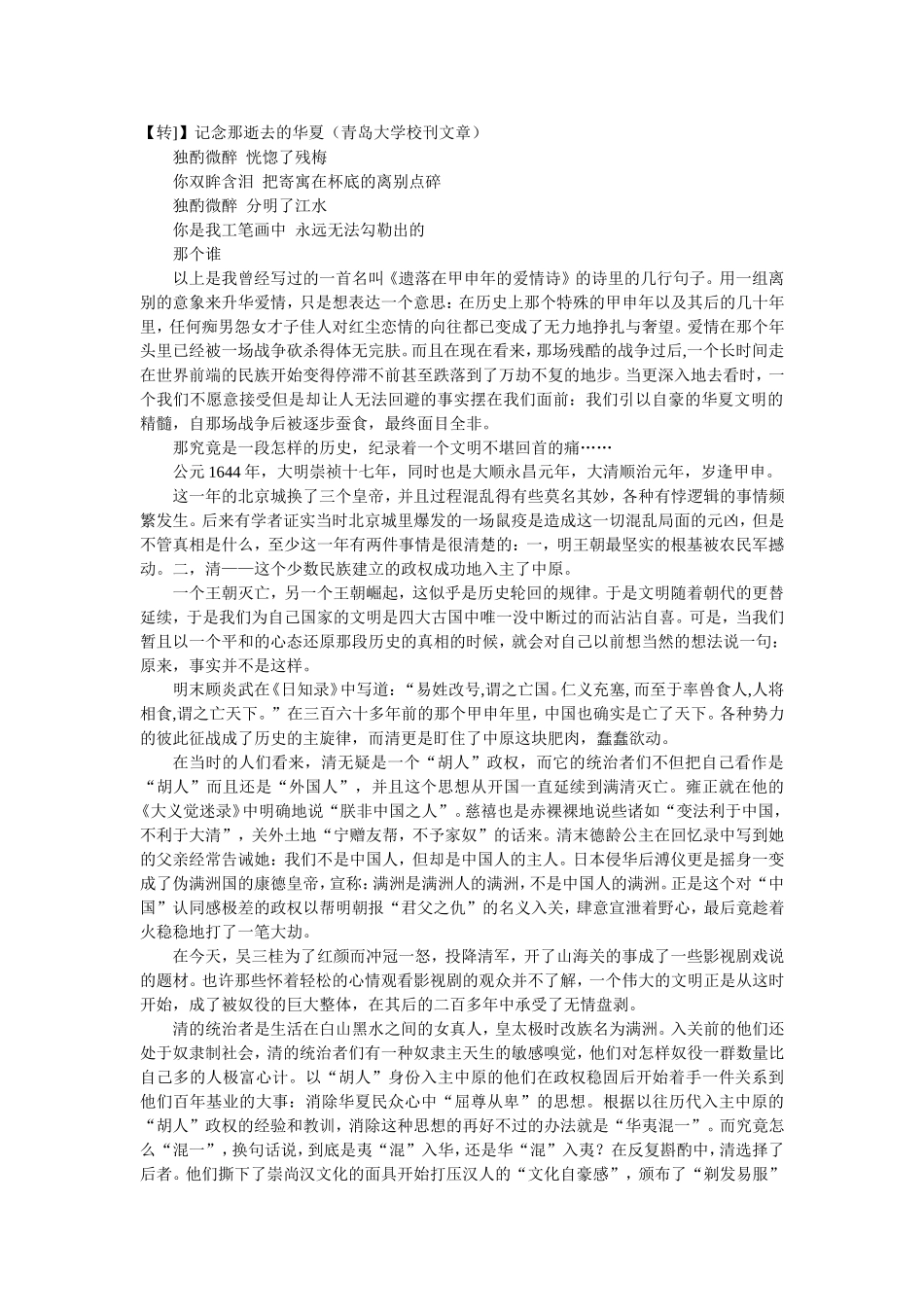【转]】记念那逝去的华夏(青岛大学校刊文章)独酌微醉恍惚了残梅你双眸含泪把寄寓在杯底的离别点碎独酌微醉分明了江水你是我工笔画中永远无法勾勒出的那个谁以上是我曾经写过的一首名叫《遗落在甲申年的爱情诗》的诗里的几行句子。用一组离别的意象来升华爱情,只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在历史上那个特殊的甲申年以及其后的几十年里,任何痴男怨女才子佳人对红尘恋情的向往都已变成了无力地挣扎与奢望。爱情在那个年头里已经被一场战争砍杀得体无完肤。而且在现在看来,那场残酷的战争过后,一个长时间走在世界前端的民族开始变得停滞不前甚至跌落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当更深入地去看时,一个我们不愿意接受但是却让人无法回避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引以自豪的华夏文明的精髓,自那场战争后被逐步蚕食,最终面目全非。那究竟是一段怎样的历史,纪录着一个文明不堪回首的痛……公元1644年,大明崇祯十七年,同时也是大顺永昌元年,大清顺治元年,岁逢甲申。这一年的北京城换了三个皇帝,并且过程混乱得有些莫名其妙,各种有悖逻辑的事情频繁发生。后来有学者证实当时北京城里爆发的一场鼠疫是造成这一切混乱局面的元凶,但是不管真相是什么,至少这一年有两件事情是很清楚的:一,明王朝最坚实的根基被农民军撼动。二,清——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成功地入主了中原。一个王朝灭亡,另一个王朝崛起,这似乎是历史轮回的规律。于是文明随着朝代的更替延续,于是我们为自己国家的文明是四大古国中唯一没中断过的而沾沾自喜。可是,当我们暂且以一个平和的心态还原那段历史的真相的时候,就会对自己以前想当然的想法说一句:原来,事实并不是这样。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三百六十多年前的那个甲申年里,中国也确实是亡了天下。各种势力的彼此征战成了历史的主旋律,而清更是盯住了中原这块肥肉,蠢蠢欲动。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清无疑是一个“胡人”政权,而它的统治者们不但把自己看作是“胡人”而且还是“外国人”,并且这个思想从开国一直延续到满清灭亡。雍正就在他的《大义觉迷录》中明确地说“朕非中国之人”。慈禧也是赤裸裸地说些诸如“变法利于中国,不利于大清”,关外土地“宁赠友帮,不予家奴”的话来。清末德龄公主在回忆录中写到她的父亲经常告诫她:我们不是中国人,但却是中国人的主人。日本侵华后溥仪更是摇身一变成了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宣称: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不是中国人的满洲。正是这个对“中国”认同感极差的政权以帮明朝报“君父之仇”的名义入关,肆意宣泄着野心,最后竟趁着火稳稳地打了一笔大劫。在今天,吴三桂为了红颜而冲冠一怒,投降清军,开了山海关的事成了一些影视剧戏说的题材。也许那些怀着轻松的心情观看影视剧的观众并不了解,一个伟大的文明正是从这时开始,成了被奴役的巨大整体,在其后的二百多年中承受了无情盘剥。清的统治者是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皇太极时改族名为满洲。入关前的他们还处于奴隶制社会,清的统治者们有一种奴隶主天生的敏感嗅觉,他们对怎样奴役一群数量比自己多的人极富心计。以“胡人”身份入主中原的他们在政权稳固后开始着手一件关系到他们百年基业的大事:消除华夏民众心中“屈尊从卑”的思想。根据以往历代入主中原的“胡人”政权的经验和教训,消除这种思想的再好不过的办法就是“华夷混一”。而究竟怎么“混一”,换句话说,到底是夷“混”入华,还是华“混”入夷?在反复斟酌中,清选择了后者。他们撕下了崇尚汉文化的面具开始打压汉人的“文化自豪感”,颁布了“剃发易服”政策。自古以来汉人皆认为头发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大都束发。服饰更是传承了千年的飘逸华丽的峨冠博带,而清廷却让汉人除了留下脑后“大小如金钱,粗细如鼠尾”的辫子外把四周头发尽皆剃去,并脱下他们的民族服饰,换上满人的服装,意图把汉人“胡化”,让他们失去自己的民族记忆,造成一种“同类化”的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夷夏大防”引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从而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历史上强迫汉人外形上从胡俗的胡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