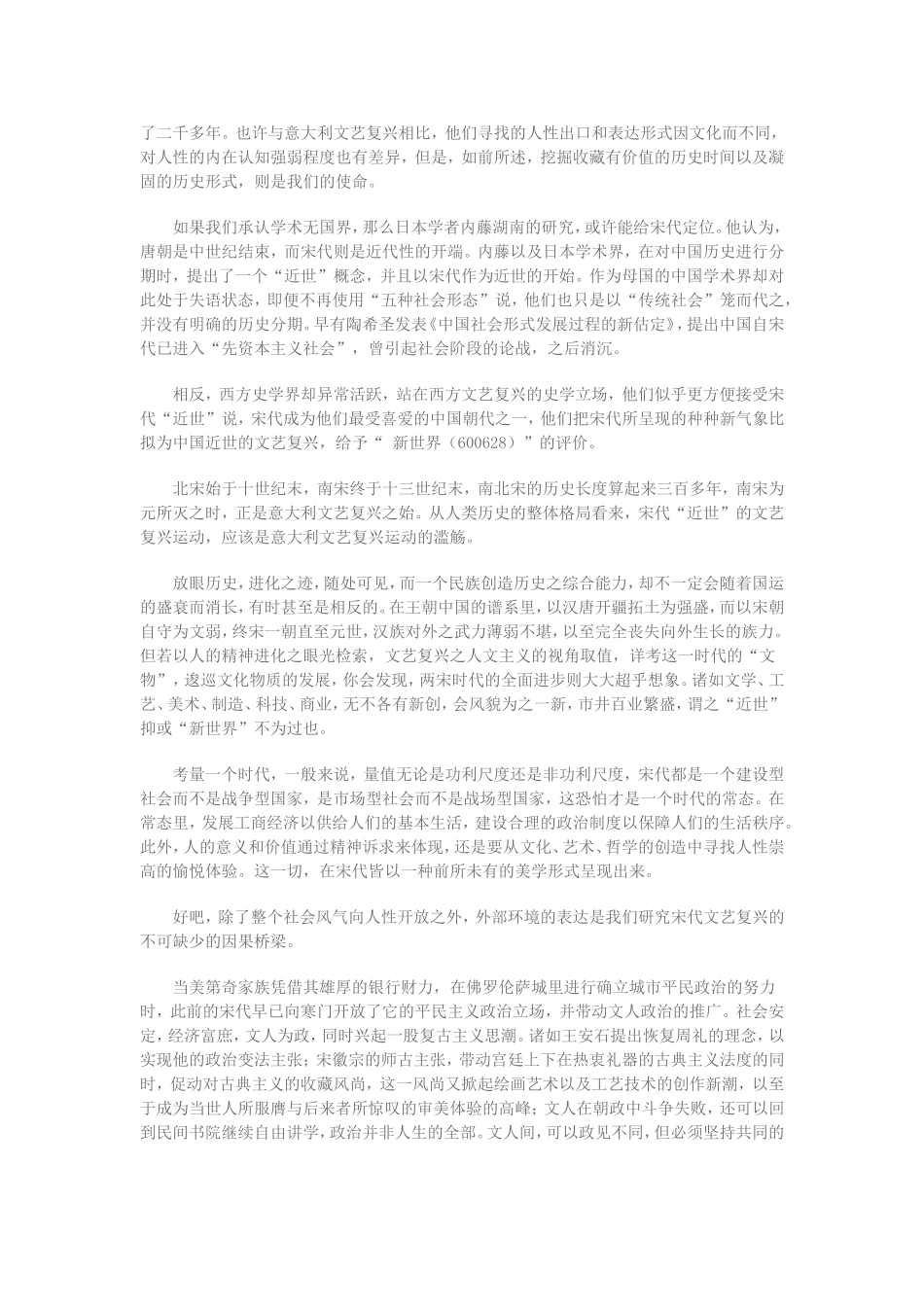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文艺复兴来源:经济观察报作者:李冬君13世纪末开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回归人性的一面镜子,不巧的是,以此为镜,我们看到的却是人性碎片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人性过度膨胀、将精神挤丢了的时代,没有闲暇去原创崇高纯粹的艺术,时尚在匆忙与粗鄙的商业化运作中,散发出的是精致的铜臭味道。不过,作为一名严肃的研究者,我不是用这面镜子来比照当下的,而是用它去鉴定12世纪的中国宋代。看起来,这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只要关于“人”的意义和自由是衡量一切精神创造的价值标尺,而且这个“价值标尺”是亘古不变的公理,是普世的共识,那么,一个当下研究者,在人类精神的大舞台上,凭借那个“价值标尺”,愉快地穿越其间,去维系一个非常有趣的三角时空关系,将宋代置于那座体现了丰富的人类精神内在性的镜子面前,去发现宋代其实已经开始了文艺复兴。人是逐利的,必沦为工具,人也是纯粹的,亦必是人自己的目的。艺术是人作为工具过程的精神润滑剂,也是人以自己为目的的唯一证据。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艺术就应该贯穿我们生活的始终。在两宋,在意大利,我们的确看到了,唯有艺术无愧于这一“价值标尺”,艺术贯穿于精神生活中的繁忙景象,在汴京、在杭州、在佛罗伦萨随处可见,展示着文艺复兴的丰姿和自由气象,从12世纪到13世纪,艺术带给人的是精神饱满,人性欢快,目之所及,酣畅、自由、唯美、纯粹。人性也是考量宋代文艺复兴的指标公元13世纪末,在意大利半岛上,人性将可爱的世俗欲望从教堂的顽石缝里,悄然释放出来,竟然兴起了一场回归人性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有特定的古典含义,它要摆脱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在对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再生中,使人性重获人文主义的形而上肯定,人文主义成为启蒙核心的思想资源,它所唤起的人性能量,成为人追求真善美的原动力。回味二千多年前那个人性灿烂的时代,那个人性自由原创生活的艺术时代,那个被雅斯贝斯称作人类历史的“轴心期”时代,基于人性的创造,几乎涵盖并奠定了人类精神所有需求的第一次,哲学、雕塑、音乐、神庙建筑、绘画、广场、学院、悲剧喜剧、逻辑学、几何学、历史学、体育竞技等等,人性之精神的能量、思想的动力,无所不至。事实是,在古希腊,一切尊重人性、提升人性、歌颂人性的所有艺术,都获得了人的精神认可以及传承不息。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人类遭遇什么样的非人性灾难,挫折之后,只要回到原典,就有重新开始的勇气。“适合人性”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志,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具有“近代性”的标尺,而只有不断地适于人性的需求也才具有普世性。那么,用这把普世的价值标尺,立定在世界史的广角格局上,来衡量我们的历史呢?你会发现中国历史上也有个文艺复兴时代,而最接近这一普世价值的应该是宋代。因为人总要秉着本性活下去,无论压力多大,束缚多紧,它总要找到缝隙去透气。算上公元前后,在中国这片热土上,人性不气不馁地为它自己寻找崇高的存在的合理性,已经努力了二千多年。也许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比,他们寻找的人性出口和表达形式因文化而不同,对人性的内在认知强弱程度也有差异,但是,如前所述,挖掘收藏有价值的历史时间以及凝固的历史形式,则是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承认学术无国界,那么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研究,或许能给宋代定位。他认为,唐朝是中世纪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代性的开端。内藤以及日本学术界,在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时,提出了一个“近世”概念,并且以宋代作为近世的开始。作为母国的中国学术界却对此处于失语状态,即便不再使用“五种社会形态”说,他们也只是以“传统社会”笼而代之,并没有明确的历史分期。早有陶希圣发表《中国社会形式发展过程的新估定》,提出中国自宋代已进入“先资本主义社会”,曾引起社会阶段的论战,之后消沉。相反,西方史学界却异常活跃,站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史学立场,他们似乎更方便接受宋代“近世”说,宋代成为他们最受喜爱的中国朝代之一,他们把宋代所呈现的种种新气象比拟为中国近世的文艺复兴,给予“新世界(600628)”的评价。北宋始于十世纪末,南宋终于十三世纪末,南北宋的历史长度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