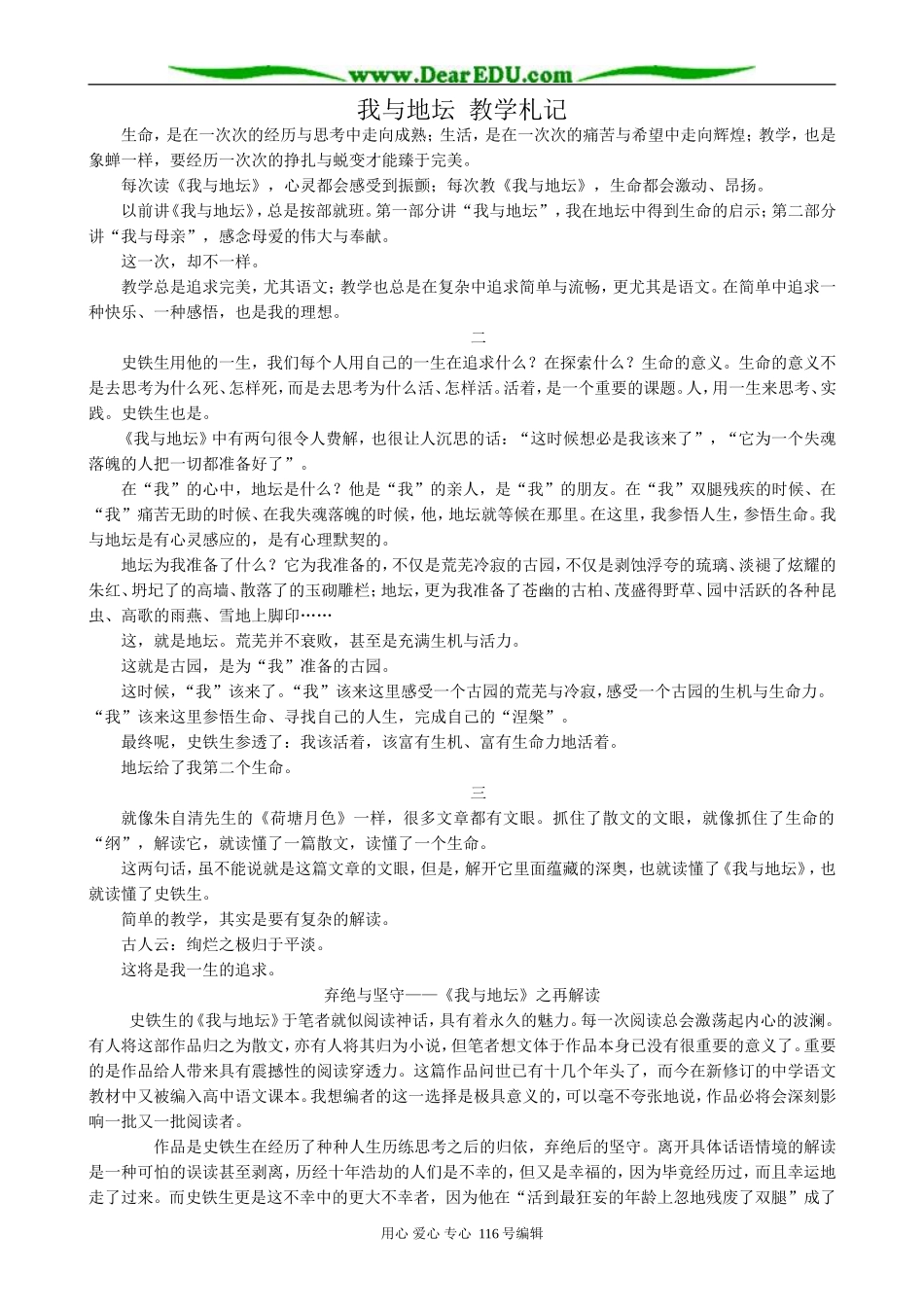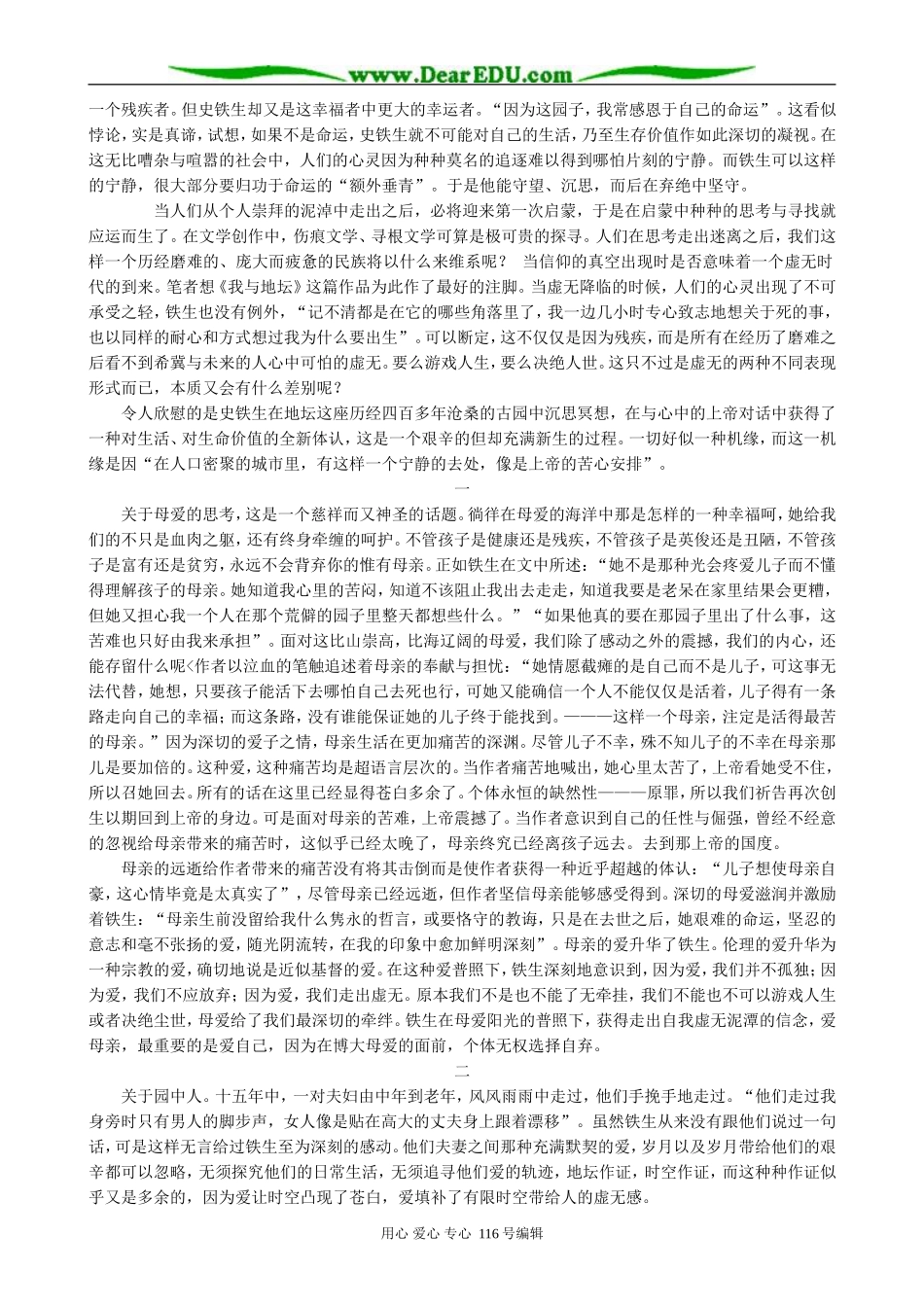我与地坛教学札记生命,是在一次次的经历与思考中走向成熟;生活,是在一次次的痛苦与希望中走向辉煌;教学,也是象蝉一样,要经历一次次的挣扎与蜕变才能臻于完美。每次读《我与地坛》,心灵都会感受到振颤;每次教《我与地坛》,生命都会激动、昂扬。以前讲《我与地坛》,总是按部就班。第一部分讲“我与地坛”,我在地坛中得到生命的启示;第二部分讲“我与母亲”,感念母爱的伟大与奉献。这一次,却不一样。教学总是追求完美,尤其语文;教学也总是在复杂中追求简单与流畅,更尤其是语文。在简单中追求一种快乐、一种感悟,也是我的理想。二史铁生用他的一生,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一生在追求什么?在探索什么?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不是去思考为什么死、怎样死,而是去思考为什么活、怎样活。活着,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人,用一生来思考、实践。史铁生也是。《我与地坛》中有两句很令人费解,也很让人沉思的话:“这时候想必是我该来了”,“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在“我”的心中,地坛是什么?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朋友。在“我”双腿残疾的时候、在“我”痛苦无助的时候、在我失魂落魄的时候,他,地坛就等候在那里。在这里,我参悟人生,参悟生命。我与地坛是有心灵感应的,是有心理默契的。地坛为我准备了什么?它为我准备的,不仅是荒芜冷寂的古园,不仅是剥蚀浮夸的琉璃、淡褪了炫耀的朱红、坍圮了的高墙、散落了的玉砌雕栏;地坛,更为我准备了苍幽的古柏、茂盛得野草、园中活跃的各种昆虫、高歌的雨燕、雪地上脚印……这,就是地坛。荒芜并不衰败,甚至是充满生机与活力。这就是古园,是为“我”准备的古园。这时候,“我”该来了。“我”该来这里感受一个古园的荒芜与冷寂,感受一个古园的生机与生命力。“我”该来这里参悟生命、寻找自己的人生,完成自己的“涅槃”。最终呢,史铁生参透了:我该活着,该富有生机、富有生命力地活着。地坛给了我第二个生命。三就像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一样,很多文章都有文眼。抓住了散文的文眼,就像抓住了生命的“纲”,解读它,就读懂了一篇散文,读懂了一个生命。这两句话,虽不能说就是这篇文章的文眼,但是,解开它里面蕴藏的深奥,也就读懂了《我与地坛》,也就读懂了史铁生。简单的教学,其实是要有复杂的解读。古人云: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将是我一生的追求。弃绝与坚守——《我与地坛》之再解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于笔者就似阅读神话,具有着永久的魅力。每一次阅读总会激荡起内心的波澜。有人将这部作品归之为散文,亦有人将其归为小说,但笔者想文体于作品本身已没有很重要的意义了。重要的是作品给人带来具有震撼性的阅读穿透力。这篇作品问世已有十几个年头了,而今在新修订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又被编入高中语文课本。我想编者的这一选择是极具意义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品必将会深刻影响一批又一批阅读者。作品是史铁生在经历了种种人生历练思考之后的归依,弃绝后的坚守。离开具体话语情境的解读是一种可怕的误读甚至剥离,历经十年浩劫的人们是不幸的,但又是幸福的,因为毕竟经历过,而且幸运地走了过来。而史铁生更是这不幸中的更大不幸者,因为他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成了用心爱心专心116号编辑一个残疾者。但史铁生却又是这幸福者中更大的幸运者。“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这看似悖论,实是真谛,试想,如果不是命运,史铁生就不可能对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存价值作如此深切的凝视。在这无比嘈杂与喧嚣的社会中,人们的心灵因为种种莫名的追逐难以得到哪怕片刻的宁静。而铁生可以这样的宁静,很大部分要归功于命运的“额外垂青”。于是他能守望、沉思,而后在弃绝中坚守。当人们从个人崇拜的泥淖中走出之后,必将迎来第一次启蒙,于是在启蒙中种种的思考与寻找就应运而生了。在文学创作中,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可算是极可贵的探寻。人们在思考走出迷离之后,我们这样一个历经磨难的、庞大而疲惫的民族将以什么来维系呢?当信仰的真空出现时是否意味着一个虚无时代的到来。笔者想《我与地坛》这篇作品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脚。当虚无降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