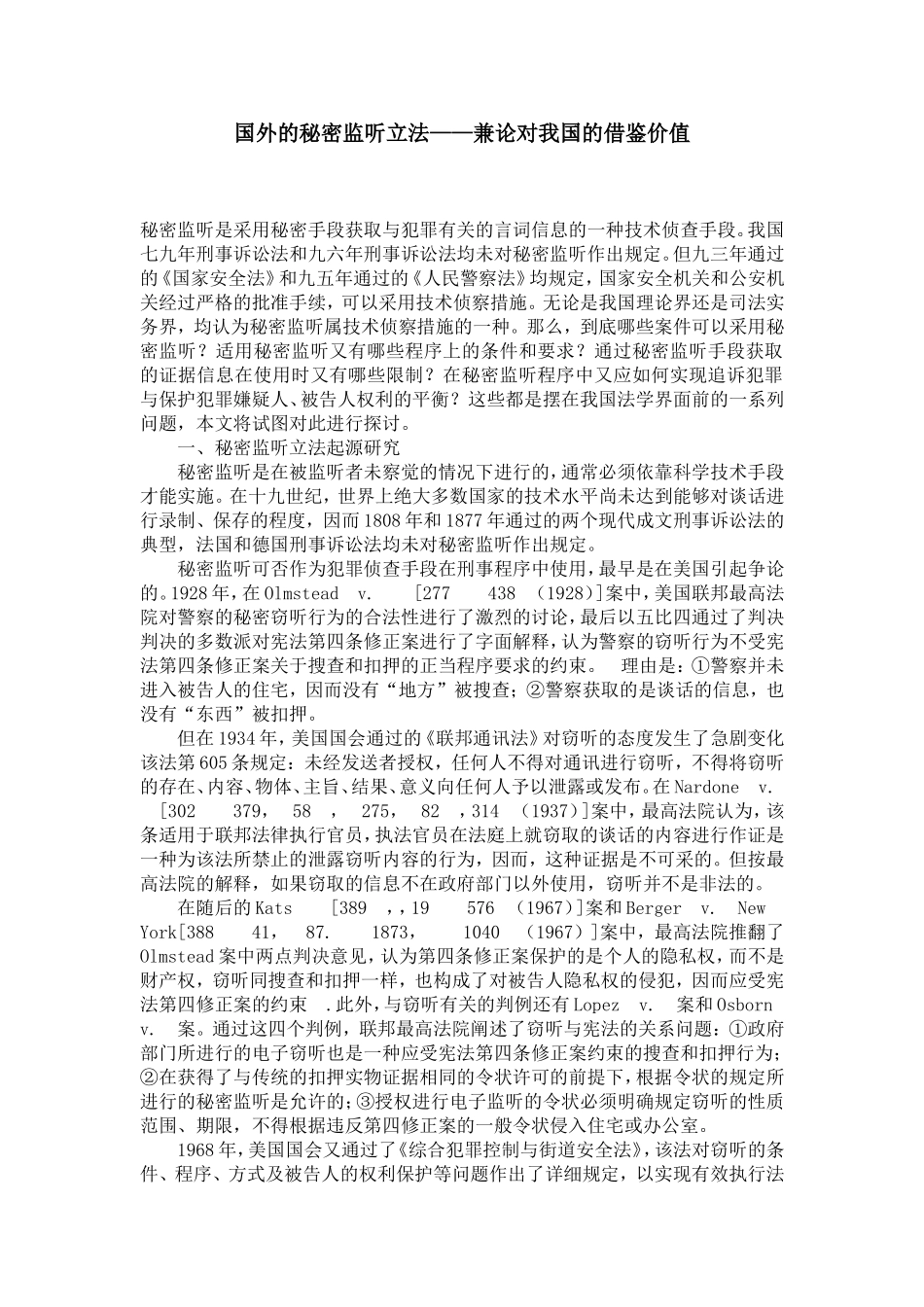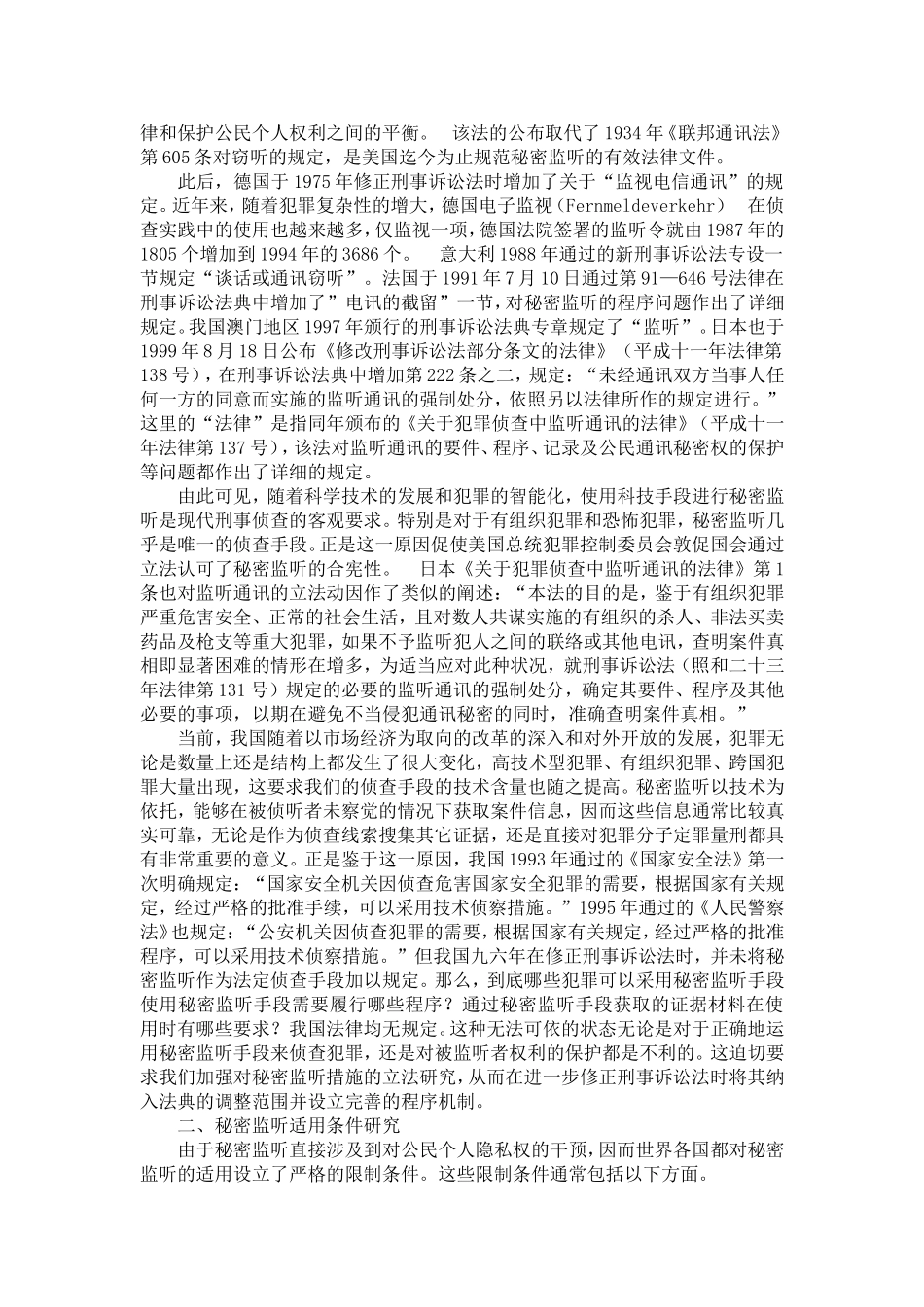国外的秘密监听立法——兼论对我国的借鉴价值秘密监听是采用秘密手段获取与犯罪有关的言词信息的一种技术侦查手段。我国七九年刑事诉讼法和九六年刑事诉讼法均未对秘密监听作出规定。但九三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和九五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均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察措施。无论是我国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认为秘密监听属技术侦察措施的一种。那么,到底哪些案件可以采用秘密监听?适用秘密监听又有哪些程序上的条件和要求?通过秘密监听手段获取的证据信息在使用时又有哪些限制?在秘密监听程序中又应如何实现追诉犯罪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平衡?这些都是摆在我国法学界面前的一系列问题,本文将试图对此进行探讨。一、秘密监听立法起源研究秘密监听是在被监听者未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通常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手段才能实施。在十九世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技术水平尚未达到能够对谈话进行录制、保存的程度,因而1808年和1877年通过的两个现代成文刑事诉讼法的典型,法国和德国刑事诉讼法均未对秘密监听作出规定。秘密监听可否作为犯罪侦查手段在刑事程序中使用,最早是在美国引起争论的。1928年,在Olmsteadv.[277438(1928)]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警察的秘密窃听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后以五比四通过了判决判决的多数派对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进行了字面解释,认为警察的窃听行为不受宪法第四条修正案关于搜查和扣押的正当程序要求的约束。理由是:①警察并未进入被告人的住宅,因而没有“地方”被搜查;②警察获取的是谈话的信息,也没有“东西”被扣押。但在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通讯法》对窃听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该法第605条规定:未经发送者授权,任何人不得对通讯进行窃听,不得将窃听的存在、内容、物体、主旨、结果、意义向任何人予以泄露或发布。在Nardonev.[302379,58,275,82,314(1937)]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该条适用于联邦法律执行官员,执法官员在法庭上就窃取的谈话的内容进行作证是一种为该法所禁止的泄露窃听内容的行为,因而,这种证据是不可采的。但按最高法院的解释,如果窃取的信息不在政府部门以外使用,窃听并不是非法的。在随后的Kats[389,,19576(1967)]案和Bergerv.NewYork[38841,87.1873,1040(1967)]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Olmstead案中两点判决意见,认为第四条修正案保护的是个人的隐私权,而不是财产权,窃听同搜查和扣押一样,也构成了对被告人隐私权的侵犯,因而应受宪法第四修正案的约束.此外,与窃听有关的判例还有Lopezv.案和Osbornv.案。通过这四个判例,联邦最高法院阐述了窃听与宪法的关系问题:①政府部门所进行的电子窃听也是一种应受宪法第四条修正案约束的搜查和扣押行为;②在获得了与传统的扣押实物证据相同的令状许可的前提下,根据令状的规定所进行的秘密监听是允许的;③授权进行电子监听的令状必须明确规定窃听的性质范围、期限,不得根据违反第四修正案的一般令状侵入住宅或办公室。1968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该法对窃听的条件、程序、方式及被告人的权利保护等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以实现有效执行法律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该法的公布取代了1934年《联邦通讯法》第605条对窃听的规定,是美国迄今为止规范秘密监听的有效法律文件。此后,德国于1975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关于“监视电信通讯”的规定。近年来,随着犯罪复杂性的增大,德国电子监视(Fernmeldeverkehr)在侦查实践中的使用也越来越多,仅监视一项,德国法院签署的监听令就由1987年的1805个增加到1994年的3686个。意大利1988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专设一节规定“谈话或通讯窃听”。法国于1991年7月10日通过第91—646号法律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增加了”电讯的截留”一节,对秘密监听的程序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我国澳门地区1997年颁行的刑事诉讼法典专章规定了“监听”。日本也于1999年8月18日公布《修改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的法律》(平成十一年法律第138号),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增加第222条之二,规定:“未经通讯双方当事人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