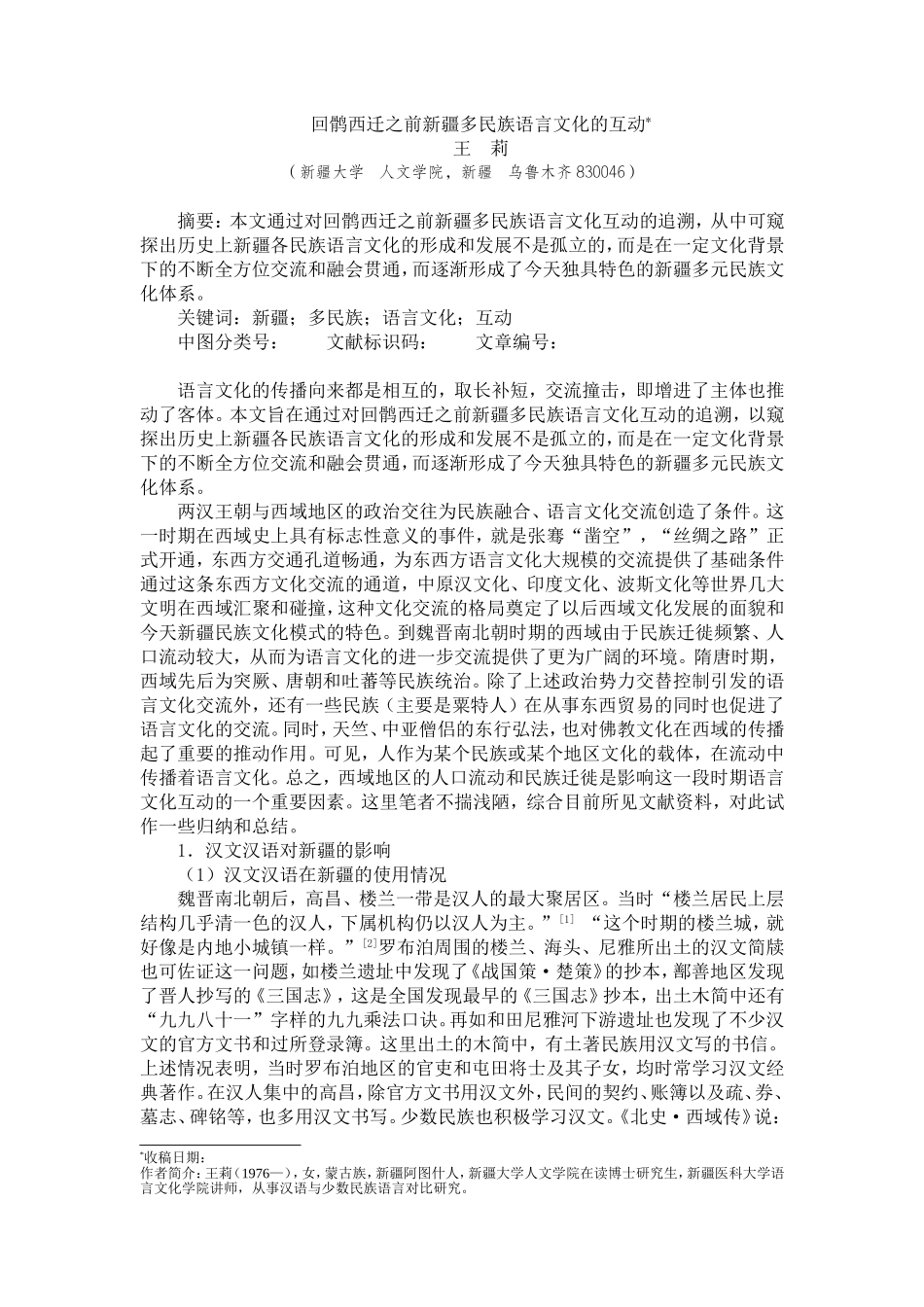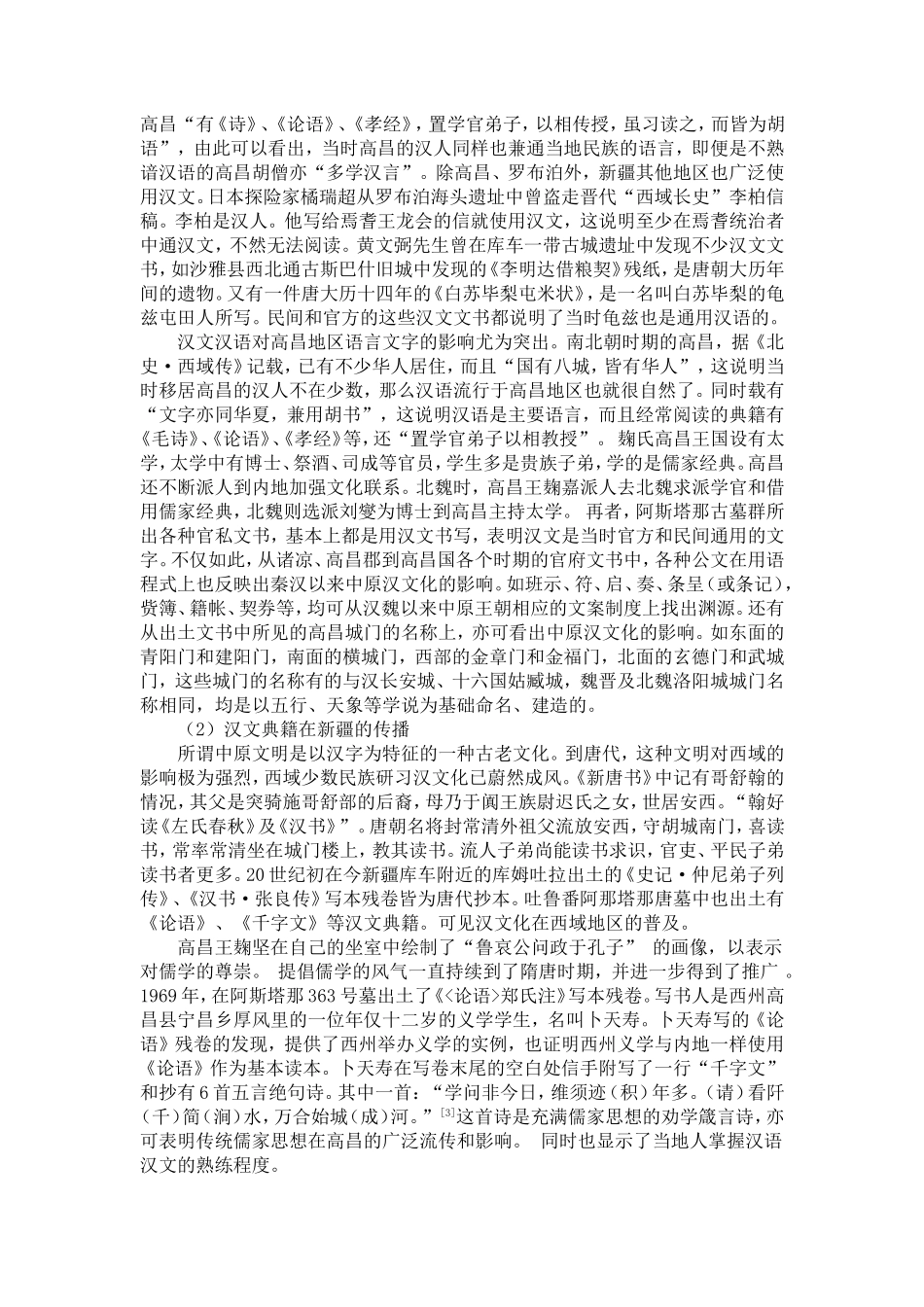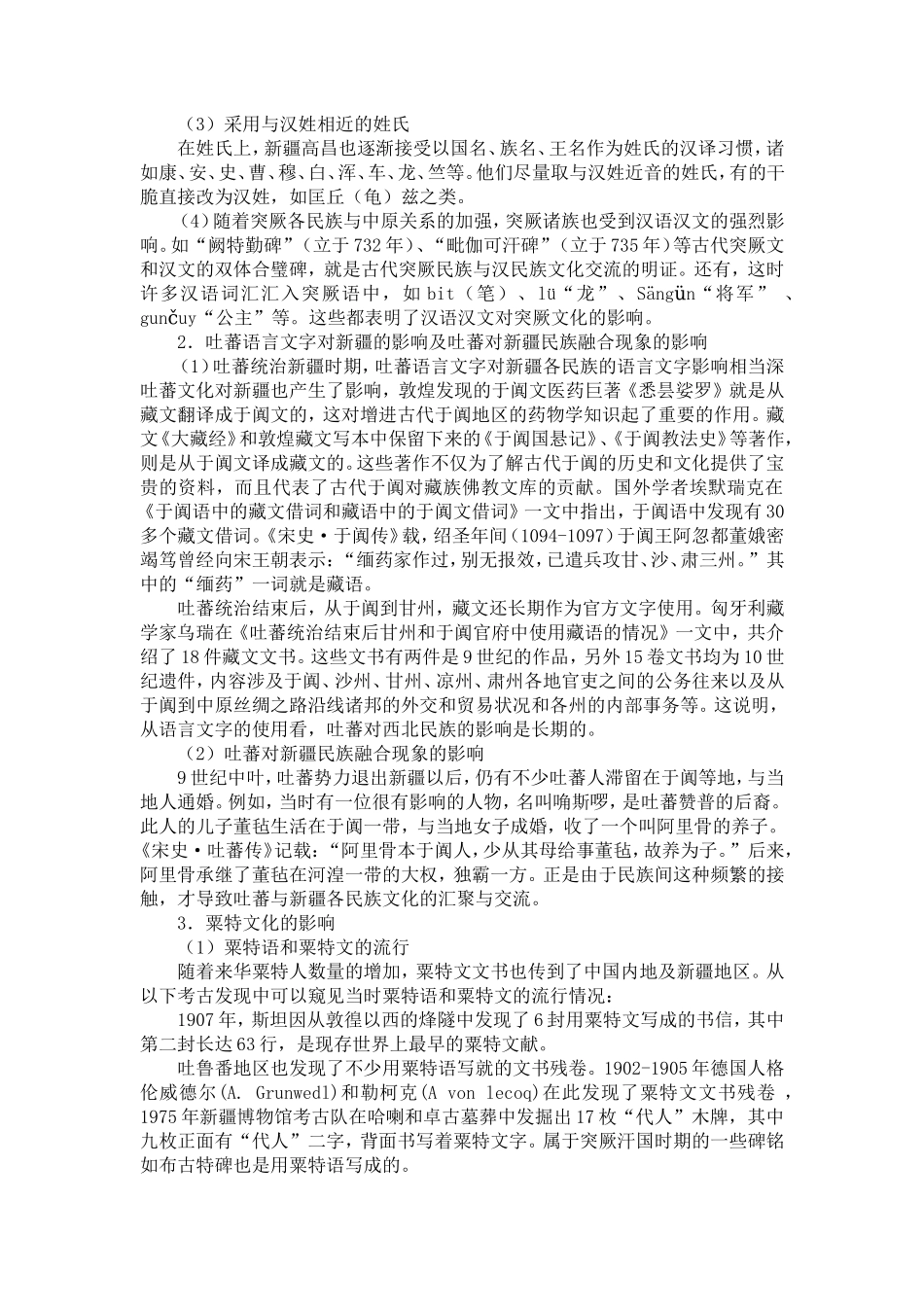回鹘西迁之前新疆多民族语言文化的互动*王莉(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摘要:本文通过对回鹘西迁之前新疆多民族语言文化互动的追溯,从中可窥探出历史上新疆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不断全方位交流和融会贯通,而逐渐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体系。关键词:新疆;多民族;语言文化;互动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语言文化的传播向来都是相互的,取长补短,交流撞击,即增进了主体也推动了客体。本文旨在通过对回鹘西迁之前新疆多民族语言文化互动的追溯,以窥探出历史上新疆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不断全方位交流和融会贯通,而逐渐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体系。两汉王朝与西域地区的政治交往为民族融合、语言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在西域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就是张骞“凿空”,“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东西方交通孔道畅通,为东西方语言文化大规模的交流提供了基础条件通过这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等世界几大文明在西域汇聚和碰撞,这种文化交流的格局奠定了以后西域文化发展的面貌和今天新疆民族文化模式的特色。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由于民族迁徙频繁、人口流动较大,从而为语言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环境。隋唐时期,西域先后为突厥、唐朝和吐蕃等民族统治。除了上述政治势力交替控制引发的语言文化交流外,还有一些民族(主要是粟特人)在从事东西贸易的同时也促进了语言文化的交流。同时,天竺、中亚僧侣的东行弘法,也对佛教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见,人作为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区文化的载体,在流动中传播着语言文化。总之,西域地区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是影响这一段时期语言文化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笔者不揣浅陋,综合目前所见文献资料,对此试作一些归纳和总结。1.汉文汉语对新疆的影响(1)汉文汉语在新疆的使用情况魏晋南北朝后,高昌、楼兰一带是汉人的最大聚居区。当时“楼兰居民上层结构几乎清一色的汉人,下属机构仍以汉人为主。”[1]“这个时期的楼兰城,就好像是内地小城镇一样。”[2]罗布泊周围的楼兰、海头、尼雅所出土的汉文简牍也可佐证这一问题,如楼兰遗址中发现了《战国策·楚策》的抄本,鄯善地区发现了晋人抄写的《三国志》,这是全国发现最早的《三国志》抄本,出土木简中还有“九九八十一”字样的九九乘法口诀。再如和田尼雅河下游遗址也发现了不少汉文的官方文书和过所登录簿。这里出土的木简中,有土著民族用汉文写的书信。上述情况表明,当时罗布泊地区的官吏和屯田将士及其子女,均时常学习汉文经典著作。在汉人集中的高昌,除官方文书用汉文外,民间的契约、账簿以及疏、券、墓志、碑铭等,也多用汉文书写。少数民族也积极学习汉文。《北史·西域传》说:*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王莉(1976—),女,蒙古族,新疆阿图什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从事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高昌“有《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传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高昌的汉人同样也兼通当地民族的语言,即便是不熟谙汉语的高昌胡僧亦“多学汉言”。除高昌、罗布泊外,新疆其他地区也广泛使用汉文。日本探险家橘瑞超从罗布泊海头遗址中曾盗走晋代“西域长史”李柏信稿。李柏是汉人。他写给焉耆王龙会的信就使用汉文,这说明至少在焉耆统治者中通汉文,不然无法阅读。黄文弼先生曾在库车一带古城遗址中发现不少汉文文书,如沙雅县西北通古斯巴什旧城中发现的《李明达借粮契》残纸,是唐朝大历年间的遗物。又有一件唐大历十四年的《白苏毕梨屯米状》,是一名叫白苏毕梨的龟兹屯田人所写。民间和官方的这些汉文文书都说明了当时龟兹也是通用汉语的。汉文汉语对高昌地区语言文字的影响尤为突出。南北朝时期的高昌,据《北史·西域传》记载,已有不少华人居住,而且“国有八城,皆有华人”,这说明当时移居高昌的汉人不在少数,那么汉语流行于高昌地区也就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