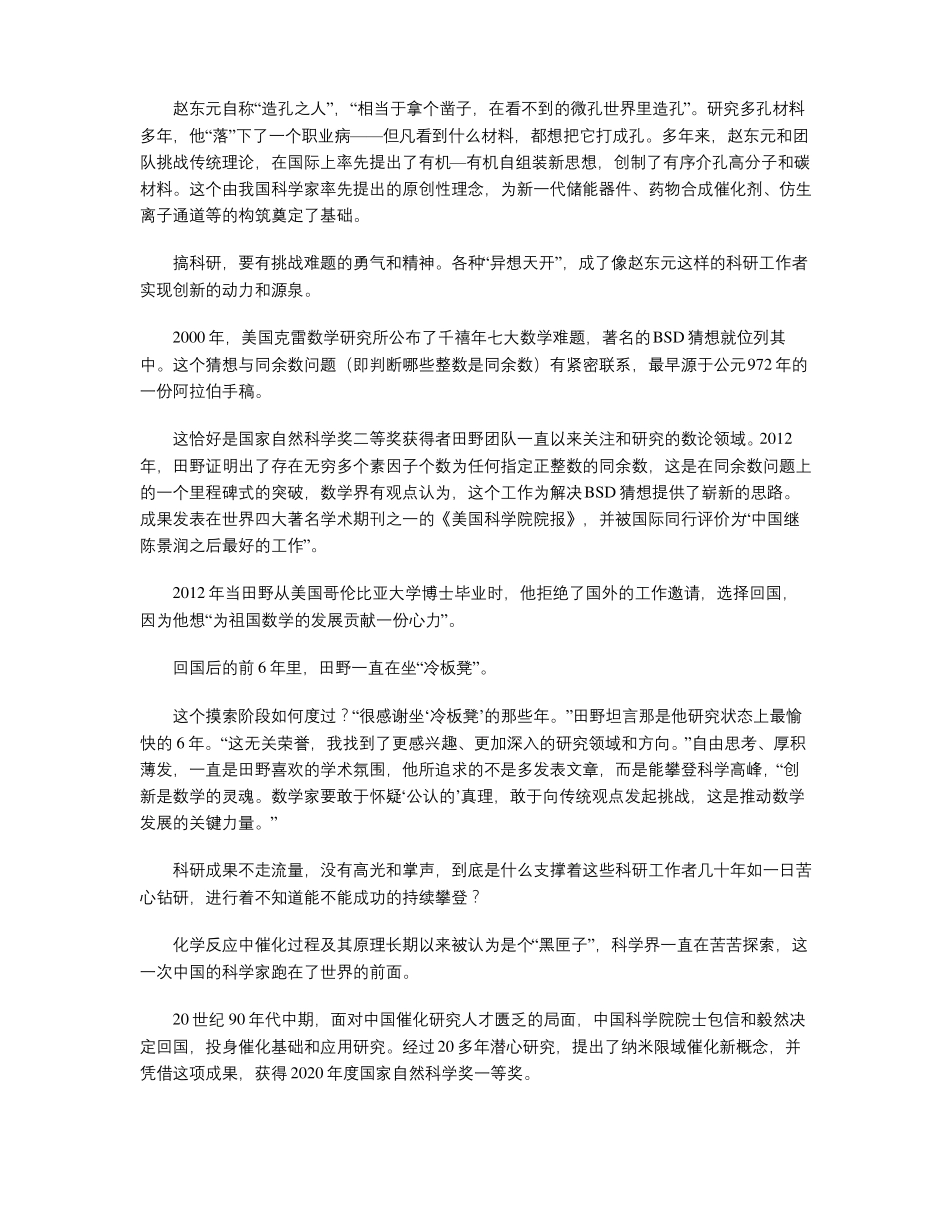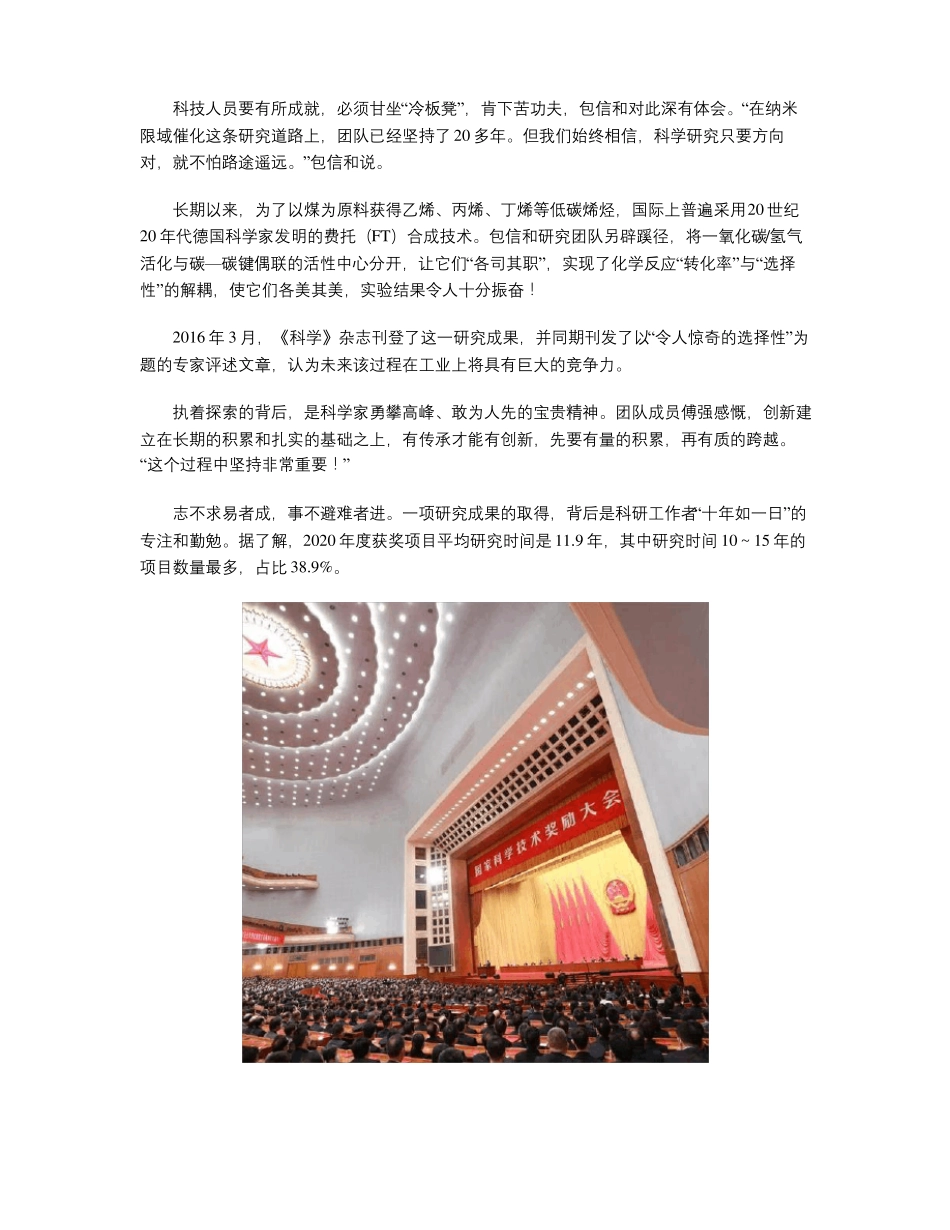心怀“国之大者”作者:崔兴毅来源:《科学大观园》2021年第23期11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因为他们,星光熠熠。有满头银发的长者,有风华正茂的青年,他们是科技界的杰出代表。站在领奖台上,他们的手中,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这里颁授。46项国家自然科学奖、6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157项国家科技进步奖……这是一份令人赞叹的成绩单。科研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成绩单背后,是多少科技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初心、执着攻关的坚韧和热忱——为了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前沿科技乘势而上,关键技术不断攻克。走近一个个获奖项目,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脉动清晰可感。国家科技奖励持续激励基础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奖,是授予在基础研究领域具有重大突破和发现的重量级奖项,由于它的高标准,一等奖曾经数次空缺。凭借在介孔材料领域里程碑式的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团队荣获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一项科研成果能够被人们认可,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莫大的荣幸。”赵东元感慨道。赵东元自称“造孔之人”,“相当于拿个凿子,在看不到的微孔世界里造孔”。研究多孔材料多年,他“落”下了一个职业病——但凡看到什么材料,都想把它打成孔。多年来,赵东元和团队挑战传统理论,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有机—有机自组装新思想,创制了有序介孔高分子和碳材料。这个由我国科学家率先提出的原创性理念,为新一代储能器件、药物合成催化剂、仿生离子通道等的构筑奠定了基础。搞科研,要有挑战难题的勇气和精神。各种“异想天开”,成了像赵东元这样的科研工作者实现创新的动力和源泉。2000年,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公布了千禧年七大数学难题,著名的BSD猜想就位列其中。这个猜想与同余数问题(即判断哪些整数是同余数)有紧密联系,最早源于公元972年的一份阿拉伯手稿。这恰好是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田野团队一直以来关注和研究的数论领域。2012年,田野证明出了存在无穷多个素因子个数为任何指定正整数的同余数,这是在同余数问题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数学界有观点认为,这个工作为解决BSD猜想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成果发表在世界四大著名学术期刊之一的《美国科学院院报》,并被国际同行评价为“中国继陈景润之后最好的工作”。2012年当田野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时,他拒绝了国外的工作邀请,选择回国,因为他想“为祖国数学的发展贡献一份心力”。回国后的前6年里,田野一直在坐“冷板凳”。这个摸索阶段如何度过?“很感谢坐‘冷板凳’的那些年。”田野坦言那是他研究状态上最愉快的6年。“这无关荣誉,我找到了更感兴趣、更加深入的研究领域和方向。”自由思考、厚积薄发,一直是田野喜欢的学术氛围,他所追求的不是多发表文章,而是能攀登科学高峰,“创新是数学的灵魂。数学家要敢于怀疑‘公认的’真理,敢于向传统观点发起挑战,这是推动数学发展的关键力量。”科研成果不走流量,没有高光和掌声,到底是什么支撑着这些科研工作者几十年如一日苦心钻研,进行着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持续攀登?化学反应中催化过程及其原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个“黑匣子”,科学界一直在苦苦探索,这一次中国的科学家跑在了世界的前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面对中国催化研究人才匮乏的局面,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毅然决定回国,投身催化基础和应用研究。经过20多年潜心研究,提出了纳米限域催化新概念,并凭借这项成果,获得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科技人员要有所成就,必须甘坐“冷板凳”,肯下苦功夫,包信和对此深有体会。“在纳米限域催化这条研究道路上,团队已经坚持了20多年。但我们始终相信,科学研究只要方向对,就不怕路途遥远。”包信和说。长期以来,为了以煤为原料获得乙烯、丙烯、丁烯等低碳烯烃,国际上普遍采用20世纪2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明的费托(FT)合成技术。包信和研究团队另辟蹊径,将一氧化碳/氢气活化与碳—碳键偶联的活性中心分开,让它们“各司其职”,实现了化学反应“转化率”与“选择性”的解耦,使它们各美其美,实验结果令人十分振奋!2016年3月,《科学》杂志刊登了这一研究成果,并同期刊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