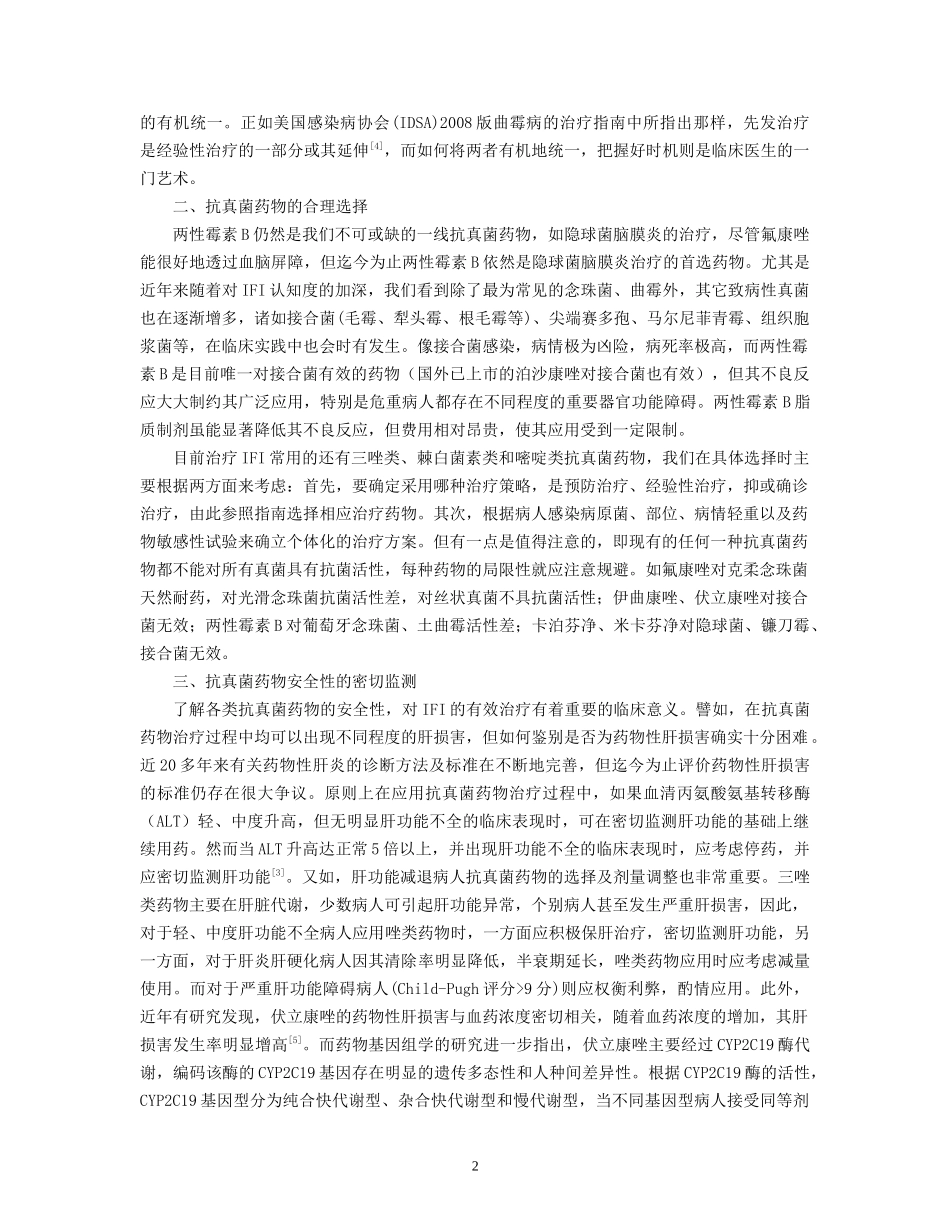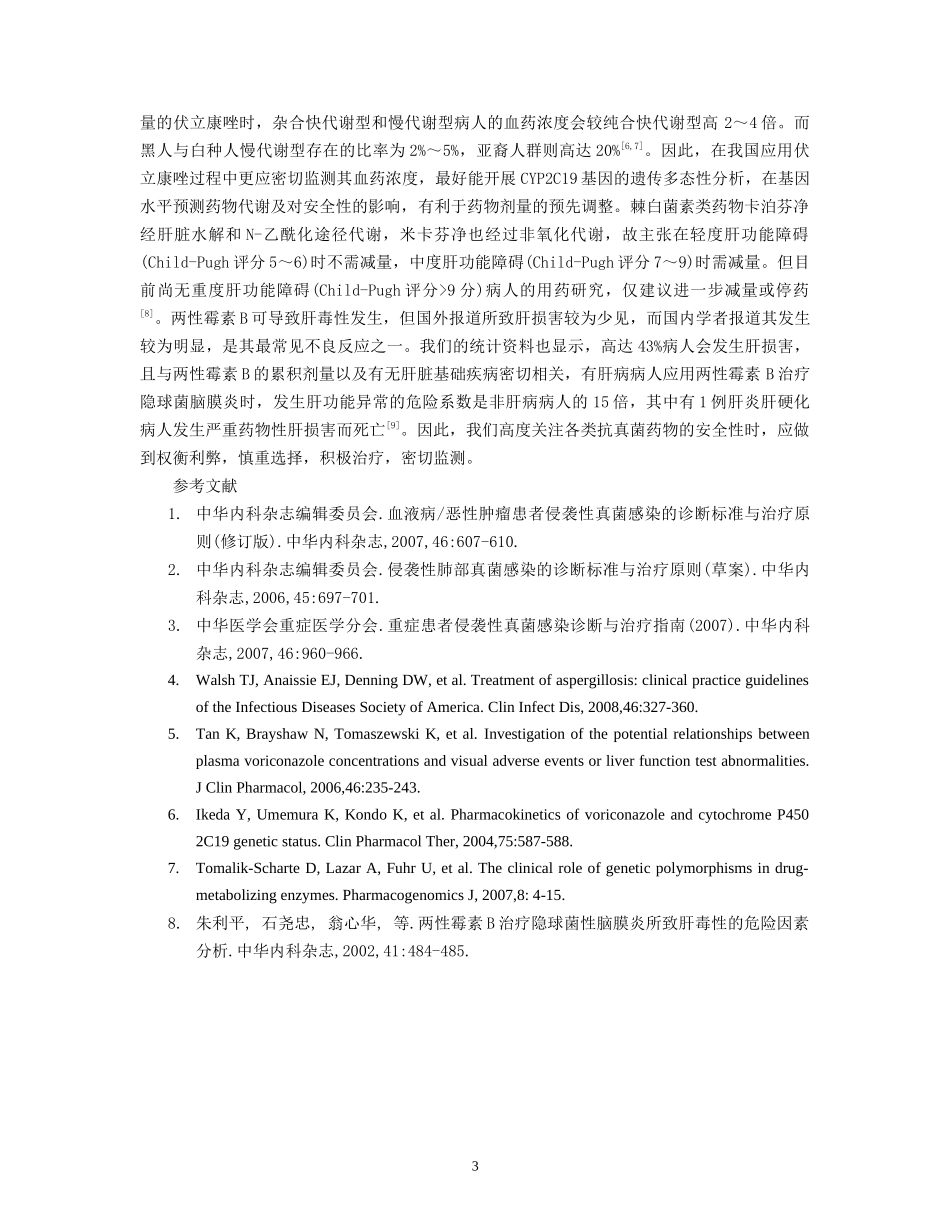在指南与实践中加深对危重病人侵袭性真菌感染的认识Insightsintoinvasivefungalinfectionsinpatientswithcriticalillness:Interactionsbetweenguidelinesandpractice翁心华朱利平(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200040)随着骨髓移植、实体器官移植、肿瘤化疗、大剂量广谱抗菌药物的长期应用,以及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的广泛应用等因素,侵袭性真菌感染(IFI)的患病率和病死率显著上升。为此,近年来在此领域也有较多新进展,如诊断方面建立了肺部高分辨CT早期诊断侵袭性肺曲霉病,开展了血清曲霉特异性抗原检测(半乳甘露聚糖试验,GM试验),以及血清真菌特异性抗原检测[(1→3)-β-D-葡聚糖试验,BG试验],为IFI的早期诊断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新型抗真菌药物的不断问世,如两性霉素B的脂质制剂、伊曲康唑的水溶制剂、伏立康唑、泊沙康唑、卡泊芬净等,为IFI的有效治疗带来了希望。在此基础上,欧美、澳洲、日本等国相继出台并更新IFI治疗指南,我国血液病学、呼吸学科及危重病学科也先后制订和更新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指南,为提高对IFI的认识与交流,降低其患病率和病死率起到关键性作用。尽管如此,侵袭性真菌感染仍然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就目前IFI的治疗指南与实践,重点讨论以下几点认识。一、经验性治疗与先发治疗的有机统一所谓经验性治疗,在血液病学科是指在免疫缺陷、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出现不明原因发热,广谱抗菌药物治疗7天无效者,或起初有效,但3~7d后再出现发热,在积极寻找病因同时,可经验性应用抗真菌药物治疗[1]。在呼吸病和危重病学科也有类似的定义,主要是针对拟诊病人在未获得微生物学依据,且广谱抗菌药物治疗无效时,给予积极地抗真菌药物治疗[2,3]。先发治疗则是指临床诊断病人已经具备微生物学[分泌物或体液真菌培养,和(或)血液真菌抗原及其他血清免疫学检测]阳性证据,但尚无无菌体液或组织病理学确诊证据时所采取的治疗策略。由此可见,先发治疗要较经验性治疗针对性更强,可避免过早治疗很有可能并非真菌感染而导致的过度治疗,所以目前更倾向于先发治疗。但有时若等到完全明了后再治疗,会错过治疗窗口,达不到满意的疗效,甚或延误病机导致死亡,因而在临床实践中治疗时机的把握有时确实很难。我们在实践工作中体会到一点,就是在做出决策前,对病人的高危因素和病情危重程度作一评估非常重要。对于极度高危且病情危重病人,由于一旦出现IFI,病死率极高,而早期诊断又非常困难,此时宜采用经验性治疗,甚至早期经验性治疗,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对于病情并非十分凶险的病人,我们尽可能多收集一些临床真菌感染的微生物学证据,应积极开展呼吸道等临床标本的真菌涂片、培养,以及肺部CT的动态监测,有条件的单位还可进行GM试验和BG试验,由此所采用的先发治疗针对性更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应用GM、BG试验时,对于非血液系统粒细胞缺乏或骨髓移植病人,其敏感性和特异性都有很大的差异,应结合临床综合考虑其结果,以免误诊或漏诊。对于一些病情相对较轻的病人,或慢性疑难病例,我们更可以充分寻求确诊依据,尤其是病理组织培养和真菌病理学诊断,以达到精确制导的目的。因此,指南中所提出的经验性治疗和先发治疗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很好1的有机统一。正如美国感染病协会(IDSA)2008版曲霉病的治疗指南中所指出那样,先发治疗是经验性治疗的一部分或其延伸[4],而如何将两者有机地统一,把握好时机则是临床医生的一门艺术。二、抗真菌药物的合理选择两性霉素B仍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线抗真菌药物,如隐球菌脑膜炎的治疗,尽管氟康唑能很好地透过血脑屏障,但迄今为止两性霉素B依然是隐球菌脑膜炎治疗的首选药物。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对IFI认知度的加深,我们看到除了最为常见的念珠菌、曲霉外,其它致病性真菌也在逐渐增多,诸如接合菌(毛霉、犁头霉、根毛霉等)、尖端赛多孢、马尔尼菲青霉、组织胞浆菌等,在临床实践中也会时有发生。像接合菌感染,病情极为凶险,病死率极高,而两性霉素B是目前唯一对接合菌有效的药物(国外已上市的泊沙康唑对接合菌也有效),但其不良反应大大制约其广泛应用,特别是危重病人都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