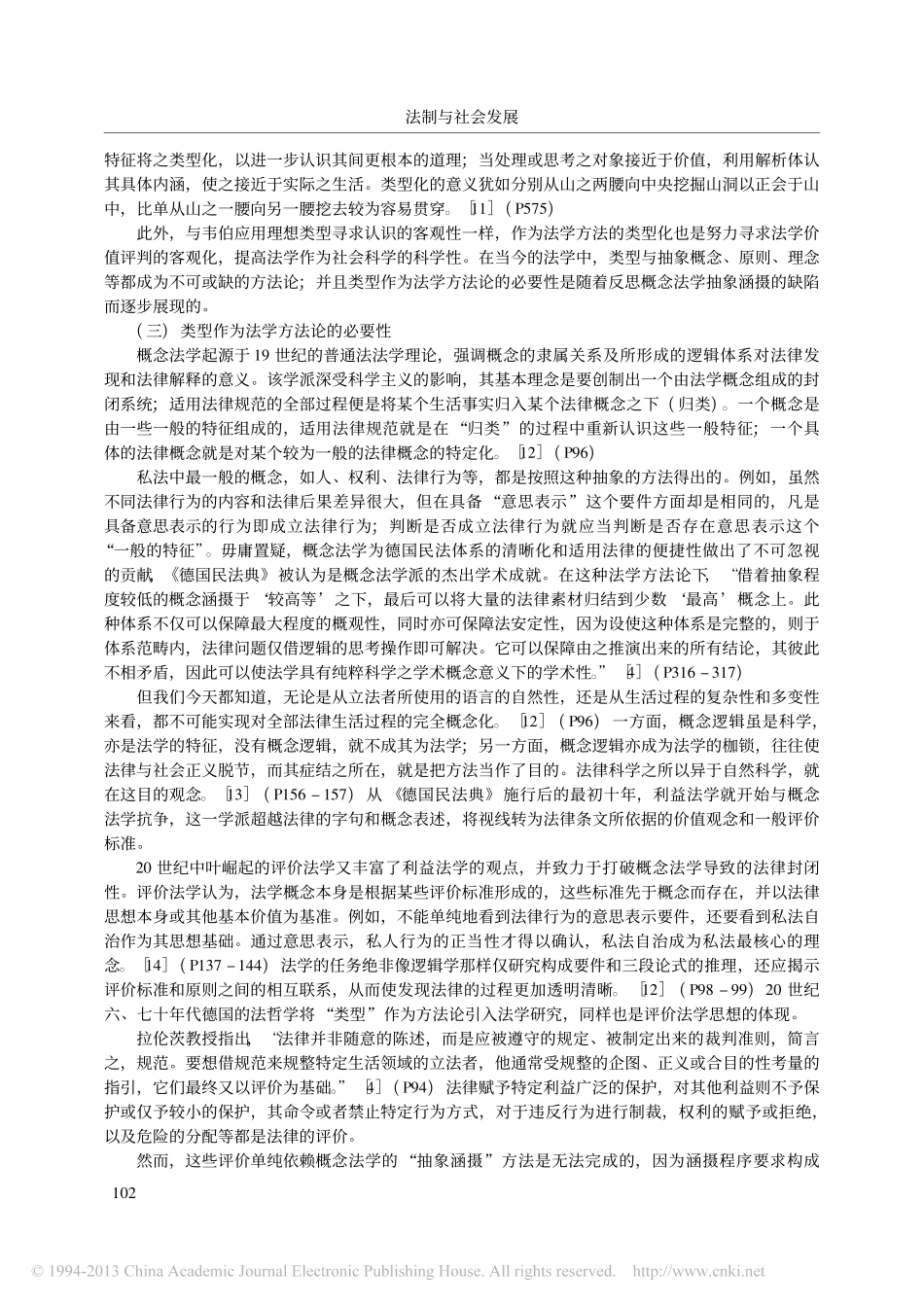收稿日期:2013-03-0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事行为制度研究”(10BFX086)作者简介:程淑娟(1972-),女,陕西宝鸡人,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①法哲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强调“万物归一”的神学取向,二是强调“格物致知”的科学取向,三是强调“对话商谈”诠释学取向。当前的法哲学以科学取向和诠释学作为主要路径。参见谢晖:《科学与诠释:法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法律科学》2003年第1期。而“诠释”是一种“理解的艺术”,理解就要析出理解对象的本意,所以“诠释”本身就含有方法论的诉求。理解同时是客观和主观的,理解者带着客观与主观进入“理解视界”,他不是纯消极地反映要被理解的现象,而是构建被理解的现象。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147页。本文即在上述意义上使用“诠释”一语。商行为:一种类型化方法的诠释程淑娟(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陕西西安710063)摘要:类型作为法学方法论能够弥补概念法学抽象涵摄方法的不足。将商行为作为类型而非法律行为那样的抽象概念,是因为商行为符合类型的一系列要求:商行为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性,将其作为类型能区分商与非商行为,还能肯认商行为的正当性,引导商行为的理性化;商行为的构成要素具有灵动性,它们丰富且具体,有时无须全部具备,商行为的边界也具有开放性;商行为的不同构成要素之间还具有维系性。将商行为作为类型,能实现其与民法法律行为制度的协同,并能实现商行为体系的逻辑自足。关键词:商行为;类型;法学方法中图分类号:D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28(2013)03-0100-12大陆法系很多国家确立有自己的商行为制度,或是将其作为商法典的支柱性内容,或是“依附于”民法典的行为或法律行为制度。但在我国,“什么是商行为”在诠释上相当凌乱,商法法理的科学性一再被质疑。笔者认为,打破商行为研究的瓶颈,必须寻求法学方法论的突破。如果我们转换用“类型化”这一法学方法,就会发现,实践中复杂多变的商行为适宜于作为类型,而不是法律行为那样的抽象概念。这种研究方法的转换对商行为而言将不仅是另辟蹊径,更是柳暗花明的诠释。①一、作为法学方法论的类型(一)类型的含义类型即是我们常说的“种类”、“分类”以及“典型”;属于某一类型的事物,应当具有共同的特征。据学者考证,类型一词起源于希腊字,原意指纯粹的击打、锤击或因击打所造成的结果,再后来被作为“转借意义”指一种有特征的形体、特性或风格;或模范、典范、模型、范例等。[1](P300-301)001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13年第3期(总第111期)在哲学的认识论上,类型显然是以事物“共相”之存在为前提。所谓“共相”,是“殊相”的对称,凡是在感觉中所给定的东西,或和感觉中所给定的东西同性质的东西,我们就说它是一个特殊的东西;与此相反,一个共相则是那种能为许多特殊的东西所分享的。[2](P75)类型不仅表示多数个别或特殊对象的典范,而且也表示多数现象所共同的基本形式;它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共相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对具体事物的一定程度的抽象。虽然相对于舍弃个别特征,追求事物“最本质性”规定的抽象概念,类型的抽象程度较低,但类型不是具体、特殊的事物,而是“一种可以反复找到的存在物”。[1](P302)黑格尔在其辩证法中曾提出过“具体概念”,系指事物所固有的具体性,经过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以理性的形式在人脑中再现出来,从而展现出事物的联系性、全面性和丰富性。[3](P119)类型与具体概念的功能较为相似,都关切因形而上的抽象概念所忽略的对“意义脉络”的掌握,此外,它们都“一方面应于其诸多因素中来开展概念,另一方面应由此等因素出发,而一再反省每项因素与其余全部因素的脉络关联”。[4](P335)因而类型不仅是认识论,也是与辩证法相似的方法论。(二)类型在社会学的应用及对法学的启示应用类型的研究方法即“类型化”。类型化的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有极大的应用空间。马克斯·韦伯通过“理想类型”说明和解释理想与生活经验的联系,完美诠释了类型对社会学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