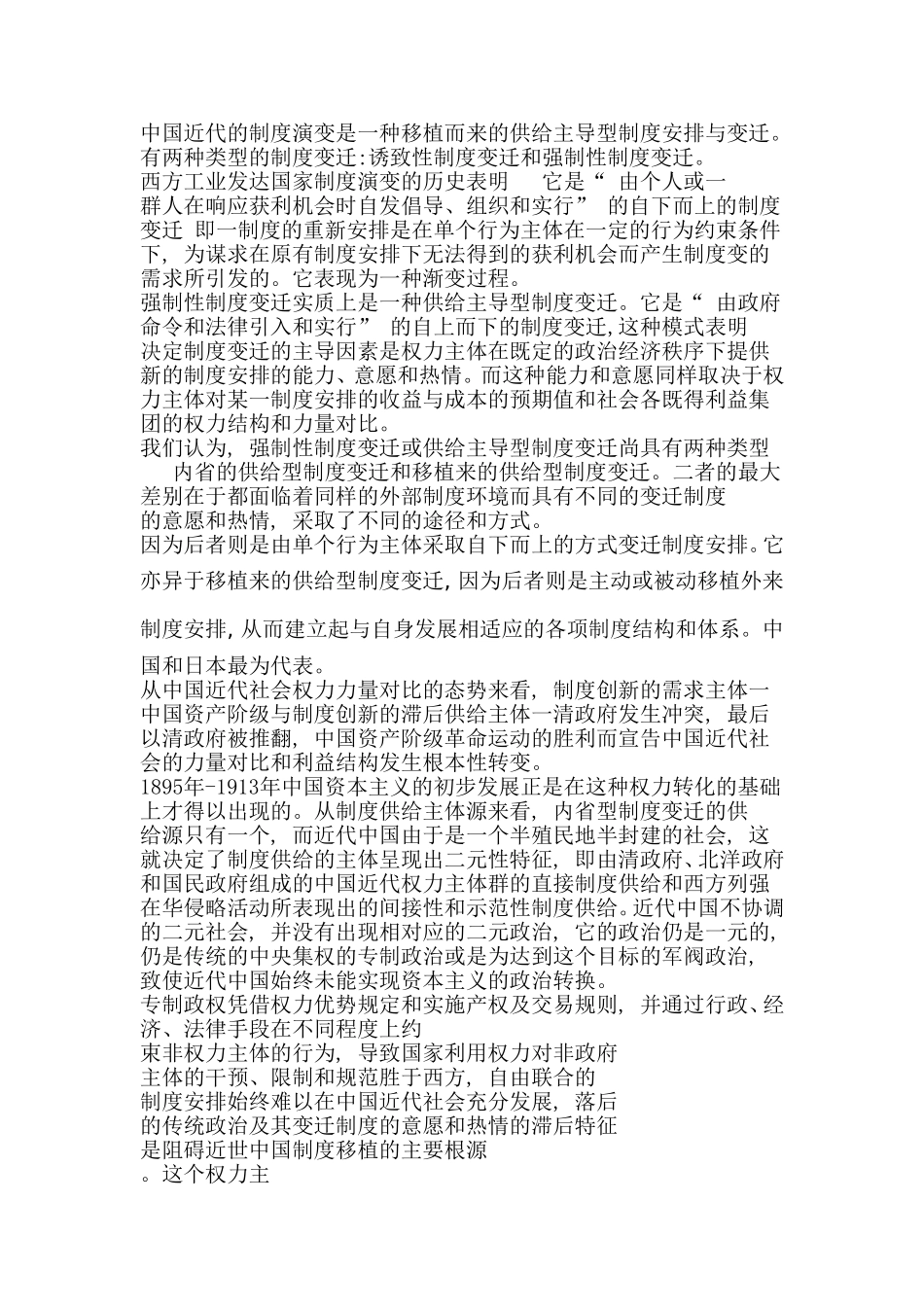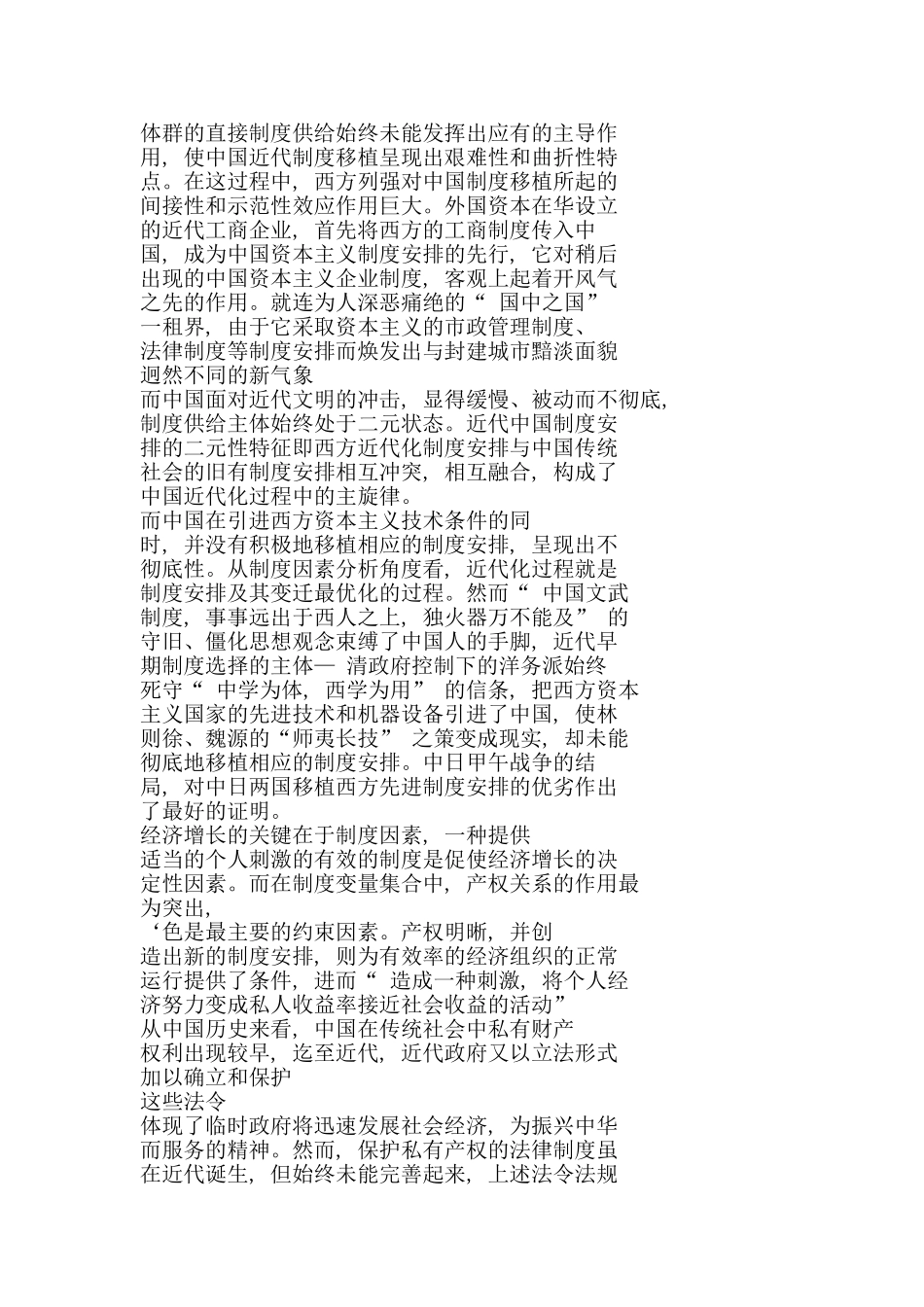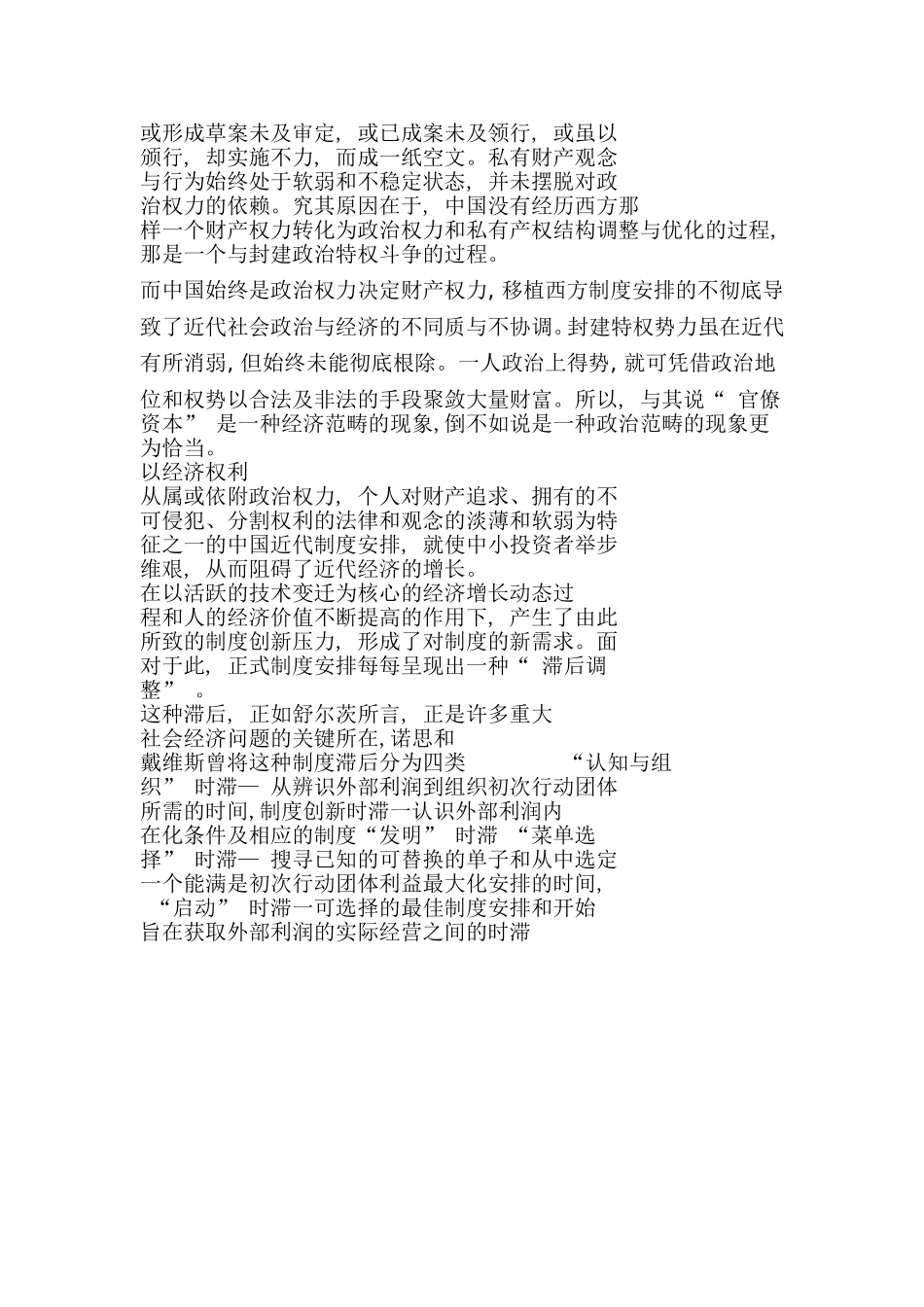中国近代的制度演变是一种移植而来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安排与变迁。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制度演变的历史表明它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即一制度的重新安排是在单个行为主体在一定的行为约束条件下,为谋求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而产生制度变的需求所引发的。它表现为一种渐变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实质上是一种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它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这种模式表明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是权力主体在既定的政治经济秩序下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意愿和热情。而这种能力和意愿同样取决于权力主体对某一制度安排的收益与成本的预期值和社会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我们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或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尚具有两种类型内省的供给型制度变迁和移植来的供给型制度变迁。二者的最大差别在于都面临着同样的外部制度环境而具有不同的变迁制度的意愿和热情,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因为后者则是由单个行为主体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变迁制度安排。它亦异于移植来的供给型制度变迁,因为后者则是主动或被动移植外来制度安排,从而建立起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结构和体系。中国和日本最为代表。从中国近代社会权力力量对比的态势来看,制度创新的需求主体一中国资产阶级与制度创新的滞后供给主体一清政府发生冲突,最后以清政府被推翻,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而宣告中国近代社会的力量对比和利益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1895年-1913年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正是在这种权力转化的基础上才得以出现的。从制度供给主体源来看,内省型制度变迁的供给源只有一个,而近代中国由于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决定了制度供给的主体呈现出二元性特征,即由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组成的中国近代权力主体群的直接制度供给和西方列强在华侵略活动所表现出的间接性和示范性制度供给。近代中国不协调的二元社会,并没有出现相对应的二元政治,它的政治仍是一元的,仍是传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或是为达到这个目标的军阀政治,致使近代中国始终未能实现资本主义的政治转换。专制政权凭借权力优势规定和实施产权及交易规则,并通过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非权力主体的行为,导致国家利用权力对非政府主体的干预、限制和规范胜于西方,自由联合的制度安排始终难以在中国近代社会充分发展,落后的传统政治及其变迁制度的意愿和热情的滞后特征是阻碍近世中国制度移植的主要根源。这个权力主体群的直接制度供给始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主导作用,使中国近代制度移植呈现出艰难性和曲折性特点。在这过程中,西方列强对中国制度移植所起的间接性和示范性效应作用巨大。外国资本在华设立的近代工商企业,首先将西方的工商制度传入中国,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制度安排的先行,它对稍后出现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客观上起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就连为人深恶痛绝的“国中之国”一租界,由于它采取资本主义的市政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安排而焕发出与封建城市黯淡面貌迥然不同的新气象而中国面对近代文明的冲击,显得缓慢、被动而不彻底,制度供给主体始终处于二元状态。近代中国制度安排的二元性特征即西方近代化制度安排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旧有制度安排相互冲突,相互融合,构成了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主旋律。而中国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技术条件的同时,并没有积极地移植相应的制度安排,呈现出不彻底性。从制度因素分析角度看,近代化过程就是制度安排及其变迁最优化的过程。然而“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的守旧、僵化思想观念束缚了中国人的手脚,近代早期制度选择的主体—清政府控制下的洋务派始终死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条,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引进了中国,使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之策变成现实,却未能彻底地移植相应的制度安排。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日两国移植西方先进制度安排的优劣作出了最好的证明。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