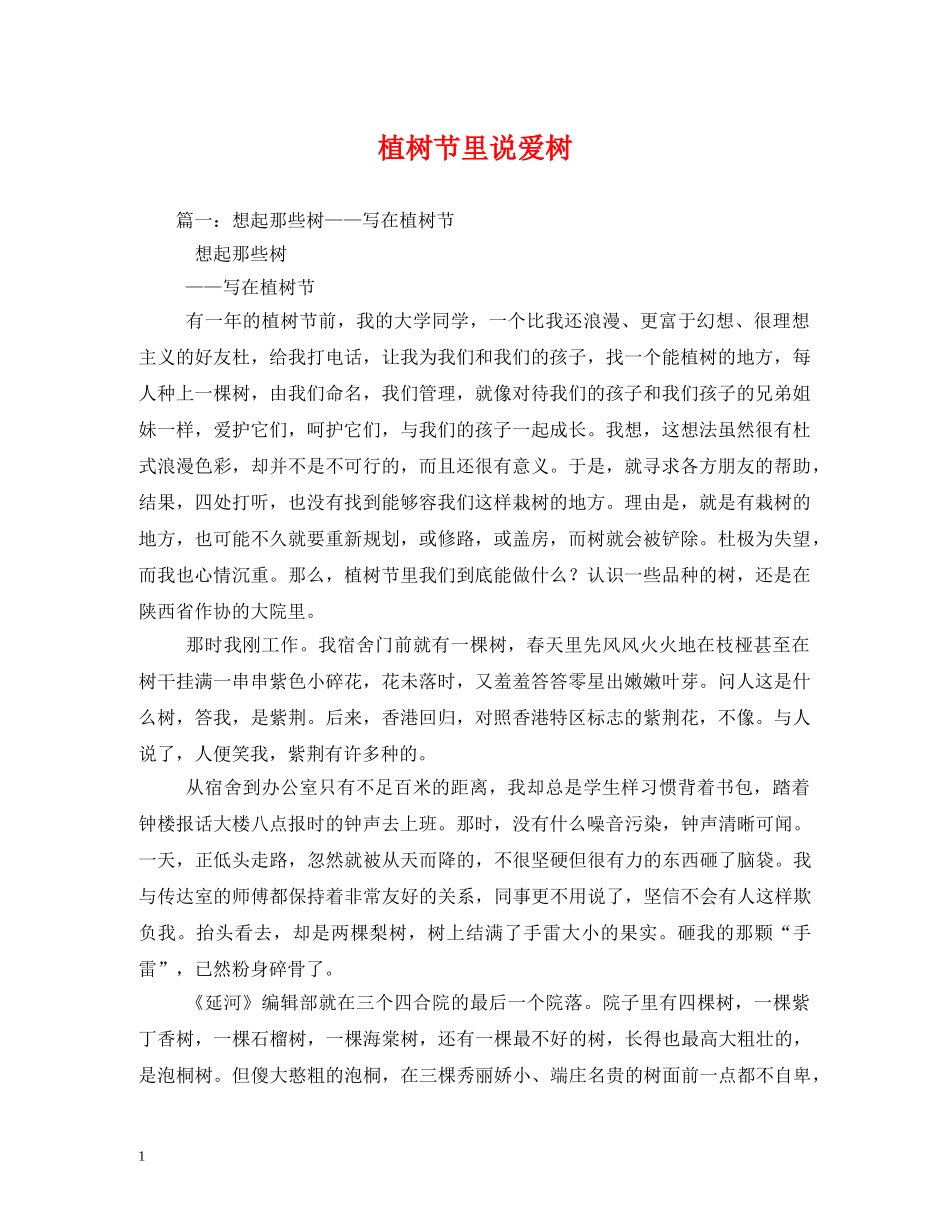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植树节里说爱树篇一:想起那些树——写在植树节想起那些树——写在植树节有一年的植树节前,我的大学同学,一个比我还浪漫、更富于幻想、很理想主义的好友杜,给我打电话,让我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找一个能植树的地方,每人种上一棵树,由我们命名,我们管理,就像对待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的兄弟姐妹一样,爱护它们,呵护它们,与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我想,这想法虽然很有杜式浪漫色彩,却并不是不可行的,而且还很有意义。于是,就寻求各方朋友的帮助,结果,四处打听,也没有找到能够容我们这样栽树的地方。理由是,就是有栽树的地方,也可能不久就要重新规划,或修路,或盖房,而树就会被铲除。杜极为失望,而我也心情沉重。那么,植树节里我们到底能做什么?认识一些品种的树,还是在陕西省作协的大院里。那时我刚工作。我宿舍门前就有一棵树,春天里先风风火火地在枝桠甚至在树干挂满一串串紫色小碎花,花未落时,又羞羞答答零星出嫩嫩叶芽。问人这是什么树,答我,是紫荆。后来,香港回归,对照香港特区标志的紫荆花,不像。与人说了,人便笑我,紫荆有许多种的。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不足百米的距离,我却总是学生样习惯背着书包,踏着钟楼报话大楼八点报时的钟声去上班。那时,没有什么噪音污染,钟声清晰可闻。一天,正低头走路,忽然就被从天而降的,不很坚硬但很有力的东西砸了脑袋。我与传达室的师傅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同事更不用说了,坚信不会有人这样欺负我。抬头看去,却是两棵梨树,树上结满了手雷大小的果实。砸我的那颗“手雷”,已然粉身碎骨了。《延河》编辑部就在三个四合院的最后一个院落。院子里有四棵树,一棵紫丁香树,一棵石榴树,一棵海棠树,还有一棵最不好的树,长得也最高大粗壮的,是泡桐树。但傻大憨粗的泡桐,在三棵秀丽娇小、端庄名贵的树面前一点都不自卑,1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春天里我行我素地开着淡紫色的大喇叭花,之后又劈劈啪啪地将一个个指肚大小的果实砸在人的身上,砸在院子里。一阵秋风起,又将它那肥大的树叶落满了院子。早晨上班来第一件事,就是和编辑部的人一起清扫泡桐的花朵,泡桐的果实,泡桐的树叶。我们一年四季都为这棵泡桐树忙乎,但是我们从不嫌弃抱怨它。因为就是这棵最普通的泡桐树,使夏季的院子阴凉了许多,我们常在荫凉下,闻着海棠花、紫丁香花的清香,打克朗棋,开编前会,畅谈着文坛情况,作家的创作,以及刊用稿子的各自意见。一年的夏天,奇热无比。主编白描家养的一只小狗终究耐不住酷暑而死去,白主编将小狗葬在了那棵海棠树下。第二年的春天,海棠花开得非常繁盛,灿烂了满枝头,枝叶也浓绿浓绿的,令人不禁想起那个曾经活泼可爱的小生命。中间那个院子是《小说评论》和创联部的办公院,院子里有一棵枝杈非常多的腊梅树,几乎占据了院子的三分之一。有许多枝杈都快伸进了办公室的窗子里,但是没有人随意折断它,即使是它傲雪盛开的时节,人们只是驻足欣赏品味。到了秋天,腊梅树上结出许多的硬壳种子,待这些种子成熟了,美编郑文华会拾起一些,种在花盆里,竟神奇般地长出小苗苗来。1996年之后整个作协大院改造,所有的树,铲掉的铲掉,移栽的移栽,但移栽的也都没有存活下来。郑文华就将花盆中的腊梅移栽到前院狭小的空地上。我也从一同事那里移栽了一棵,种在另一小块地里。每天上班时,都要去看望它们的长势。眼看它们又茁壮成长起来,突然有一天,又莫名地被铲除了。看着那一小块它生活过的地方,我伤心地发呆很久。不想去追究谁是刽子手,生命对于树来说也只有一次。它们没有能力和人讲它们的生存权,它们也没有任何树权,生存权和树权在人权那里实在算不了什么。况且,即使追究也无法挽回它的生命。中间院落的另外一棵树是白玉兰。白玉兰在它开花时,总让我无法面对它冰清玉洁灵慧聪明的美丽。上大学时,西北大学校长办公楼,也就是当时称作的红楼前,就有一棵清秀挺拔的白玉兰。那时,我和许多青春期的女孩一样,甚至我更加幼稚和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