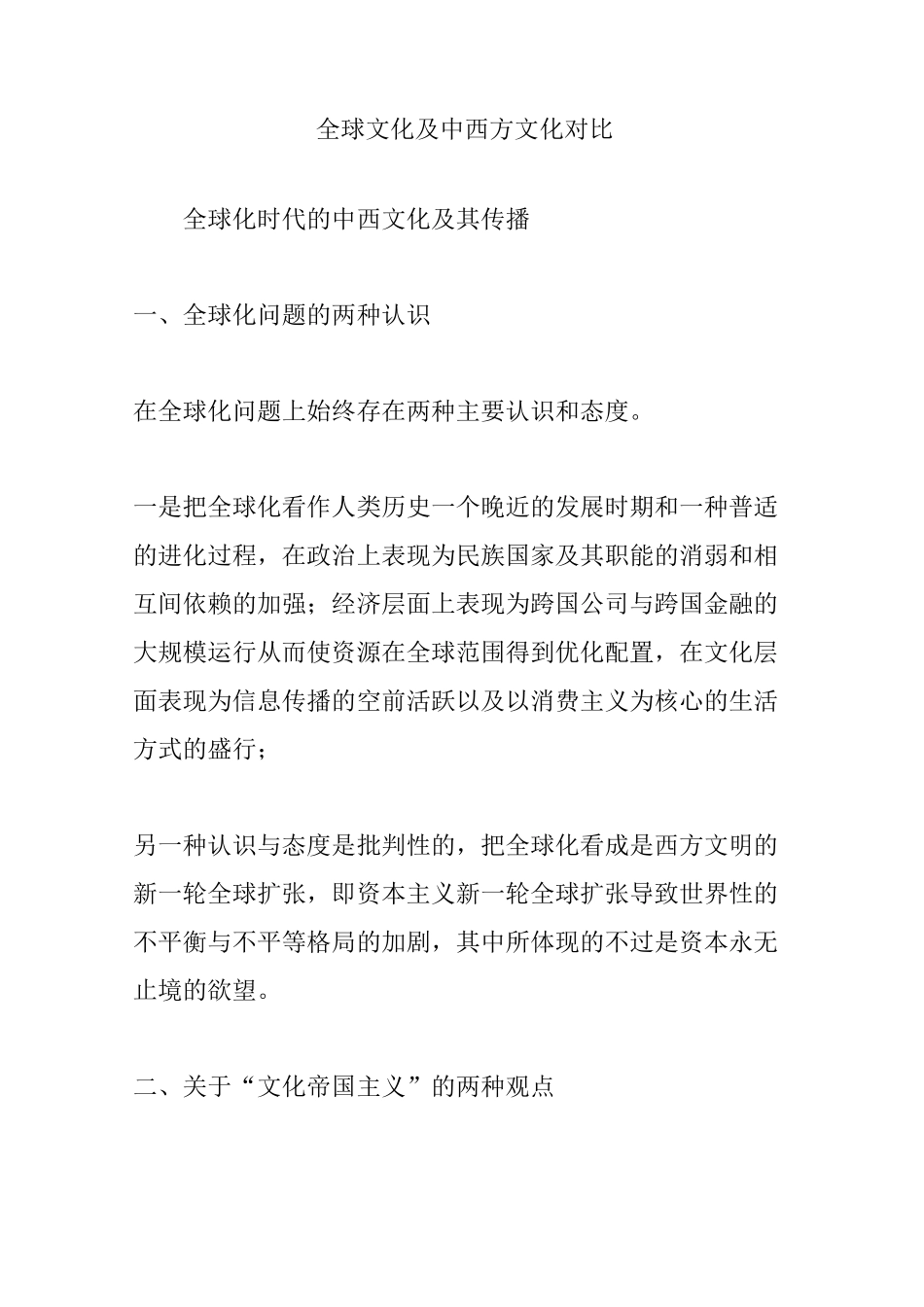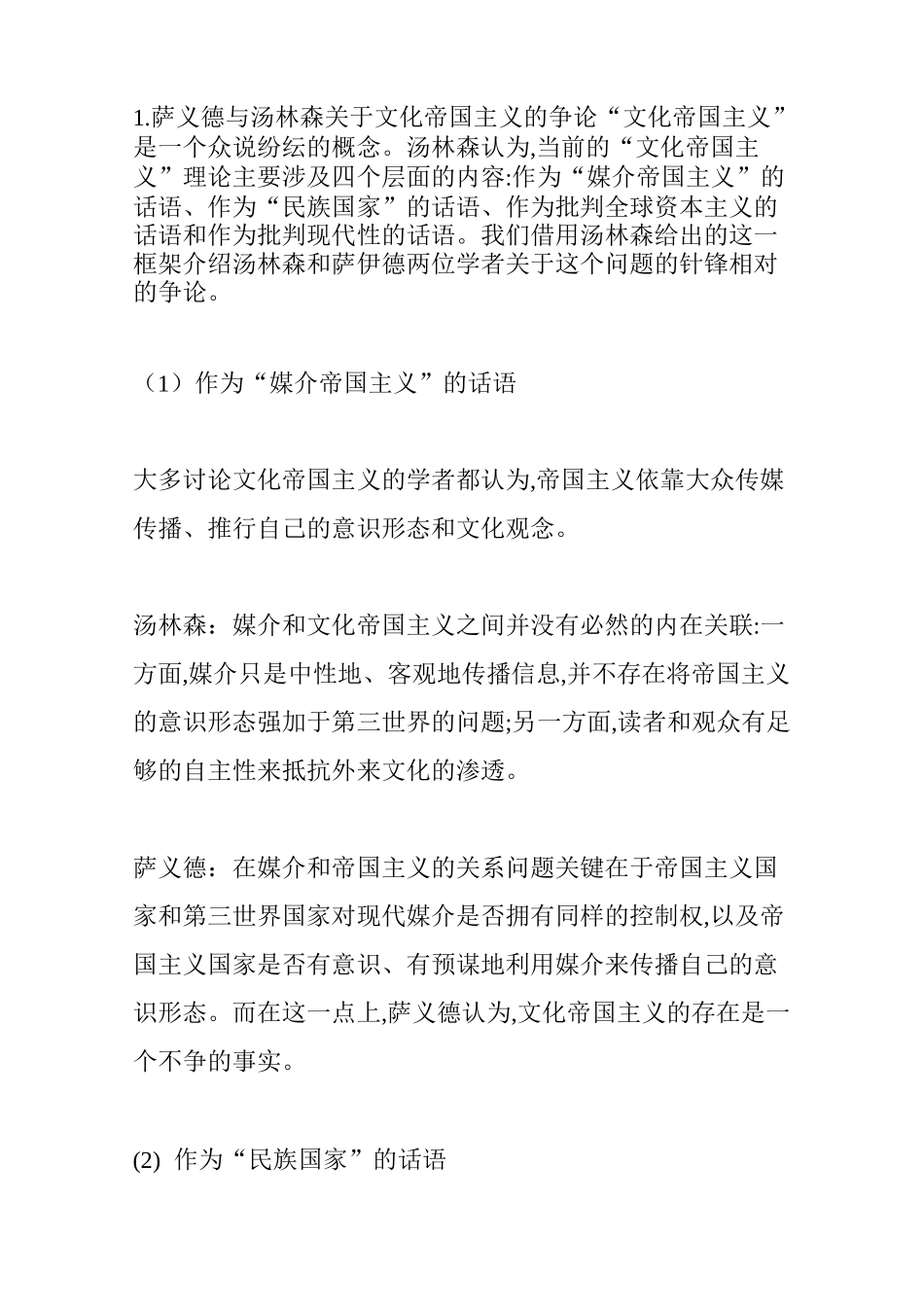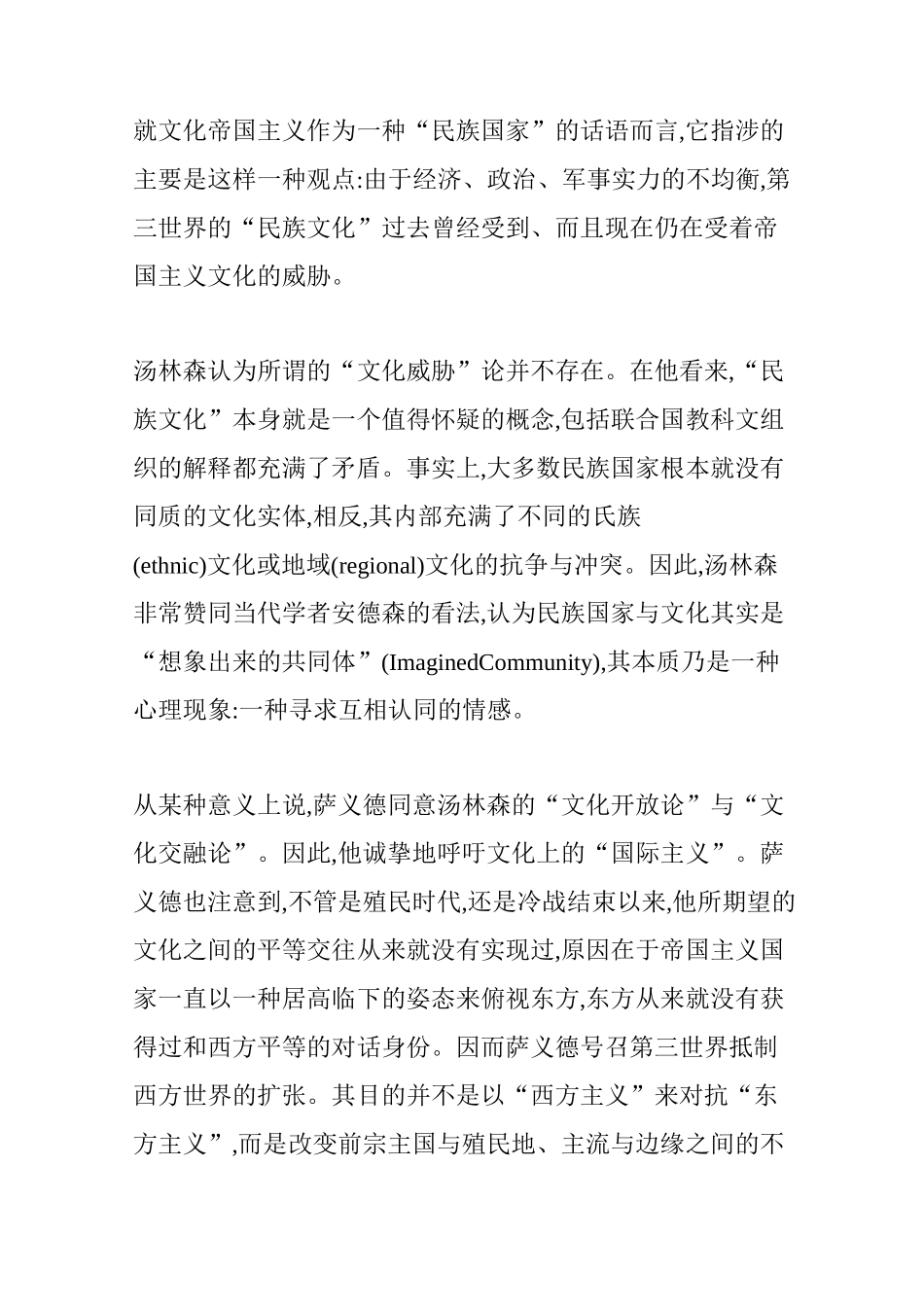全球文化及中西方文化对比全球化时代的中西文化及其传播一、全球化问题的两种认识在全球化问题上始终存在两种主要认识和态度。一是把全球化看作人类历史一个晚近的发展时期和一种普适的进化过程,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及其职能的消弱和相互间依赖的加强;经济层面上表现为跨国公司与跨国金融的大规模运行从而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得到优化配置,在文化层面表现为信息传播的空前活跃以及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生活方式的盛行;另一种认识与态度是批判性的,把全球化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新一轮全球扩张,即资本主义新一轮全球扩张导致世界性的不平衡与不平等格局的加剧,其中所体现的不过是资本永无止境的欲望。二、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两种观点1.萨义德与汤林森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汤林森认为,当前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主要涉及四个层面的内容: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和作为批判现代性的话语。我们借用汤林森给出的这一框架介绍汤林森和萨伊德两位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针锋相对的争论。(1)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大多讨论文化帝国主义的学者都认为,帝国主义依靠大众传媒传播、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汤林森: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关联:一方面,媒介只是中性地、客观地传播信息,并不存在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于第三世界的问题;另一方面,读者和观众有足够的自主性来抵抗外来文化的渗透。萨义德:在媒介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对现代媒介是否拥有同样的控制权,以及帝国主义国家是否有意识、有预谋地利用媒介来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点上,萨义德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就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国家”的话语而言,它指涉的主要是这样一种观点:由于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不均衡,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过去曾经受到、而且现在仍在受着帝国主义文化的威胁。汤林森认为所谓的“文化威胁”论并不存在。在他看来,“民族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概念,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解释都充满了矛盾。事实上,大多数民族国家根本就没有同质的文化实体,相反,其内部充满了不同的氏族(ethnic)文化或地域(regional)文化的抗争与冲突。因此,汤林森非常赞同当代学者安德森的看法,认为民族国家与文化其实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y),其本质乃是一种心理现象:一种寻求互相认同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萨义德同意汤林森的“文化开放论”与“文化交融论”。因此,他诚挚地呼吁文化上的“国际主义”。萨义德也注意到,不管是殖民时代,还是冷战结束以来,他所期望的文化之间的平等交往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国家一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俯视东方,东方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和西方平等的对话身份。因而萨义德号召第三世界抵制西方世界的扩张。其目的并不是以“西方主义”来对抗“东方主义”,而是改变前宗主国与殖民地、主流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3)、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汤林森主要反驳了一种功能论的说法: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先锋,其目的是通过文化层面的“同质化”,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在他看来,上述理论的错误首先在于颠倒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经济决定文化而不是相反,只有在人类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物质基础得到建立后才有“文化”可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不可能是经济的先锋。其次,如果是文化社群自觉、自主地选择了资本主义,那么即使资本主义的确带来了文化同质化的后果,那么也没有理由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萨义德:汤林森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自主性,萨义德却正好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从一开始就是以文化的扩张为条件的。萨义德主要考察了欧美“东方学”的产生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内在关系。欧洲的东方学研究一直与欧洲诸国此消彼长的斗争有关。萨义德还注意到,在整个殖民时代,西方世界许多“高尚”的文化现象都打上了帝国主义的印记,有时这些印记是暗藏着的。所以他强调“对位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