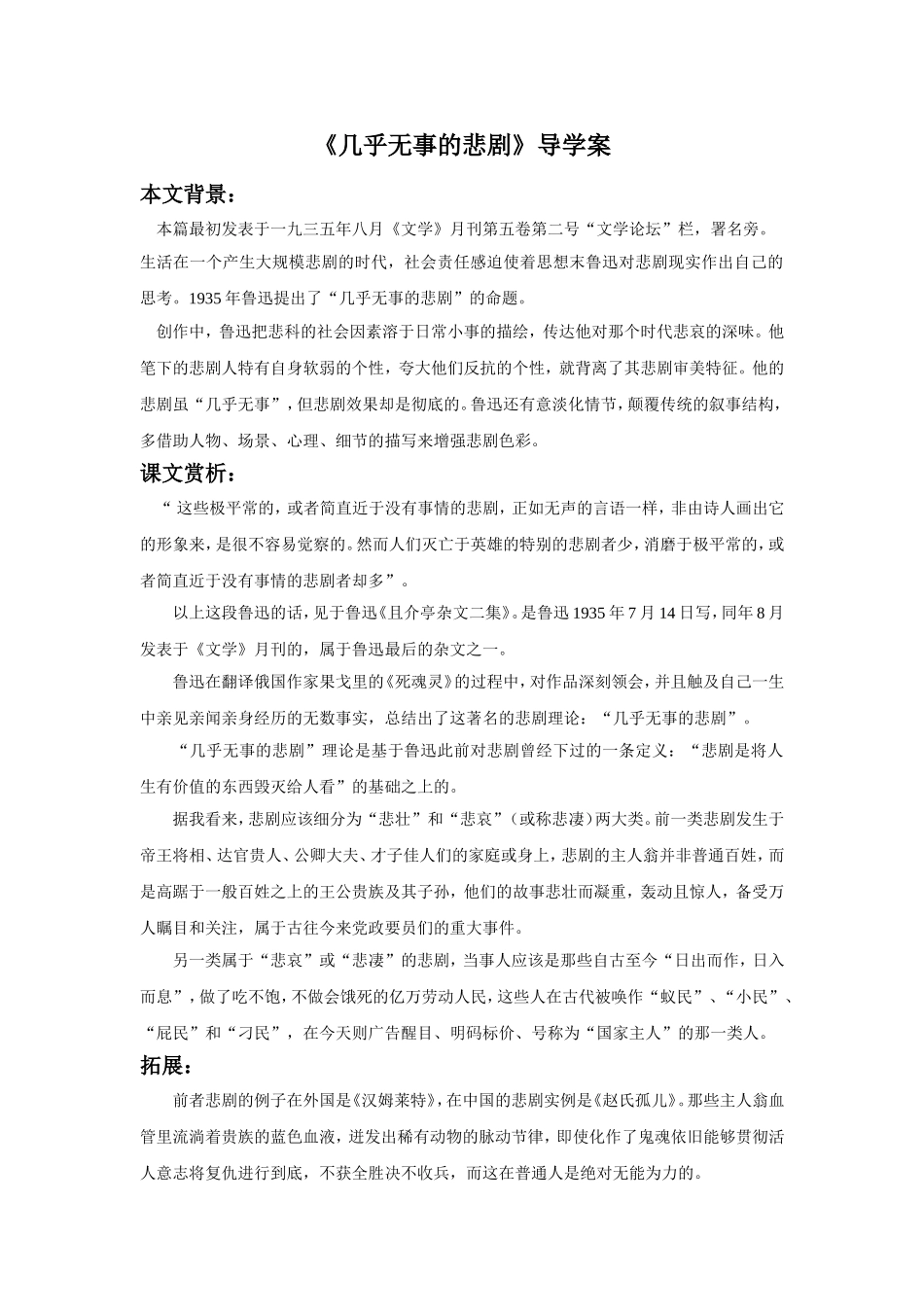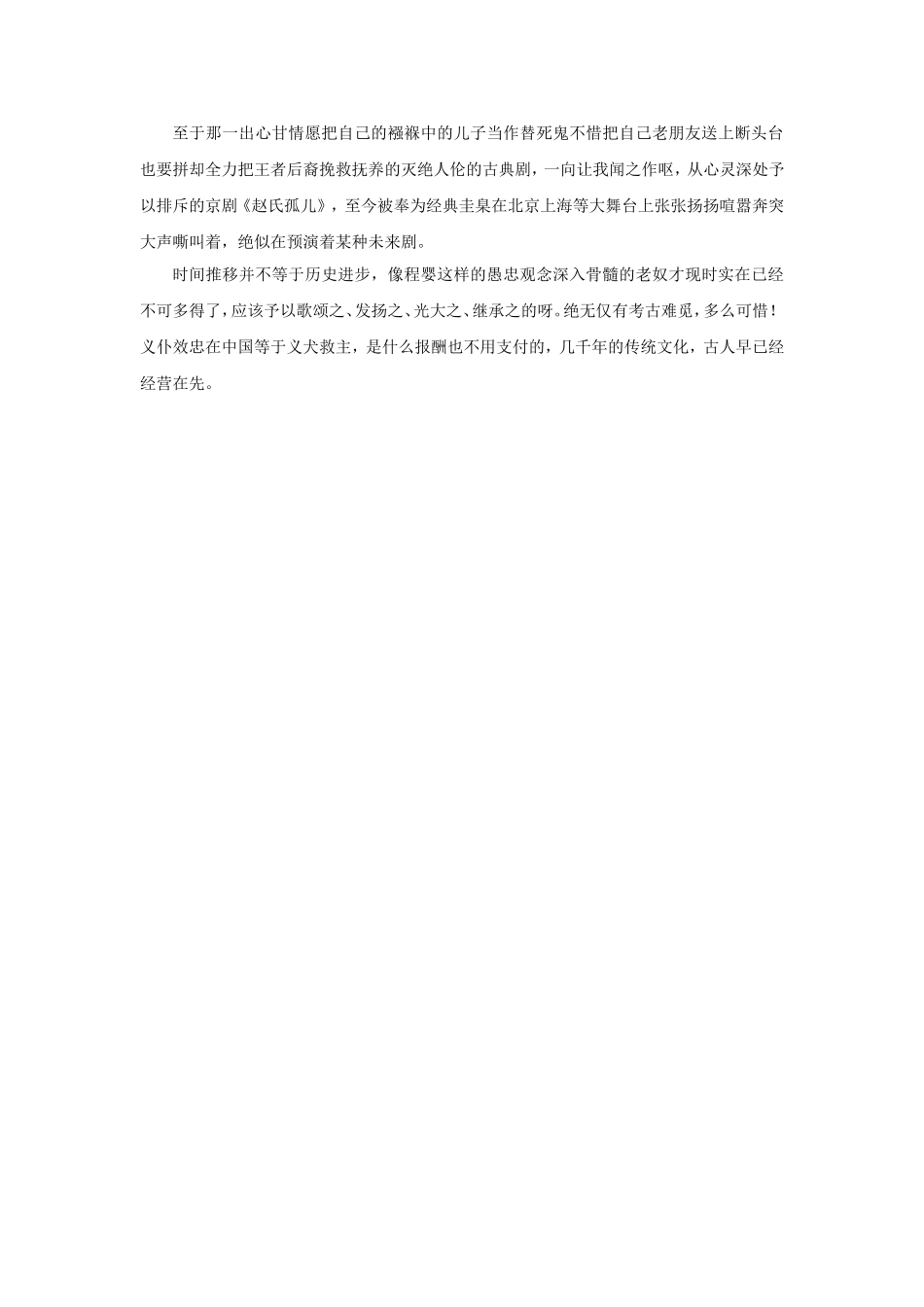《几乎无事的悲剧》导学案本文背景: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旁。生活在一个产生大规模悲剧的时代,社会责任感迫使着思想末鲁迅对悲剧现实作出自己的思考。1935年鲁迅提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的命题。创作中,鲁迅把悲科的社会因素溶于日常小事的描绘,传达他对那个时代悲哀的深味。他笔下的悲剧人特有自身软弱的个性,夸大他们反抗的个性,就背离了其悲剧审美特征。他的悲剧虽“几乎无事”,但悲剧效果却是彻底的。鲁迅还有意淡化情节,颠覆传统的叙事结构,多借助人物、场景、心理、细节的描写来增强悲剧色彩。课文赏析:“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以上这段鲁迅的话,见于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是鲁迅1935年7月14日写,同年8月发表于《文学》月刊的,属于鲁迅最后的杂文之一。鲁迅在翻译俄国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的过程中,对作品深刻领会,并且触及自己一生中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无数事实,总结出了这著名的悲剧理论:“几乎无事的悲剧”。“几乎无事的悲剧”理论是基于鲁迅此前对悲剧曾经下过的一条定义:“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基础之上的。据我看来,悲剧应该细分为“悲壮”和“悲哀”(或称悲凄)两大类。前一类悲剧发生于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公卿大夫、才子佳人们的家庭或身上,悲剧的主人翁并非普通百姓,而是高踞于一般百姓之上的王公贵族及其子孙,他们的故事悲壮而凝重,轰动且惊人,备受万人瞩目和关注,属于古往今来党政要员们的重大事件。另一类属于“悲哀”或“悲凄”的悲剧,当事人应该是那些自古至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做了吃不饱,不做会饿死的亿万劳动人民,这些人在古代被唤作“蚁民”、“小民”、“屁民”和“刁民”,在今天则广告醒目、明码标价、号称为“国家主人”的那一类人。拓展:前者悲剧的例子在外国是《汉姆莱特》,在中国的悲剧实例是《赵氏孤儿》。那些主人翁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蓝色血液,迸发出稀有动物的脉动节律,即使化作了鬼魂依旧能够贯彻活人意志将复仇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而这在普通人是绝对无能为力的。至于那一出心甘情愿把自己的襁褓中的儿子当作替死鬼不惜把自己老朋友送上断头台也要拼却全力把王者后裔挽救抚养的灭绝人伦的古典剧,一向让我闻之作呕,从心灵深处予以排斥的京剧《赵氏孤儿》,至今被奉为经典圭臬在北京上海等大舞台上张张扬扬喧嚣奔突大声嘶叫着,绝似在预演着某种未来剧。时间推移并不等于历史进步,像程婴这样的愚忠观念深入骨髓的老奴才现时实在已经不可多得了,应该予以歌颂之、发扬之、光大之、继承之的呀。绝无仅有考古难觅,多么可惜!义仆效忠在中国等于义犬救主,是什么报酬也不用支付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古人早已经经营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