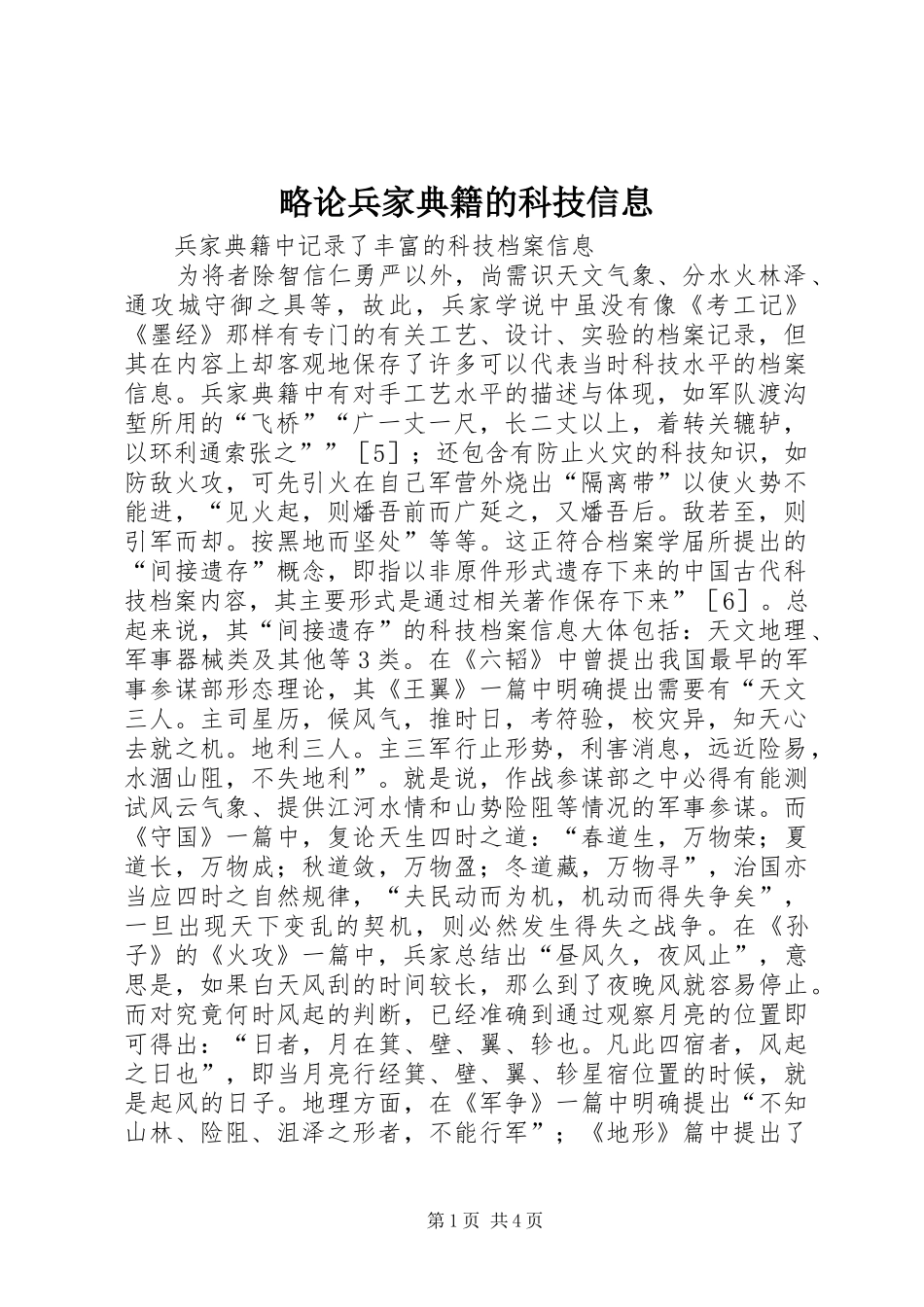略论兵家典籍的科技信息兵家典籍中记录了丰富的科技档案信息为将者除智信仁勇严以外,尚需识天文气象、分水火林泽、通攻城守御之具等,故此,兵家学说中虽没有像《考工记》《墨经》那样有专门的有关工艺、设计、实验的档案记录,但其在内容上却客观地保存了许多可以代表当时科技水平的档案信息。兵家典籍中有对手工艺水平的描述与体现,如军队渡沟堑所用的“飞桥”“广一丈一尺,长二丈以上,着转关辘轳,以环利通索张之””[5];还包含有防止火灾的科技知识,如防敌火攻,可先引火在自己军营外烧出“隔离带”以使火势不能进,“见火起,则燔吾前而广延之,又燔吾后。敌若至,则引军而却。按黑地而坚处”等等。这正符合档案学届所提出的“间接遗存”概念,即指以非原件形式遗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科技档案内容,其主要形式是通过相关著作保存下来”[6]。总起来说,其“间接遗存”的科技档案信息大体包括:天文地理、军事器械类及其他等3类。在《六韬》中曾提出我国最早的军事参谋部形态理论,其《王翼》一篇中明确提出需要有“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天心去就之机。地利三人。主三军行止形势,利害消息,远近险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就是说,作战参谋部之中必得有能测试风云气象、提供江河水情和山势险阻等情况的军事参谋。而《守国》一篇中,复论天生四时之道:“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万物盈;冬道藏,万物寻”,治国亦当应四时之自然规律,“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一旦出现天下变乱的契机,则必然发生得失之战争。在《孙子》的《火攻》一篇中,兵家总结出“昼风久,夜风止”,意思是,如果白天风刮的时间较长,那么到了夜晚风就容易停止。而对究竟何时风起的判断,已经准确到通过观察月亮的位置即可得出:“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即当月亮行经箕、壁、翼、轸星宿位置的时候,就是起风的日子。地理方面,在《军争》一篇中明确提出“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地形》篇中提出了第1页共4页“夫地形者,兵之助也”;《九地》一篇中,更细致地根据用兵原理,将兵要地理区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九类,并分别做出较详细的解释。这种对天文、地理经验的总结,无疑蕴含着科技档案信息,体现了当时的科技水平。在《吴子》中,当武侯问三军行止之道时,吴子亦提出军队行止需要“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这是对地理形态的判断;而将接战之时,面对不同的气候,需要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审候风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陈以待之”,可见风从哪个方向吹来对作战方式有不同的影响;若欲引水攻敌,要能判断出敌军“居军下湿”,若欲引火攻敌,需判断出敌军“居军荒泽,草楚幽秽”。此外,在《应变》一篇中,对于水战、谷战、雨中泥泞之战都有不同的分析与描述。比如在《司马法》中提到,“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无戎,先良也”,分别对夏朝、殷朝、周朝的战车做出了描述,还记载了这三个朝代战车不同的手工艺特点。《孙子》的《作战》一篇中,也提出了“驰车”与“革车”的区别;而若欲火攻,则“烟火必素具”;在“十万之师举矣”的前提条件中,明确指出“胶漆之材”之必备;《谋攻》一篇中,“修橹偾韫,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这指的是,上兵伐谋其下攻城,攻城之时,要制造攻城的大盾和四轮的大车等。《李卫公问对》中,记载了姜太公创制铁蒺藜和行马等用来防御敌人的工具。而《六韬》中有专门的《农器》篇,描述作战时用于攻占守御的武装器械,它们实际上全是百姓日常的生产生活用具。如耕作用的“耒耜”,可以用作拒马“;马、牛、车、舆者”,可以用为营垒蔽橹的屏障器材;“锸、斧、锯、杵臼”等可用为攻城器械;人们在日常劳作中用于平整土地的技术———“平壤”,可用于攻城作业;春季农民“拨草棘”之法,可用作同敌人车兵、骑兵作战的手段;夏季农民“耨田畴”之法,可用为同敌人步兵作战的手段等等。其《阴符》、《阴书》二篇中,详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