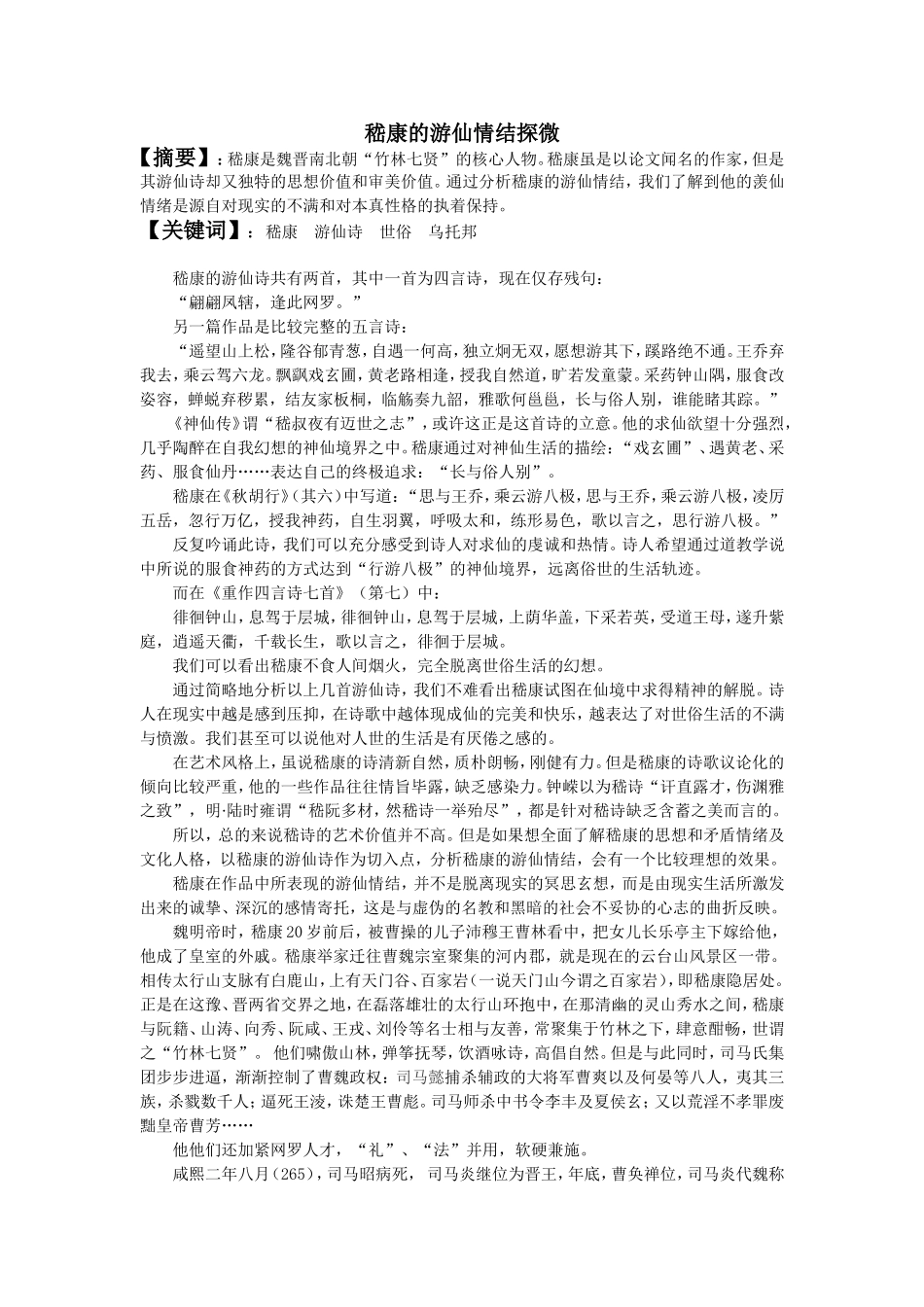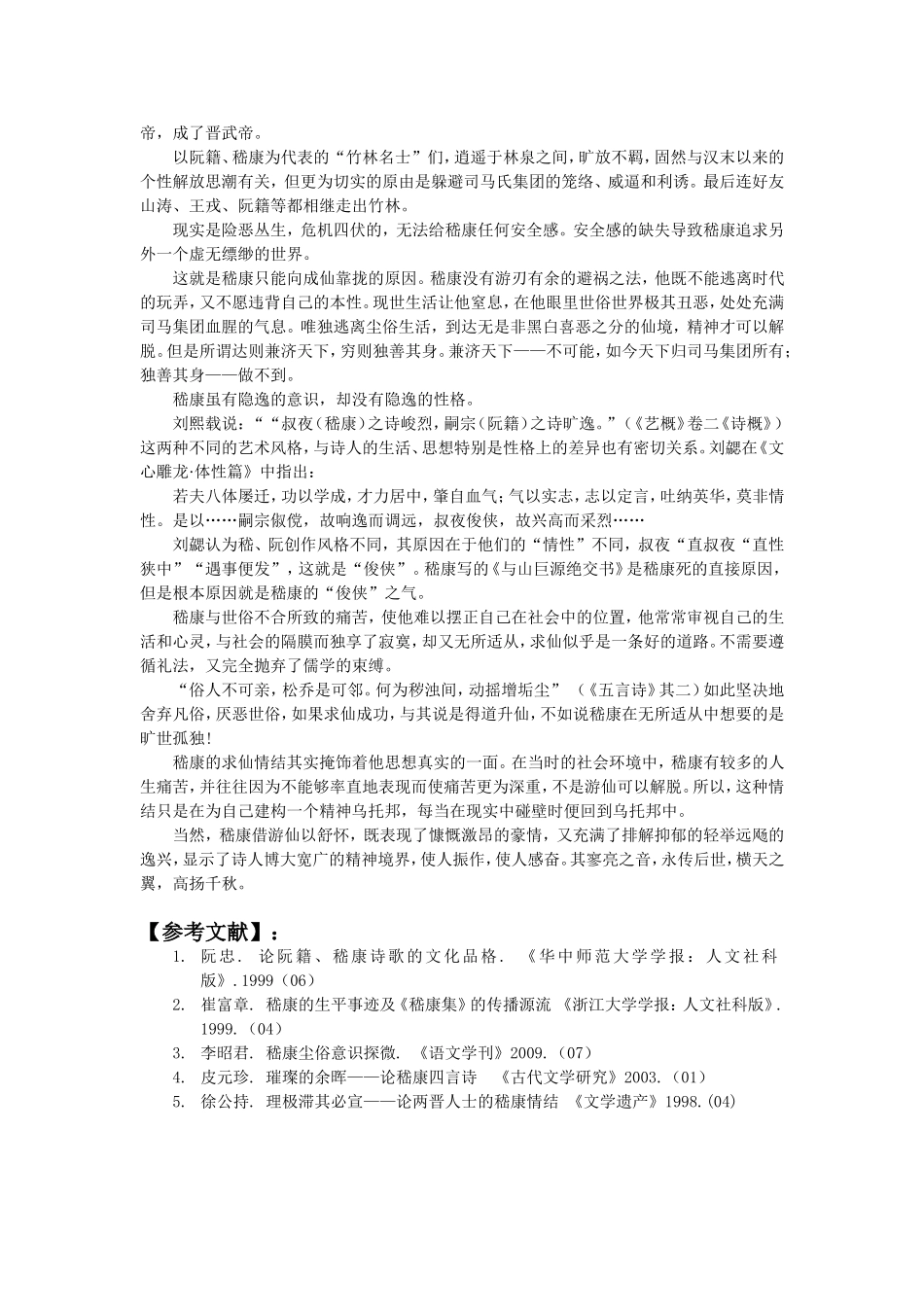嵇康的游仙情结探微【摘要】:嵇康是魏晋南北朝“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嵇康虽是以论文闻名的作家,但是其游仙诗却又独特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通过分析嵇康的游仙情结,我们了解到他的羡仙情绪是源自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本真性格的执着保持。【关键词】:嵇康游仙诗世俗乌托邦嵇康的游仙诗共有两首,其中一首为四言诗,现在仅存残句:“翩翩凤辖,逢此网罗。”另一篇作品是比较完整的五言诗:“遥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葱,自遇一何高,独立炯无双,愿想游其下,蹊路绝不通。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飘飖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桐,临觞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神仙传》谓“嵇叔夜有迈世之志”,或许这正是这首诗的立意。他的求仙欲望十分强烈,几乎陶醉在自我幻想的神仙境界之中。嵇康通过对神仙生活的描绘:“戏玄圃”、遇黄老、采药、服食仙丹……表达自己的终极追求:“长与俗人别”。嵇康在《秋胡行》(其六)中写道:“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凌厉五岳,忽行万亿,授我神药,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练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游八极。”反复吟诵此诗,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诗人对求仙的虔诚和热情。诗人希望通过道教学说中所说的服食神药的方式达到“行游八极”的神仙境界,远离俗世的生活轨迹。而在《重作四言诗七首》(第七)中:徘徊钟山,息驾于层城,徘徊钟山,息驾于层城,上荫华盖,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遥天衢,千载长生,歌以言之,徘徊于层城。我们可以看出嵇康不食人间烟火,完全脱离世俗生活的幻想。通过简略地分析以上几首游仙诗,我们不难看出嵇康试图在仙境中求得精神的解脱。诗人在现实中越是感到压抑,在诗歌中越体现成仙的完美和快乐,越表达了对世俗生活的不满与愤激。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对人世的生活是有厌倦之感的。在艺术风格上,虽说嵇康的诗清新自然,质朴朗畅,刚健有力。但是嵇康的诗歌议论化的倾向比较严重,他的一些作品往往情旨毕露,缺乏感染力。钟嵘以为嵇诗“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明·陆时雍谓“嵇阮多材,然嵇诗一举殆尽”,都是针对嵇诗缺乏含蓄之美而言的。所以,总的来说嵇诗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是如果想全面了解嵇康的思想和矛盾情绪及文化人格,以嵇康的游仙诗作为切入点,分析嵇康的游仙情结,会有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嵇康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游仙情结,并不是脱离现实的冥思玄想,而是由现实生活所激发出来的诚挚、深沉的感情寄托,这是与虚伪的名教和黑暗的社会不妥协的心志的曲折反映。魏明帝时,嵇康20岁前后,被曹操的儿子沛穆王曹林看中,把女儿长乐亭主下嫁给他,他成了皇室的外戚。嵇康举家迁往曹魏宗室聚集的河内郡,就是现在的云台山风景区一带。相传太行山支脉有白鹿山,上有天门谷、百家岩(一说天门山今谓之百家岩),即嵇康隐居处。正是在这豫、晋两省交界之地,在磊落雄壮的太行山环抱中,在那清幽的灵山秀水之间,嵇康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名士相与友善,常聚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之“竹林七贤”。他们啸傲山林,弹筝抚琴,饮酒咏诗,高倡自然。但是与此同时,司马氏集团步步进逼,渐渐控制了曹魏政权:司马懿捕杀辅政的大将军曹爽以及何晏等八人,夷其三族,杀戮数千人;逼死王淩,诛楚王曹彪。司马师杀中书令李丰及夏侯玄;又以荒淫不孝罪废黜皇帝曹芳……他他们还加紧网罗人才,“礼”、“法”并用,软硬兼施。咸熙二年八月(265),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位为晋王,年底,曹奂禅位,司马炎代魏称帝,成了晋武帝。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们,逍遥于林泉之间,旷放不羁,固然与汉末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有关,但更为切实的原由是躲避司马氏集团的笼络、威逼和利诱。最后连好友山涛、王戎、阮籍等都相继走出竹林。现实是险恶丛生,危机四伏的,无法给嵇康任何安全感。安全感的缺失导致嵇康追求另外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这就是嵇康只能向成仙靠拢的原因。嵇康没有游刃有余的避祸之法,他既不能逃离时代的玩弄,又不愿违背自己的本性。现世生活让他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