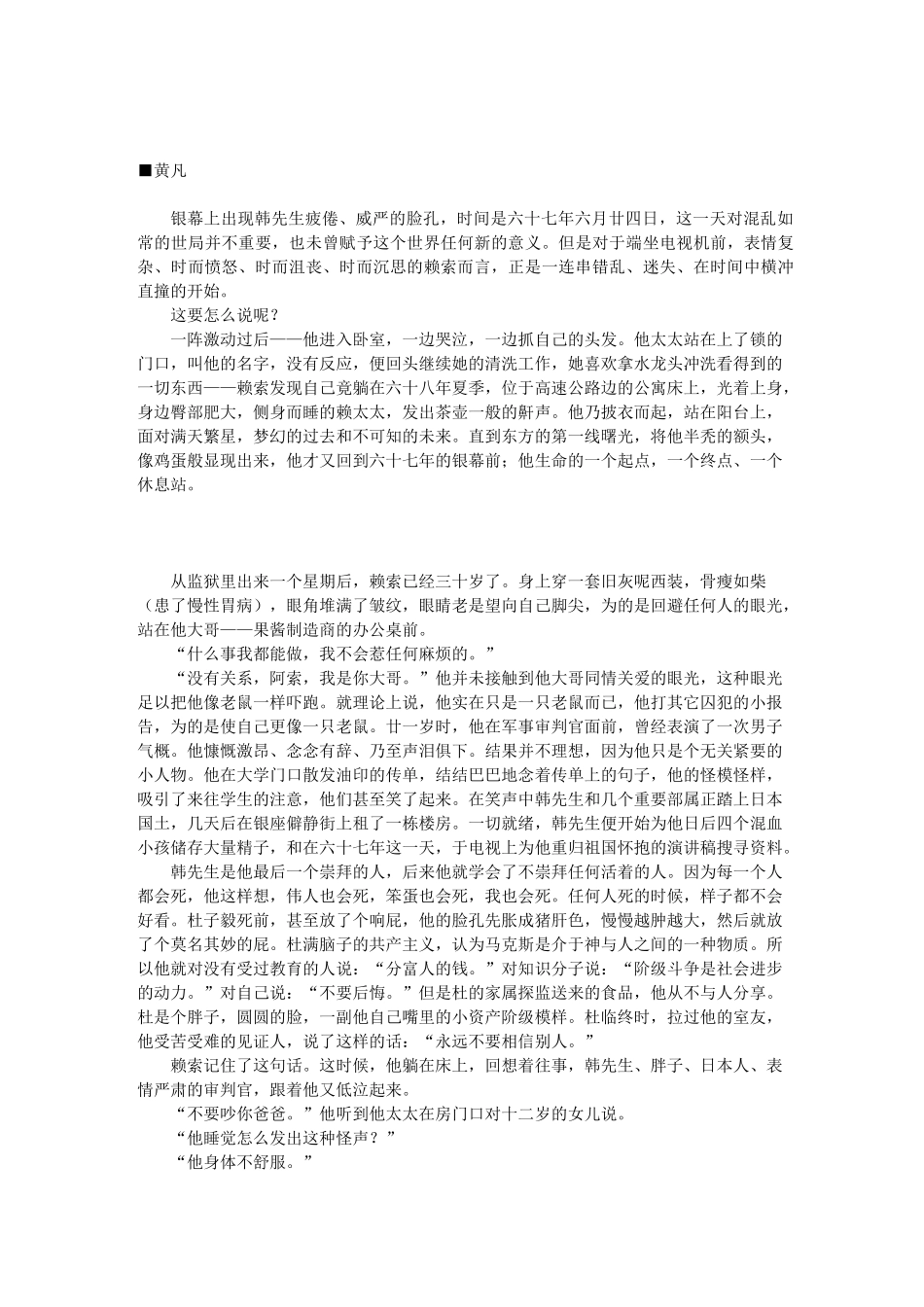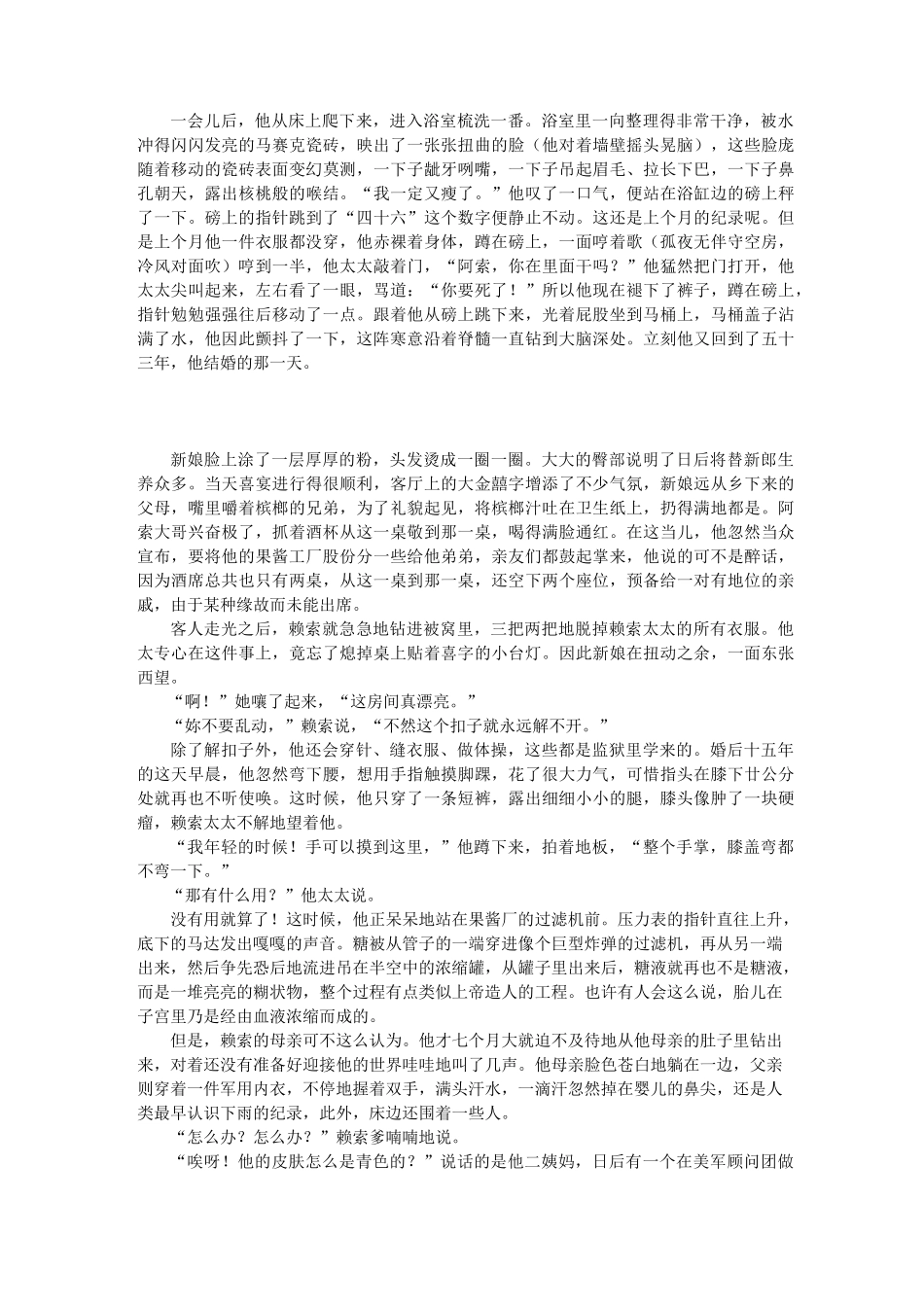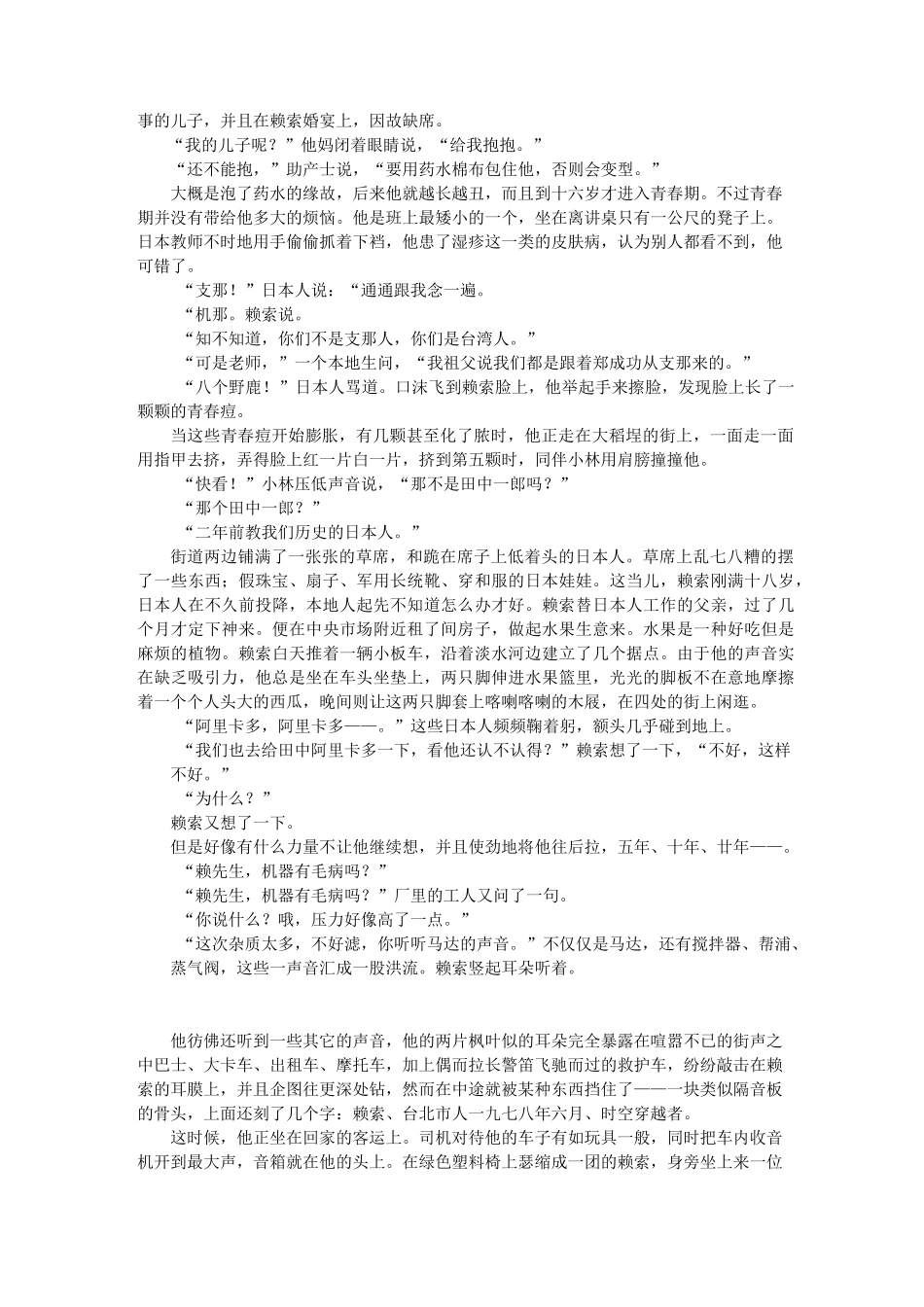■黄凡银幕上出现韩先生疲倦、威严的脸孔,时间是六十七年六月廿四日,这一天对混乱如常的世局并不重要,也未曾赋予这个世界任何新的意义。但是对于端坐电视机前,表情复杂、时而愤怒、时而沮丧、时而沉思的赖索而言,正是一连串错乱、迷失、在时间中横冲直撞的开始。这要怎么说呢?一阵激动过后——他进入卧室,一边哭泣,一边抓自己的头发。他太太站在上了锁的门口,叫他的名字,没有反应,便回头继续她的清洗工作,她喜欢拿水龙头冲洗看得到的一切东西——赖索发现自己竟躺在六十八年夏季,位于高速公路边的公寓床上,光着上身,身边臀部肥大,侧身而睡的赖太太,发出茶壶一般的鼾声。他乃披衣而起,站在阳台上,面对满天繁星,梦幻的过去和不可知的未来。直到东方的第一线曙光,将他半秃的额头,像鸡蛋般显现出来,他才又回到六十七年的银幕前;他生命的一个起点,一个终点、一个休息站。从监狱里出来一个星期后,赖索已经三十岁了。身上穿一套旧灰呢西装,骨瘦如柴(患了慢性胃病),眼角堆满了皱纹,眼睛老是望向自己脚尖,为的是回避任何人的眼光,站在他大哥——果酱制造商的办公桌前。“什么事我都能做,我不会惹任何麻烦的。”“没有关系,阿索,我是你大哥。”他并未接触到他大哥同情关爱的眼光,这种眼光足以把他像老鼠一样吓跑。就理论上说,他实在只是一只老鼠而已,他打其它囚犯的小报告,为的是使自己更像一只老鼠。廿一岁时,他在军事审判官面前,曾经表演了一次男子气概。他慷慨激昂、念念有辞、乃至声泪俱下。结果并不理想,因为他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他在大学门口散发油印的传单,结结巴巴地念着传单上的句子,他的怪模怪样,吸引了来往学生的注意,他们甚至笑了起来。在笑声中韩先生和几个重要部属正踏上日本国土,几天后在银座僻静街上租了一栋楼房。一切就绪,韩先生便开始为他日后四个混血小孩储存大量精子,和在六十七年这一天,于电视上为他重归祖国怀抱的演讲稿搜寻资料。韩先生是他最后一个崇拜的人,后来他就学会了不崇拜任何活着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死,他这样想,伟人也会死,笨蛋也会死,我也会死。任何人死的时候,样子都不会好看。杜子毅死前,甚至放了个响屁,他的脸孔先胀成猪肝色,慢慢越肿越大,然后就放了个莫名其妙的屁。杜满脑子的共产主义,认为马克斯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一种物质。所以他就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说:“分富人的钱。”对知识分子说:“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对自己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