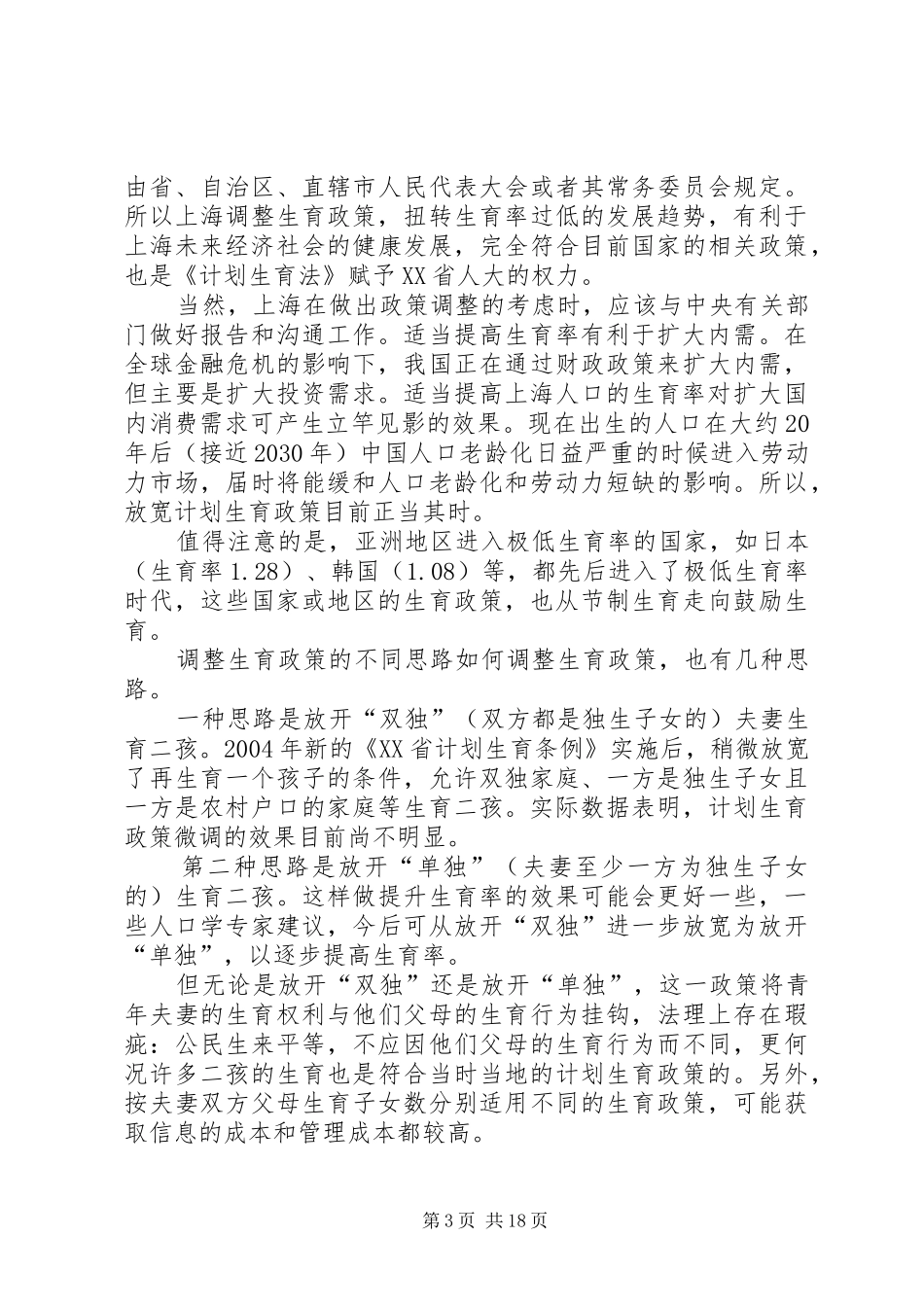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经过上世纪 50 年代的生育高峰以后,XX 省人口总和生育率(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下称“生育率”)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已降到 0.7~0.9,1993 年以来上海人口的自然变动已经连续多年负增长(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国际上将 2.1 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将 1.5 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将 1.3 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近年来 XX 省的生育率降低到 0.8 上下,可以说是“极低生育率”中的极低水平,应当引起我们对其人口学后果和经济社会后果的关注。 上海的生育率下降是影响生育的经济社会变化和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孩子的成本(尤其是照料、住房、医疗、教育等成本)和机会成本(为养育子女所耗费的时间或放弃工作的成本)不断提高,青年夫妻的生育意愿下降,结婚率降低,自愿选择不生育的“丁克”(夫妻双方工作,无子女)家庭数量增加。近年来,青年夫妻的不孕率也在提高。另一方面,一些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下称“二孩”)的意愿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实现,也人为地降低了生育率。 实际上生育率降低不是仅仅发生在上海的孤立现象。我国城市地区的生育率已经普遍降低到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我国总人口的生育率也已降低到 1.3~1.8(不同来源的数据有所差异)。从世界范围来看,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出现了普遍的和持续的生育率下降。 极低生育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目前上海的极低生育率将对上海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首先,生育率的不断降低,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和提高劳动力成本,从而对上海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生育率的不断降低,还会减少家庭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内需的扩大和经济持续增长。极低生育率还意味着未来青年在就第 1 页 共 18 页业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对提高就业人口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生育率的降低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对社会保障体制的财务可持续性产生直接冲击。上海人口的出生高峰发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当年的出生高峰人群目前已开始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并将对上海的社会保障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如上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赡养率,已上升到 1: 1.5(约 1.5 个在职职工负担 1 个离退休人员),比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