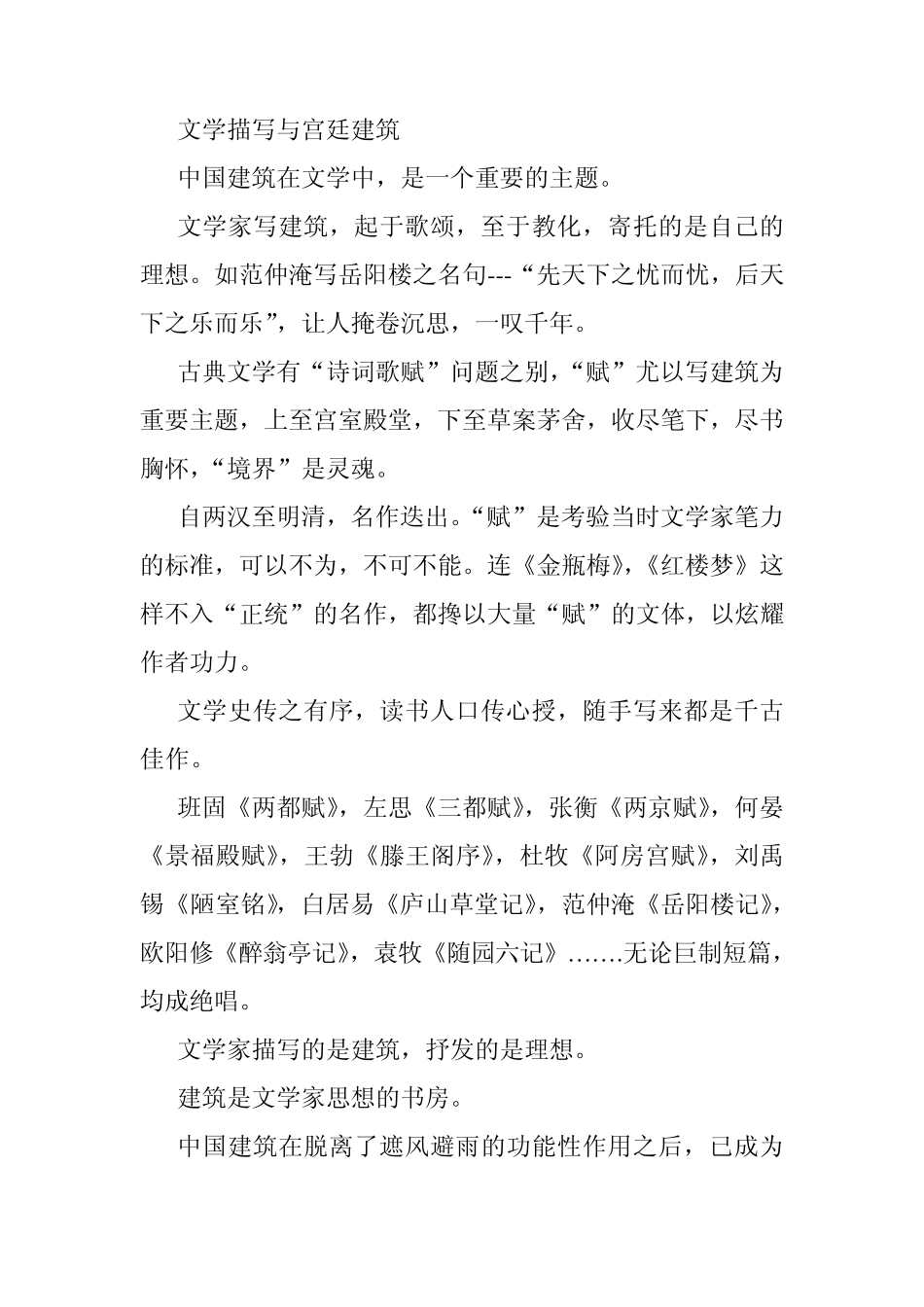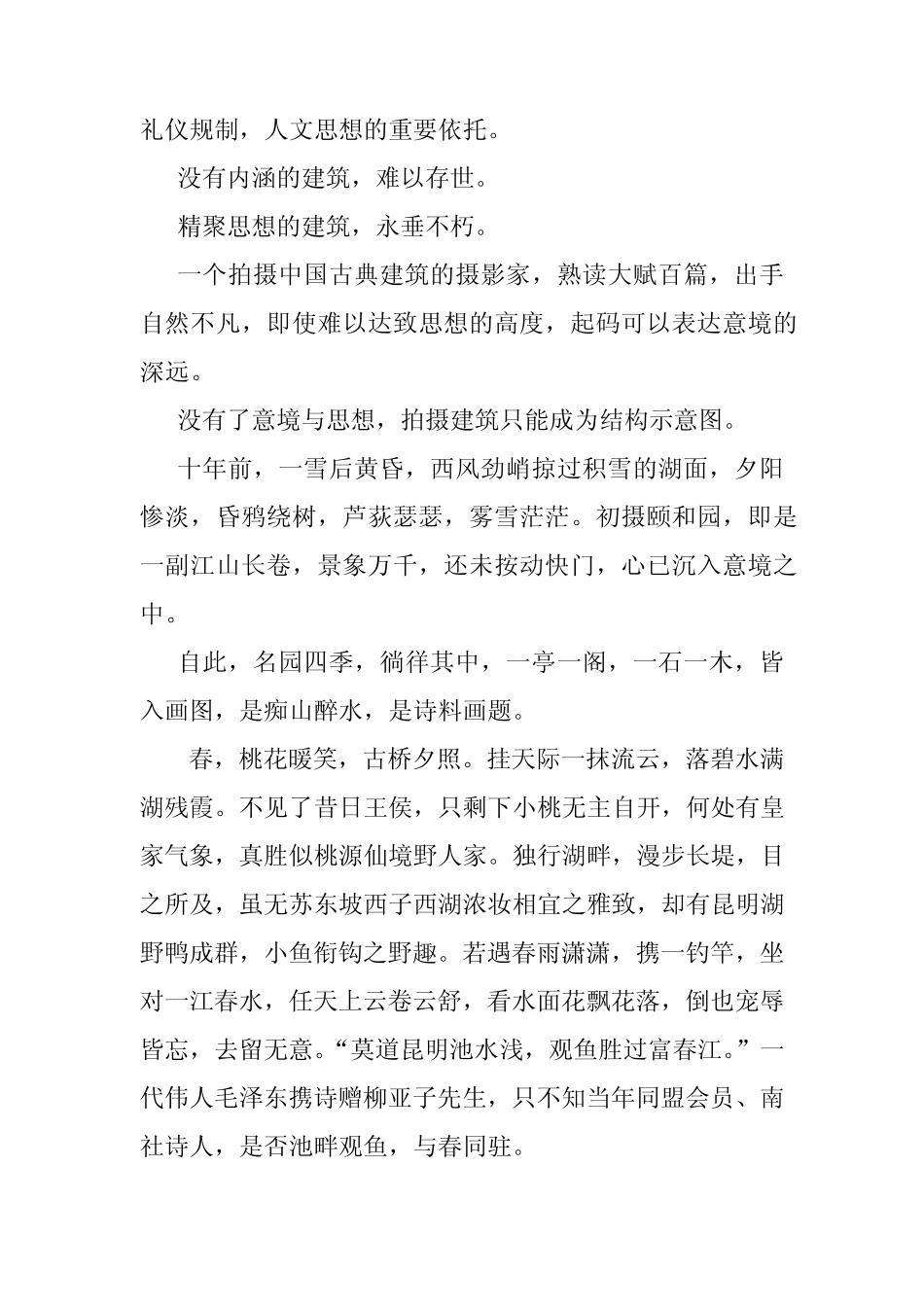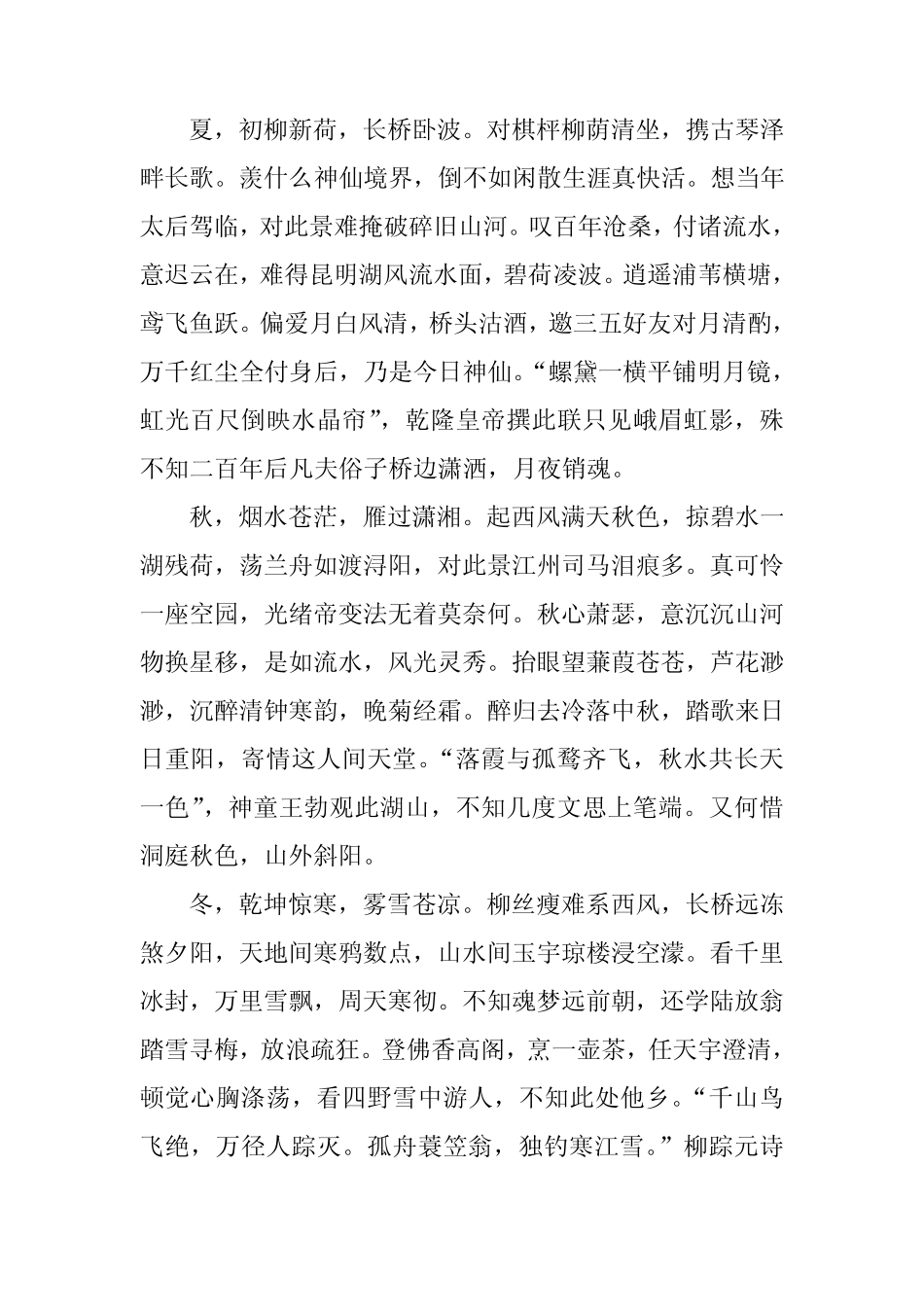文学描写与宫廷建筑 中国建筑在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文学家写建筑,起于歌颂,至于教化,寄托的是自己的理想。如范仲淹写岳阳楼之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人掩卷沉思,一叹千年。 古典文学有“诗词歌赋”问题之别,“赋”尤以写建筑为重要主题,上至宫室殿堂,下至草案茅舍,收尽笔下,尽书胸怀,“境界”是灵魂。 自两汉至明清,名作迭出。“赋”是考验当时文学家笔力的标准,可以不为,不可不能。连《金瓶梅》,《红楼梦》这样不入“正统”的名作,都搀以大量“赋”的文体,以炫耀作者功力。 文学史传之有序,读书人口传心授,随手写来都是千古佳作。 班固《两都赋》,左思《三都赋》,张衡《两京赋》,何晏《景福殿赋》,王勃《滕王阁序》,杜牧《阿房宫赋》,刘禹锡《陋室铭》,白居易《庐山草堂记》,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袁牧《随园六记》…….无论巨制短篇,均成绝唱。 文学家描写的是建筑,抒发的是理想。 建筑是文学家思想的书房。 中国建筑在脱离了遮风避雨的功能性作用之后,已成为礼仪规制,人文思想的重要依托。 没有内涵的建筑,难以存世。 精聚思想的建筑,永垂不朽。 一个拍摄中国古典建筑的摄影家,熟读大赋百篇,出手自然不凡,即使难以达致思想的高度,起码可以表达意境的深远。 没有了意境与思想,拍摄建筑只能成为结构示意图。 十年前,一雪后黄昏,西风劲峭掠过积雪的湖面,夕阳惨淡,昏鸦绕树,芦荻瑟瑟,雾雪茫茫。初摄颐和园,即是一副江山长卷,景象万千,还未按动快门,心已沉入意境之中。 自此,名园四季,徜徉其中,一亭一阁,一石一木,皆入画图,是痴山醉水,是诗料画题。 春,桃花暖笑,古桥夕照。挂天际一抹流云,落碧水满湖残霞。不见了昔日王侯,只剩下小桃无主自开,何处有皇家气象,真胜似桃源仙境野人家。独行湖畔,漫步长堤,目之所及,虽无苏东坡西子西湖浓妆相宜之雅致,却有昆明湖野鸭成群,小鱼衔钩之野趣。若遇春雨潇潇,携一钓竿,坐对一江春水,任天上云卷云舒,看水面花飘花落,倒也宠辱皆忘,去留无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一代伟人毛泽东携诗赠柳亚子先生,只不知当年同盟会员、南社诗人,是否池畔观鱼,与春同驻。 夏,初柳新荷,长桥卧波。对棋枰柳荫清坐,携古琴泽畔长歌。羡什么神仙境界,倒不如闲散生涯真快活。想当年太后驾临,对此景难掩破碎旧山河。叹百年沧桑,付诸流水,意迟云在,难得昆明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