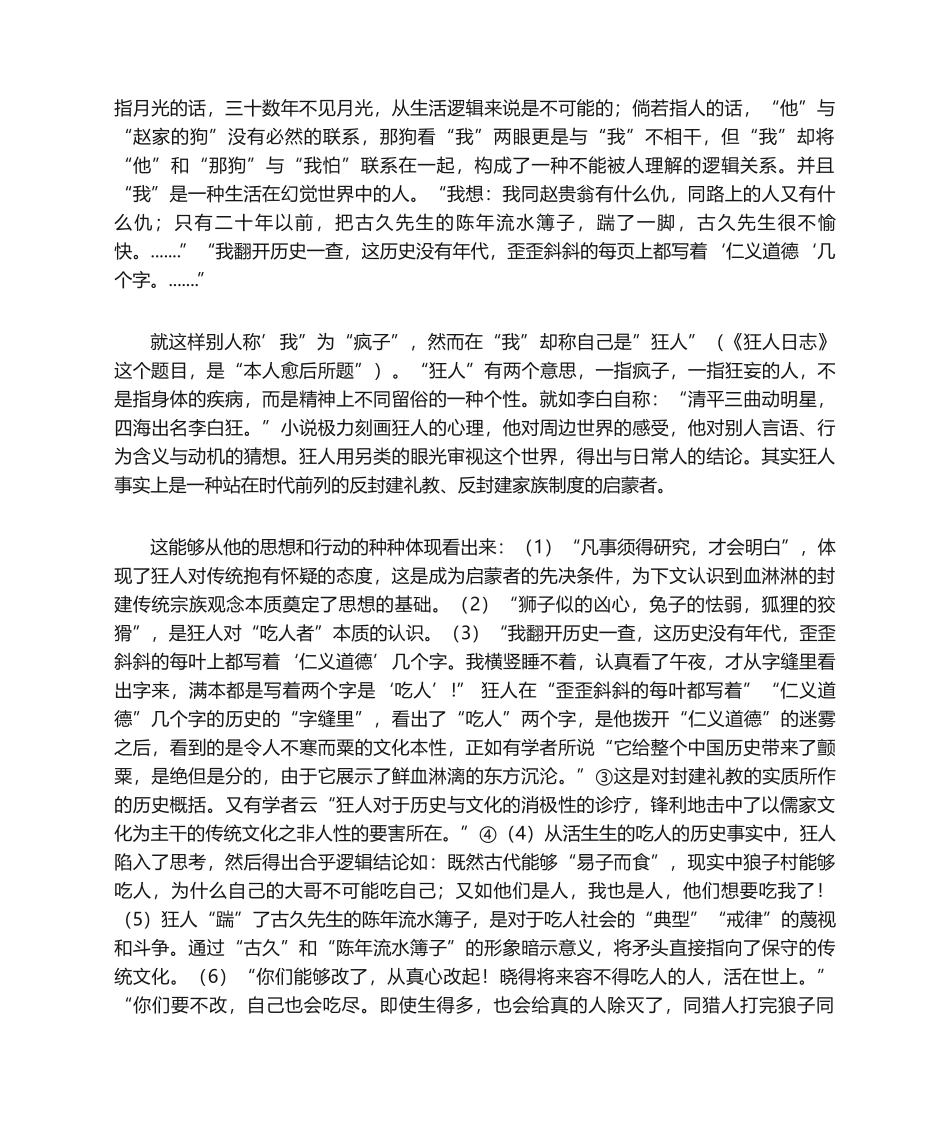简述《狂人日志》的思想内涵AP0601620 余亮宗《狂人日志》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五卷上。这正是五四运动暴发的酝酿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标语,增进了一部分有识之士思想上的觉悟。正当旧社会中的封建陈旧观念与新兴思想发生激烈的碰撞之际,鲁迅响应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在钱玄同的邀请下,他为《新青年》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第一篇便是《狂人日志》。于是中国新文学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就此诞生。《狂人日志》的创作与当时的特定思想氛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革命”提出摒弃文言文外,还提出要用当代的新兴的思想,也就是反对儒家三纲,主张人人人格独立、男女平等、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用陈独秀的原话来说:“今天’国家‘、’民族‘、’家庭‘、’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所遗漏”①;李大钊也谈到:“我们现在所规定的,是个性解放自由的我,和一种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国家、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障碍,生活的烦累”②。《狂人日志》无疑响应了时代的号召,为个性独立解放,用文字化作锋利的矛头猛然指向封建宗祖观念。毫无掩饰地揭发“仁义道德”就是“吃人”,劝大家不要再吃人,做“真的人”,呼吁“救救孩子”,这便是其意味深长的主题。小说文本中狂人的日志是以白话文的进行记叙,而文本开头“撮录者“的阐明则采用文言文的形式出现。两者文体形式呈现出格格不入状态,暗示了在文本中的“我”与称“我”为“疯子”而想把我吃了的人们思想上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为什么会被认为“疯子”或是“迫害狂”从文本中的叙述中能够看出:“我“每时每刻都感到胆怯,提防着被人活生生地吃掉,这种的对人的猜忌演变成了变态的心理。他把日常人的交往如探视、抚摸都看作是吃人行为的一部分。如“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种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将别人善意的“笑”理解为暗藏杀机的吃人者的表面文章,完全背离了正常生活的心理轨道。而“我”在这种变态的心理下,正常的逻辑必然会被打破,逻辑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我不见他,已是三十数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懂得以前的三十数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否则,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他”指的某人还是月光?文本没有言明。指月光的话,三十数年不见月光,从生活逻辑来说是不可能的;倘若指人的话,“他”与“赵家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