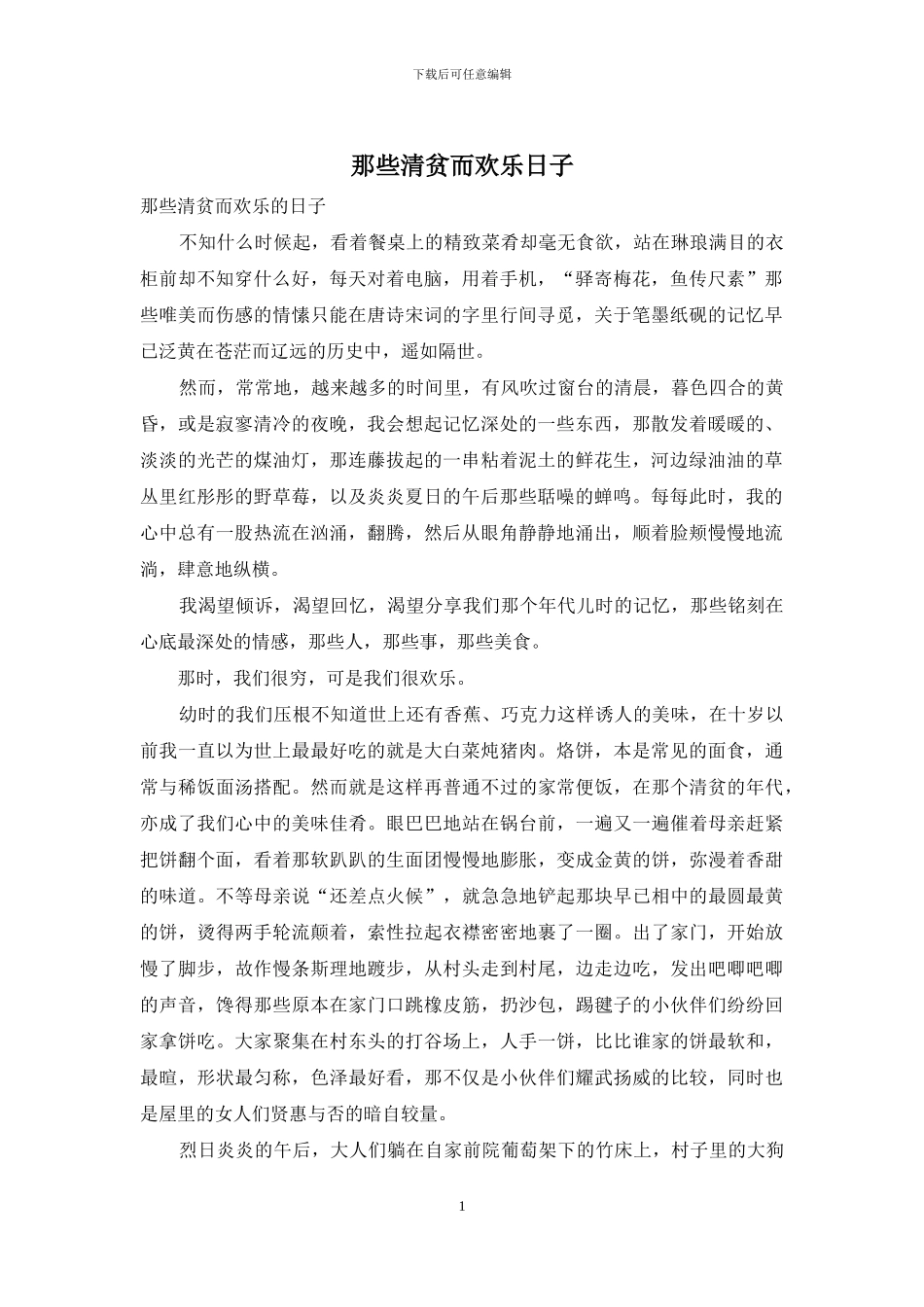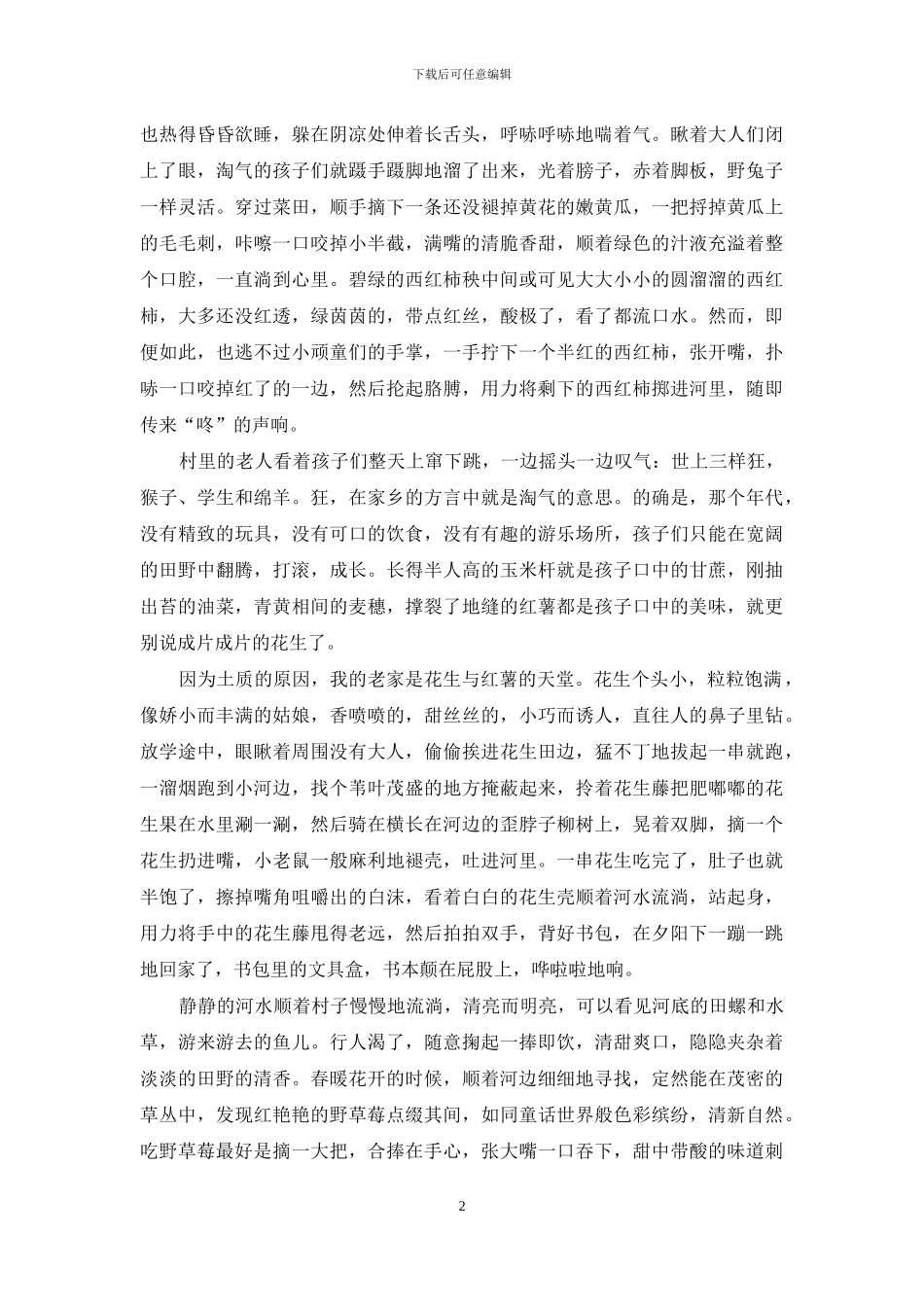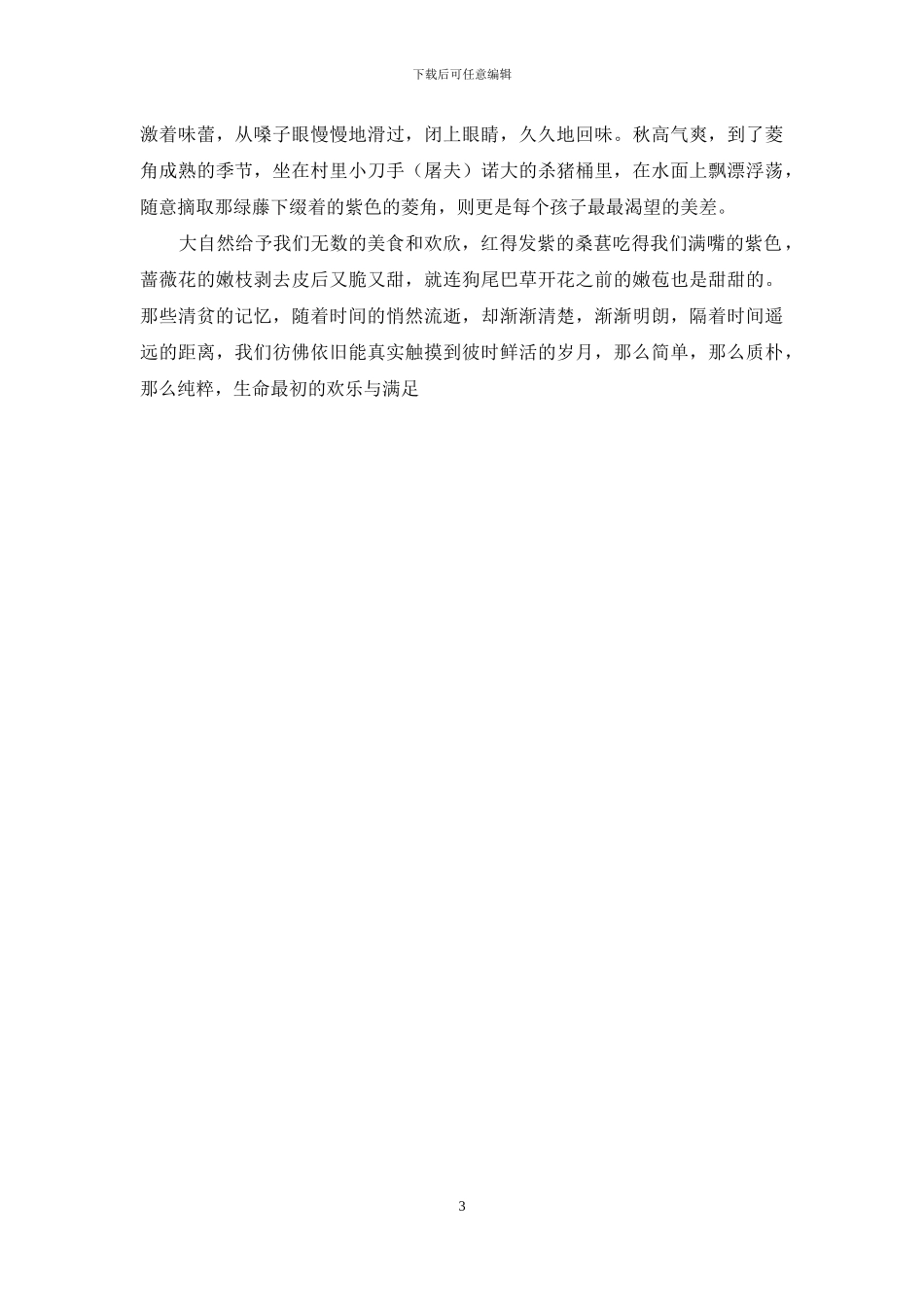下载后可任意编辑那些清贫而欢乐日子那些清贫而欢乐的日子 不知什么时候起,看着餐桌上的精致菜肴却毫无食欲,站在琳琅满目的衣柜前却不知穿什么好,每天对着电脑,用着手机,“驿寄梅花,鱼传尺素”那些唯美而伤感的情愫只能在唐诗宋词的字里行间寻觅,关于笔墨纸砚的记忆早已泛黄在苍茫而辽远的历史中,遥如隔世。 然而,常常地,越来越多的时间里,有风吹过窗台的清晨,暮色四合的黄昏,或是寂寥清冷的夜晚,我会想起记忆深处的一些东西,那散发着暖暖的、淡淡的光芒的煤油灯,那连藤拔起的一串粘着泥土的鲜花生,河边绿油油的草丛里红彤彤的野草莓,以及炎炎夏日的午后那些聒噪的蝉鸣。每每此时,我的心中总有一股热流在汹涌,翻腾,然后从眼角静静地涌出,顺着脸颊慢慢地流淌,肆意地纵横。 我渴望倾诉,渴望回忆,渴望分享我们那个年代儿时的记忆,那些铭刻在心底最深处的情感,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美食。 那时,我们很穷,可是我们很欢乐。 幼时的我们压根不知道世上还有香蕉、巧克力这样诱人的美味,在十岁以前我一直以为世上最最好吃的就是大白菜炖猪肉。烙饼,本是常见的面食,通常与稀饭面汤搭配。然而就是这样再普通不过的家常便饭,在那个清贫的年代,亦成了我们心中的美味佳肴。眼巴巴地站在锅台前,一遍又一遍催着母亲赶紧把饼翻个面,看着那软趴趴的生面团慢慢地膨胀,变成金黄的饼,弥漫着香甜的味道。不等母亲说“还差点火候”,就急急地铲起那块早已相中的最圆最黄的饼,烫得两手轮流颠着,索性拉起衣襟密密地裹了一圈。出了家门,开始放慢了脚步,故作慢条斯理地踱步,从村头走到村尾,边走边吃,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馋得那些原本在家门口跳橡皮筋,扔沙包,踢毽子的小伙伴们纷纷回家拿饼吃。大家聚集在村东头的打谷场上,人手一饼,比比谁家的饼最软和,最暄,形状最匀称,色泽最好看,那不仅是小伙伴们耀武扬威的比较,同时也是屋里的女人们贤惠与否的暗自较量。 烈日炎炎的午后,大人们躺在自家前院葡萄架下的竹床上,村子里的大狗1下载后可任意编辑也热得昏昏欲睡,躲在阴凉处伸着长舌头,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瞅着大人们闭上了眼,淘气的孩子们就蹑手蹑脚地溜了出来,光着膀子,赤着脚板,野兔子一样灵活。穿过菜田,顺手摘下一条还没褪掉黄花的嫩黄瓜,一把捋掉黄瓜上的毛毛刺,咔嚓一口咬掉小半截,满嘴的清脆香甜,顺着绿色的汁液充溢着整个口腔,一直淌到心里。碧绿的西红柿秧中间或可见大大小小的圆溜溜的西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