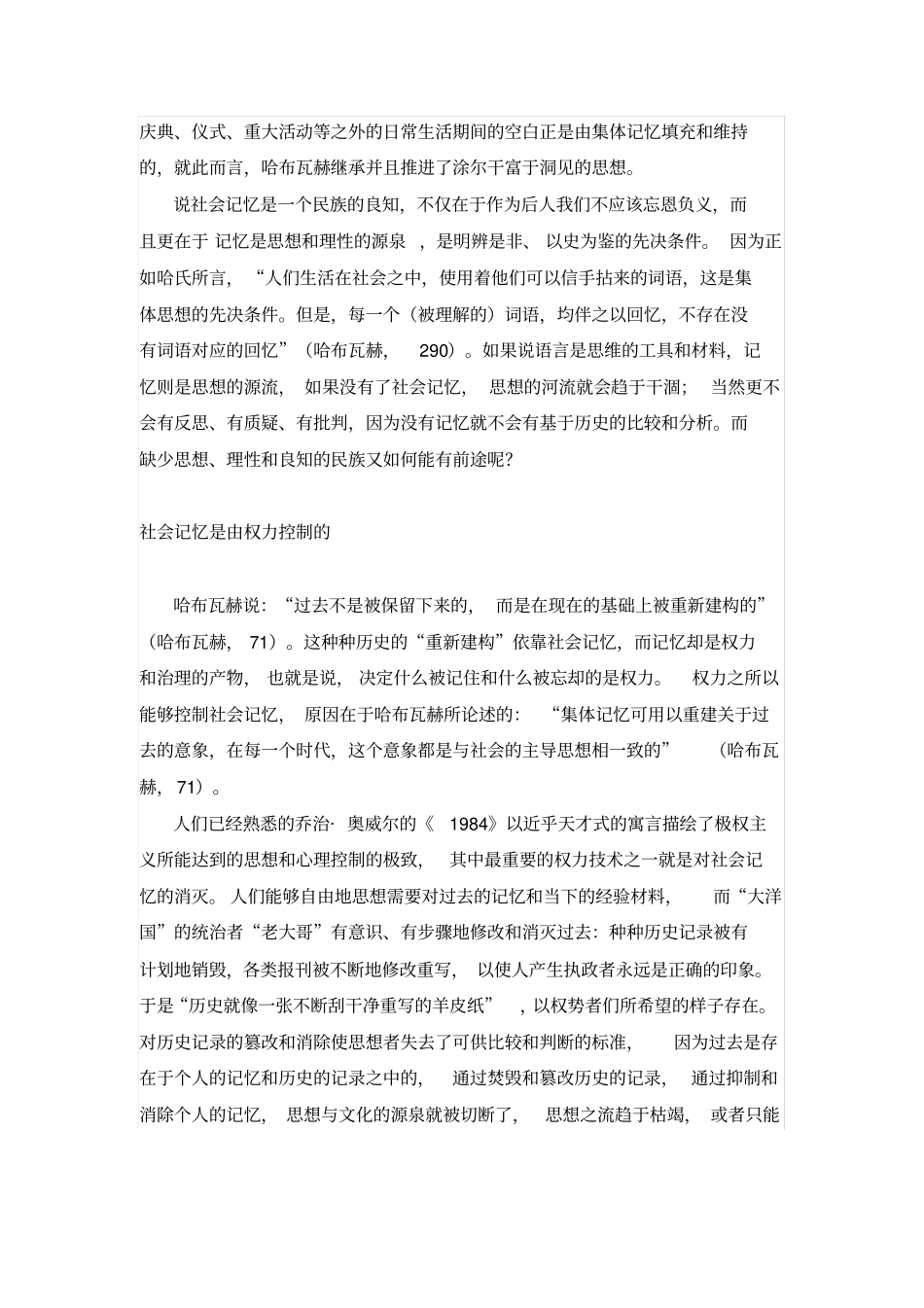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栏目曾播出这样一个节目: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十年前从古董市场高价 “淘”到五张抗美援朝烈士证书, 这个爱好收藏且原本以赚钱为目的的普通农民开始了贴钱寻找烈士家属的过程。十年间,李红旗在不懈的努力和有关部门与媒体的帮助下,找到了三位烈士的家人, 使自己成为送这些英雄魂归故里与其家庭团聚的使者。 烈士的家人在接到证书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五十多年来身处何方、 魂归何乡——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当他们手捧烈士证书老泪纵横甚至嚎啕失声的时候, 我们能够体会到李红旗的确很像上苍派来的使者。媒体的有关报道当然是高度赞扬这位“送烈士回家的人”的普通农民亦堪称英雄的举动,而除了钦佩赞赏之外,一些问题一直在心中回旋,挥之不去,左突右奔,尤如一股力量将胸膛撞击得生疼。这些问题就是: 烈士证书为什么没有送达烈士家庭?即使送交有困难也应该在相应部门存档,但却为什么流入旧货市场?谁有权力这样地处理这些宝贵资料,把它们当作废品卖掉?这些牺牲于战场的英雄对于国家来说可能只是千千万万英烈中的一员,而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却是唯一、是一切,他们难道仅仅是国家获得和巩固政权的工具?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应该由政府来完成的工作为什么却由一个普通农民千辛万苦地来承担?⋯⋯媒体除了表扬这类“好人好事”之外,是不是也该问几个为什么?长久以来,也许久到有史以来,民众的历史一直都无足轻重,如同水滴随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翻不起一点涟漪,留不下任何痕迹。类似于上述“寻亲”的事件还有许许多多, 难道我们真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忘记过去,忘记前辈,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对一个族群而言, 都是一种灾难, 对一种文化来说也将是毁灭性的。从涂尔干学派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哈布瓦赫那里我们可以获知记忆的社会本质:集体记忆是由社会框构的,存在着一个记忆的社会框架,具体而言,“进行记忆的是个体, 而不是群体或机构, 但是,这些植根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哈布瓦赫, 68-69,303)。例如,在涂尔干着力讨论的“集体欢腾”如庆典、仪式、重大活动等之外的日常生活期间的空白正是由集体记忆填充和维持的,就此而言,哈布瓦赫继承并且推进了涂尔干富于洞见的思想。说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不仅在于作为后人我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