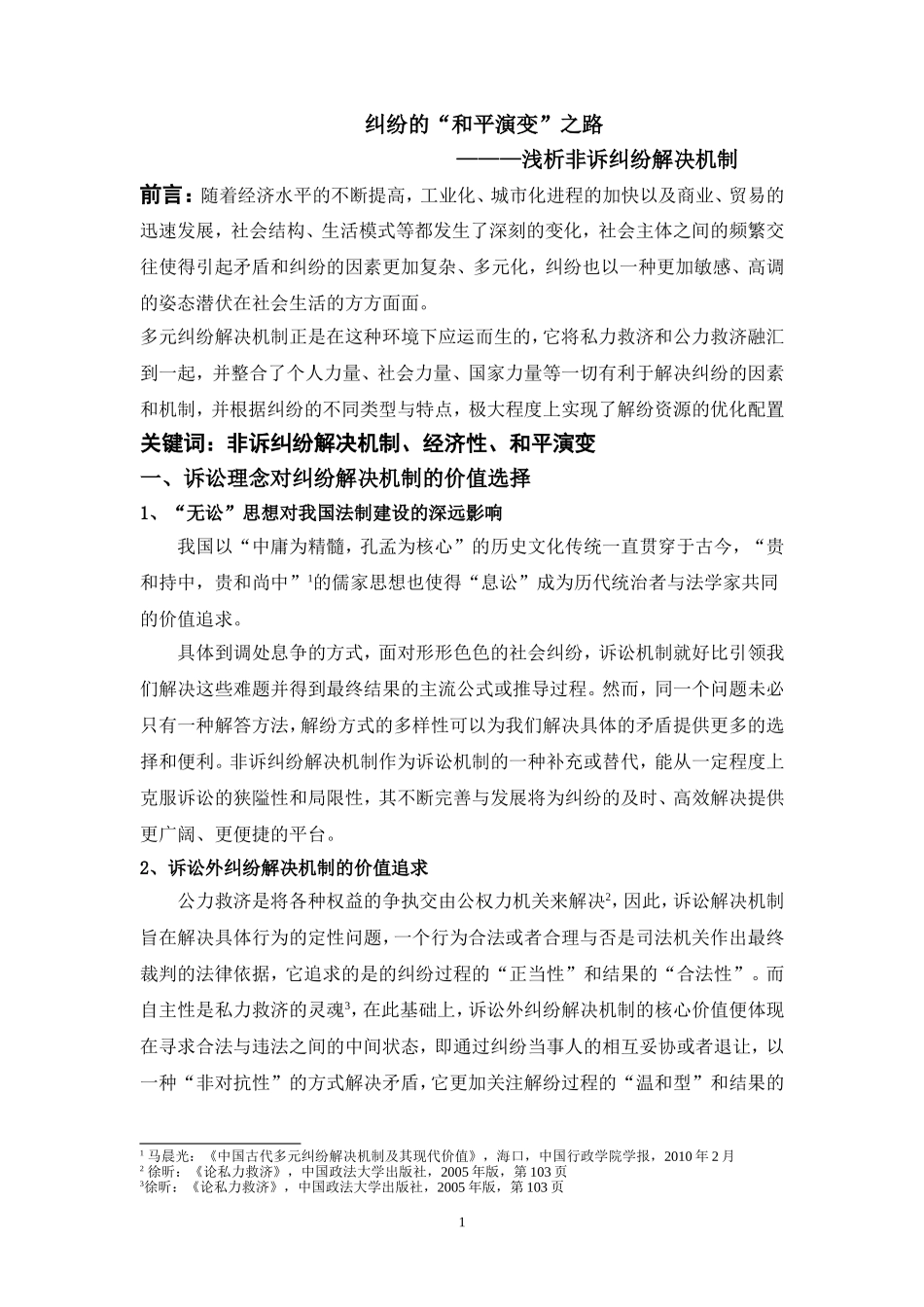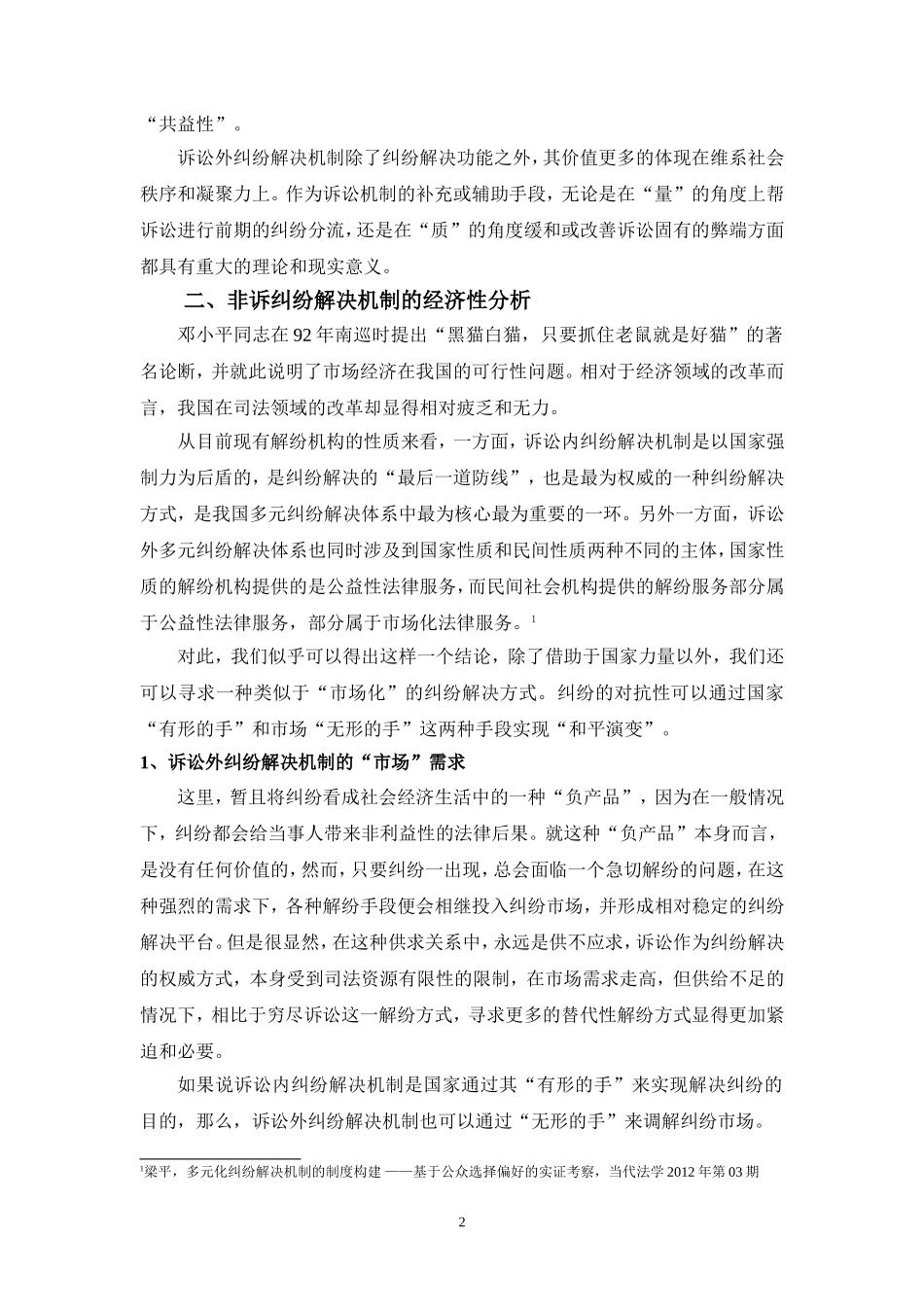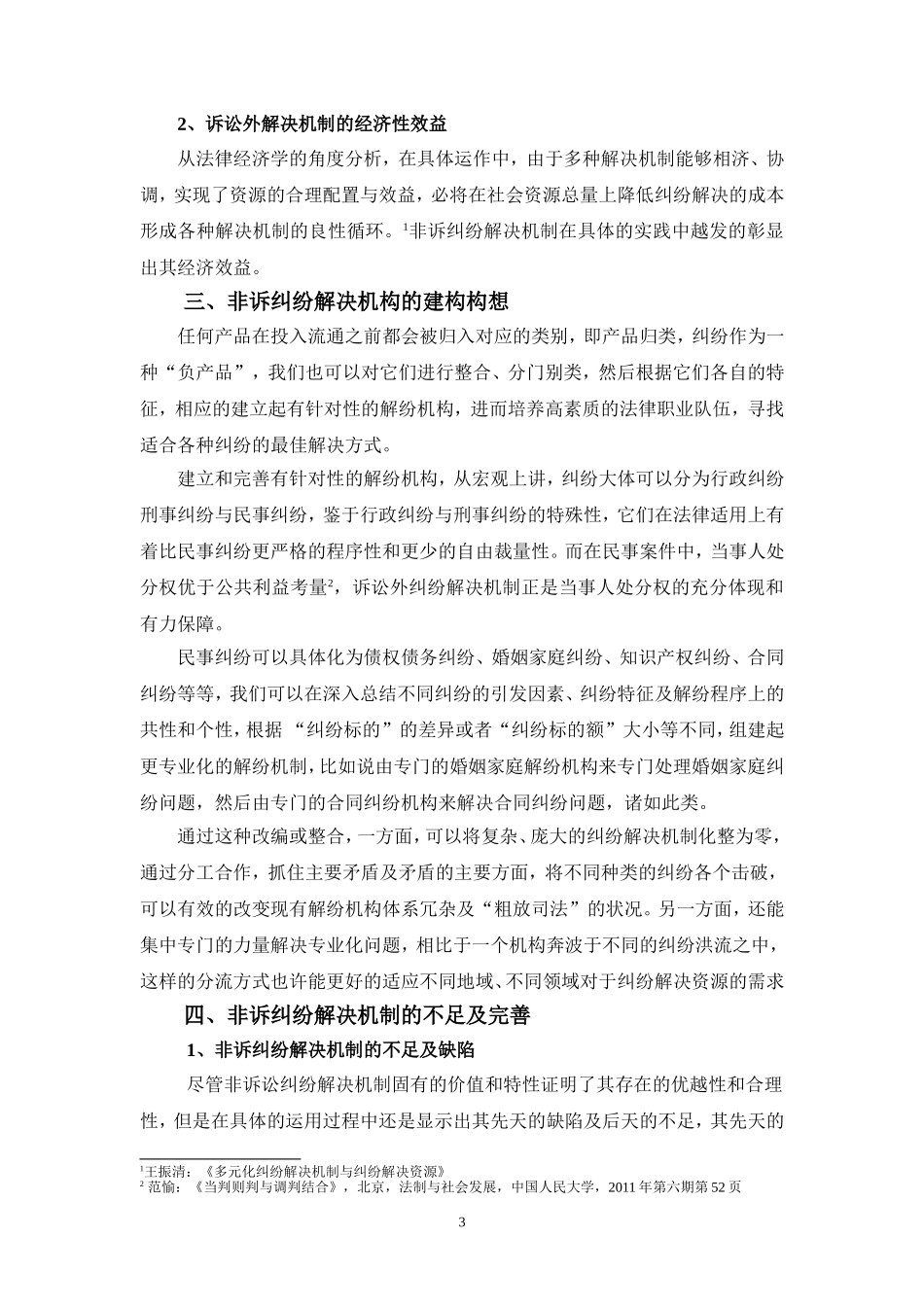纠纷的“和平演变”之路———浅析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前言: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生活模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体之间的频繁交往使得引起矛盾和纠纷的因素更加复杂、多元化,纠纷也以一种更加敏感、高调的姿态潜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它将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融汇到一起,并整合了个人力量、社会力量、国家力量等一切有利于解决纠纷的因素和机制,并根据纠纷的不同类型与特点,极大程度上实现了解纷资源的优化配置关键词: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经济性、和平演变一、诉讼理念对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选择1、“无讼”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深远影响我国以“中庸为精髓,孔孟为核心”的历史文化传统一直贯穿于古今,“贵和持中,贵和尚中”1的儒家思想也使得“息讼”成为历代统治者与法学家共同的价值追求。具体到调处息争的方式,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纠纷,诉讼机制就好比引领我们解决这些难题并得到最终结果的主流公式或推导过程。然而,同一个问题未必只有一种解答方法,解纷方式的多样性可以为我们解决具体的矛盾提供更多的选择和便利。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作为诉讼机制的一种补充或替代,能从一定程度上克服诉讼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其不断完善与发展将为纠纷的及时、高效解决提供更广阔、更便捷的平台。2、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追求公力救济是将各种权益的争执交由公权力机关来解决2,因此,诉讼解决机制旨在解决具体行为的定性问题,一个行为合法或者合理与否是司法机关作出最终裁判的法律依据,它追求的是的纠纷过程的“正当性”和结果的“合法性”。而自主性是私力救济的灵魂3,在此基础上,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价值便体现在寻求合法与违法之间的中间状态,即通过纠纷当事人的相互妥协或者退让,以一种“非对抗性”的方式解决矛盾,它更加关注解纷过程的“温和型”和结果的1马晨光:《中国古代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及其现代价值》,海口,中国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2月2徐昕:《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3徐昕:《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1“共益性”。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除了纠纷解决功能之外,其价值更多的体现在维系社会秩序和凝聚力上。作为诉讼机制的补充或辅助手段,无论是在“量”的角度上帮诉讼进行前期的纠纷分流,还是在“质”的角度缓和或改善诉讼固有的弊端方面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经济性分析邓小平同志在92年南巡时提出“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论断,并就此说明了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可行性问题。相对于经济领域的改革而言,我国在司法领域的改革却显得相对疲乏和无力。从目前现有解纷机构的性质来看,一方面,诉讼内纠纷解决机制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为权威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是我国多元纠纷解决体系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一环。另外一方面,诉讼外多元纠纷解决体系也同时涉及到国家性质和民间性质两种不同的主体,国家性质的解纷机构提供的是公益性法律服务,而民间社会机构提供的解纷服务部分属于公益性法律服务,部分属于市场化法律服务。1对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了借助于国家力量以外,我们还可以寻求一种类似于“市场化”的纠纷解决方式。纠纷的对抗性可以通过国家“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这两种手段实现“和平演变”。1、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市场”需求这里,暂且将纠纷看成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负产品”,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纠纷都会给当事人带来非利益性的法律后果。就这种“负产品”本身而言,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然而,只要纠纷一出现,总会面临一个急切解纷的问题,在这种强烈的需求下,各种解纷手段便会相继投入纠纷市场,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纠纷解决平台。但是很显然,在这种供求关系中,永远是供不应求,诉讼作为纠纷解决的权威方式,本身受到司法资源有限性的限制,在市场需求走高,但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相比于穷尽诉讼这一解纷方式,寻求更多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