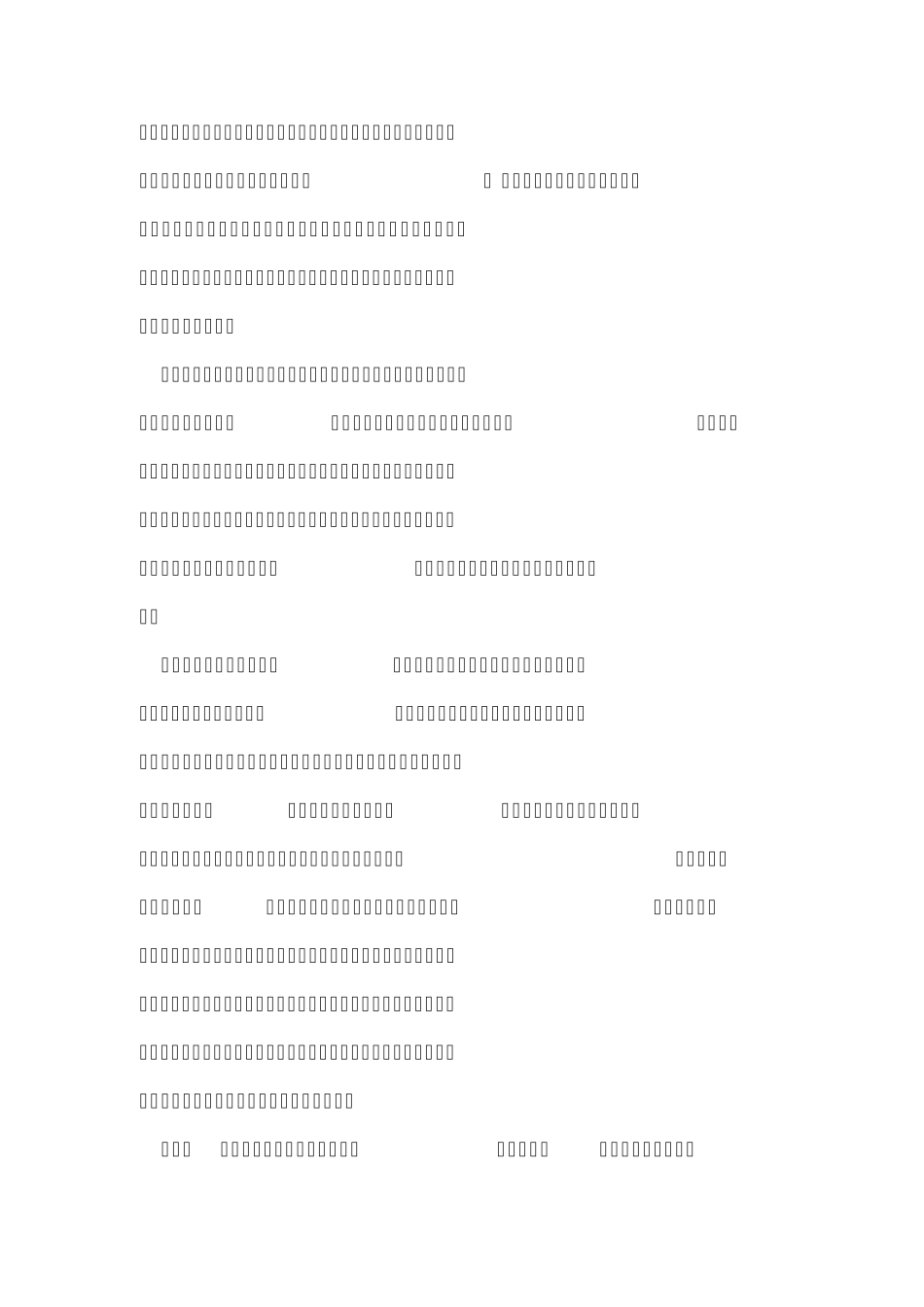《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读书笔记 作为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一书中,以论战的形式针对蒂博1的观点而发,论争的主旨是与蒂博商榷“我们心中所竭诚向往地,乃为同一目标,而朝思夕虑者,实现此目标之手段也。”他们在目的上是一致的,即“拥有一个坚实的法律制度,以抵御专擅与伪善对于我们的伤害;再者,我们都寻求国族的统一与团结,专心致志于秉持同一目标的科学研究”。 而在实现此目标的手段上,二者却大相径庭。在萨氏看来,蒂博关于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典的设想过于理想化,他通过结合当时已存在的一些法典的优缺点分析指出当时的德国并不存在制定统一的法典的条件,客观上也不具备制定法典的历史基础。萨维尼认为只有根据历史传统,才能制定出具备民族精神的法制制度。 在 “实在法的起源”中,作者写到 “在人类信史展开的最为远古的时代, 可以看出,法律已然秉有自身确定的特性,其为一定民族所特有,如同其语言、行为方式和基本的社会组织体制。”由此可知,作者认为法律起源于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如同其语言、行为等一样,具有其自身个性化的民族特性。接下来,作者再一次将法律与语言相比,认为二者同样存在于民族意识之中,它们都并非人为凭空创造的,而是一个民族从古至今通过耕作生产、日常生活逐日编织形成的,并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性的丧失而消亡。从而,此种渊源决定了法律具有双重生命, 1 蒂博是德国杰出的法学家和颇有造诣的音乐爱好者,还是德国哲学法学派的领袖,是民法学家和罗马法研究者,所著《罗马法体系》是学习罗马法的基本教科书。 既“是社会存在整理中的一部分,并将始终为其一部分”,亦为“掌握于法学家之手的独立的知识分支”。 这两种法律的存在形式间的依存合作关系解释了法律起源于有机的过程,即法一开始体现为习惯法,由习俗和人民的信仰产生,其次藉由法学家之手汇集成法律,而非任何专断意志等。 在“制定法规定与法律汇编”一章中,萨氏提出,立法的意义在于“与习俗携手协力,将凡此种种疑虑和不确定性一扫而光,而揭示和保有纯粹的、真正的法律,民族的固有的意志。”法典即为“对于全部现有法律的宣示,而具有由国家本身赋予的排他性效力”。也正是因为这种排他性效力的存在,萨氏才会如此谨慎地对待此部法典的制定。 就法律本身的状况而言,人们期望法典语言规定的精确性和在适用中的统一性,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