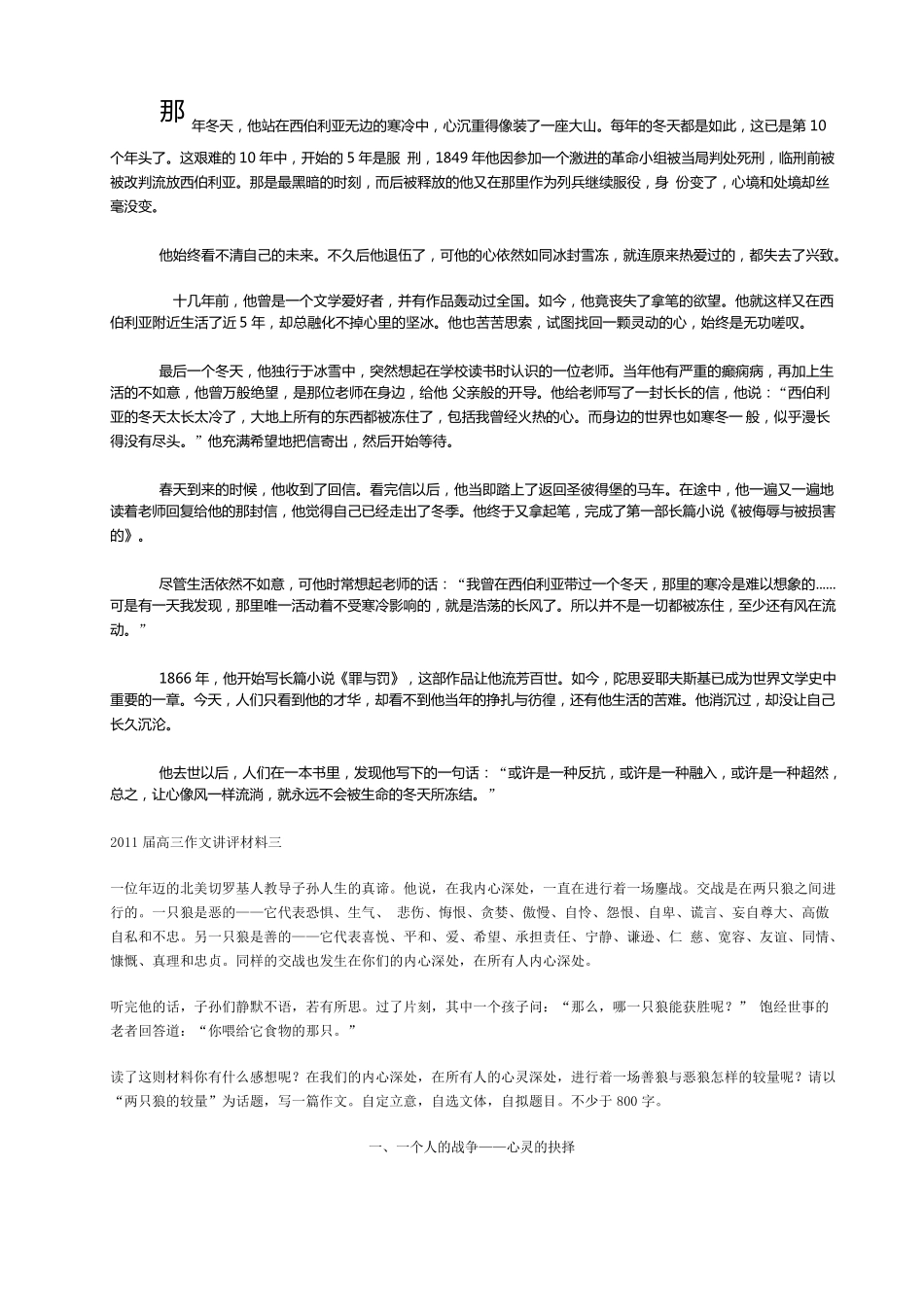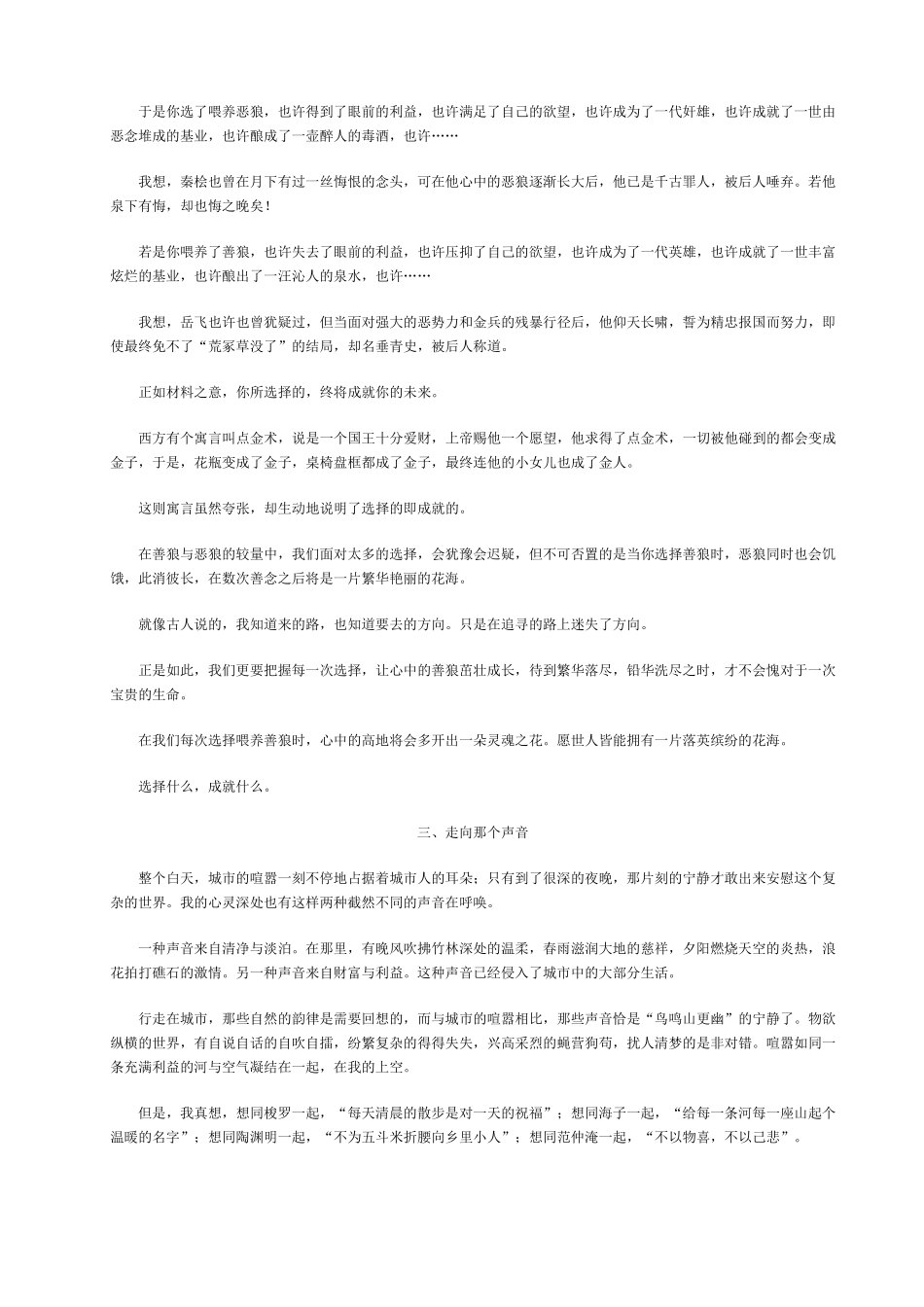那 年 冬 天 , 他 站 在 西 伯 利 亚 无 边 的 寒 冷 中 , 心 沉 重 得 像 装 了 一 座 大 山 。每年 的 冬 天 都是如此, 这已是第 10个年 头了 。这艰难的 10 年 中 , 开始的 5 年 是服 刑, 1849 年 他 因参加一 个激进的 革命小组被当局判处死刑, 临刑前被被改判流放西 伯 利 亚 。那 是最黑暗的 时刻, 而后被释放的 他 又在 那 里作为列兵继续服役, 身 份变了 , 心 境和处境却丝毫没变。 他 始终看不清自己的 未来。不久后他 退伍了 , 可他 的 心 依然如同冰封雪冻, 就连原来热爱过的 , 都失去了 兴致。 十几年 前, 他 曾是一 个文学爱好者, 并 有 作品 轰 动 过全 国 。如今 , 他 竟 丧 失了 拿 笔 的 欲 望 。他 就这样 又在 西伯 利 亚 附 近 生 活 了 近 5 年 , 却总 融 化 不掉 心 里的 坚 冰。他 也 苦 苦 思 索 , 试 图 找 回 一 颗 灵 动 的 心 , 始终是无 功 嗟 叹 。 最后一 个冬 天 , 他 独 行 于 冰雪中 , 突 然想 起 在 学校 读 书 时认 识 的 一 位 老 师 。当年 他 有 严 重 的 癫 痫 病 , 再 加上 生活 的 不如意 , 他 曾万 般 绝 望 , 是那 位 老 师 在 身边 , 给 他 父 亲 般 的 开导 。他 给 老 师 写 了 一 封长 长 的 信 , 他 说 : “西 伯 利亚 的 冬 天 太 长 太 冷 了 , 大 地 上 所 有 的 东 西 都被冻住 了 , 包 括 我 曾经 火 热的 心 。而身边 的 世 界 也 如寒 冬 一 般 , 似 乎 漫 长得 没有 尽 头。”他 充 满 希 望 地 把 信 寄 出 , 然后开始等 待 。 春 天 到 来的 时候 , 他 收 到 了 回 信 。看完 信 以 后, 他 当即 踏 上 了 返 回 圣 彼 得 堡 的 马 车 。在 途 中 , 他 一 遍 又一 遍 地读 着 老 师 回 复 给 他 的 那 封信 , 他 觉 得 自己已经 走 出 了 冬 季 。他 终于 又拿 起 笔 , 完 成 了 第一 部 长 篇 小说 《 被侮 辱 与 被损 害的 》 。 尽 管 生 活 依然不如意 , 可他 时常 想 起 老 师 的 话 : “我 曾在 西 伯 利 亚 带 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