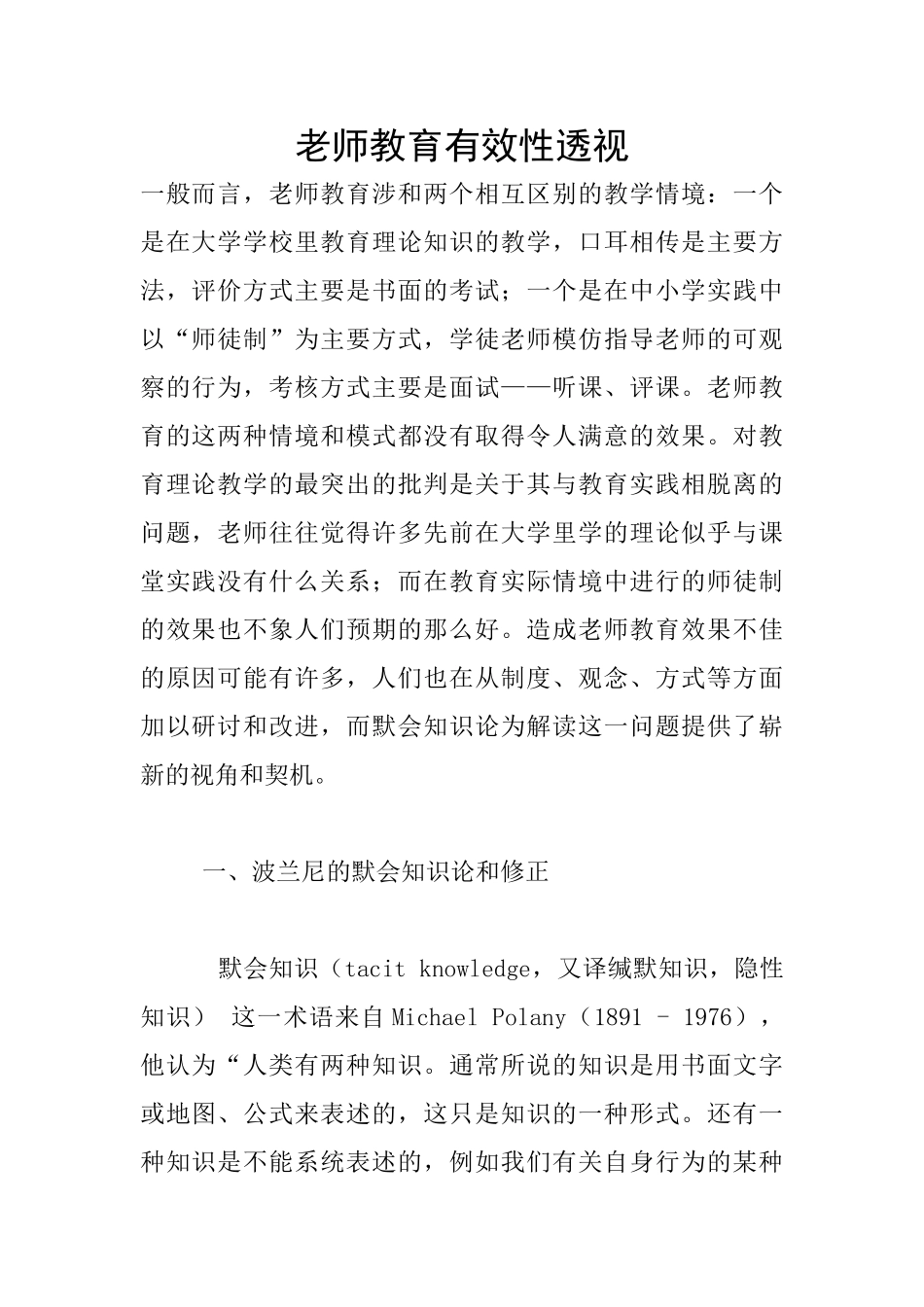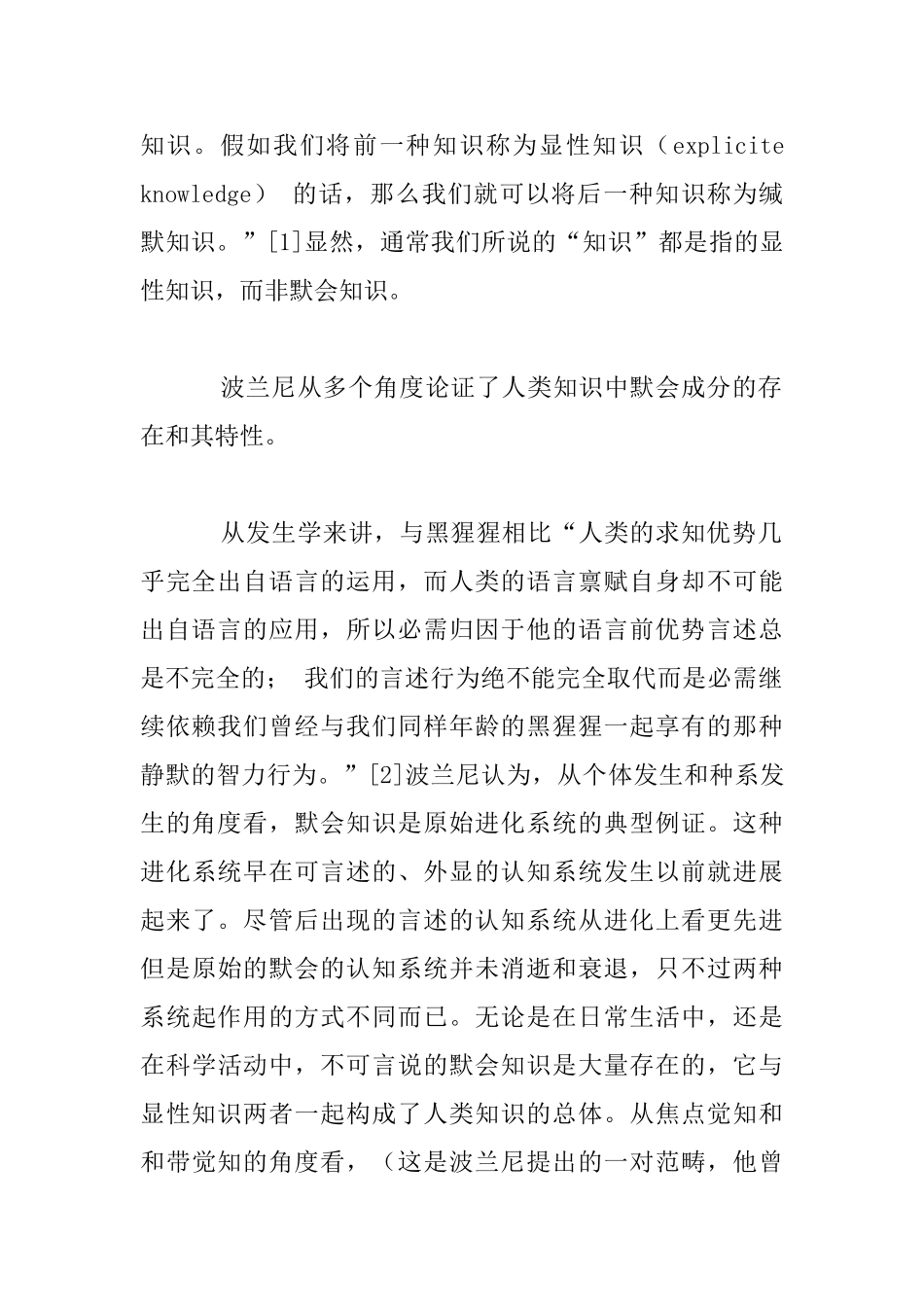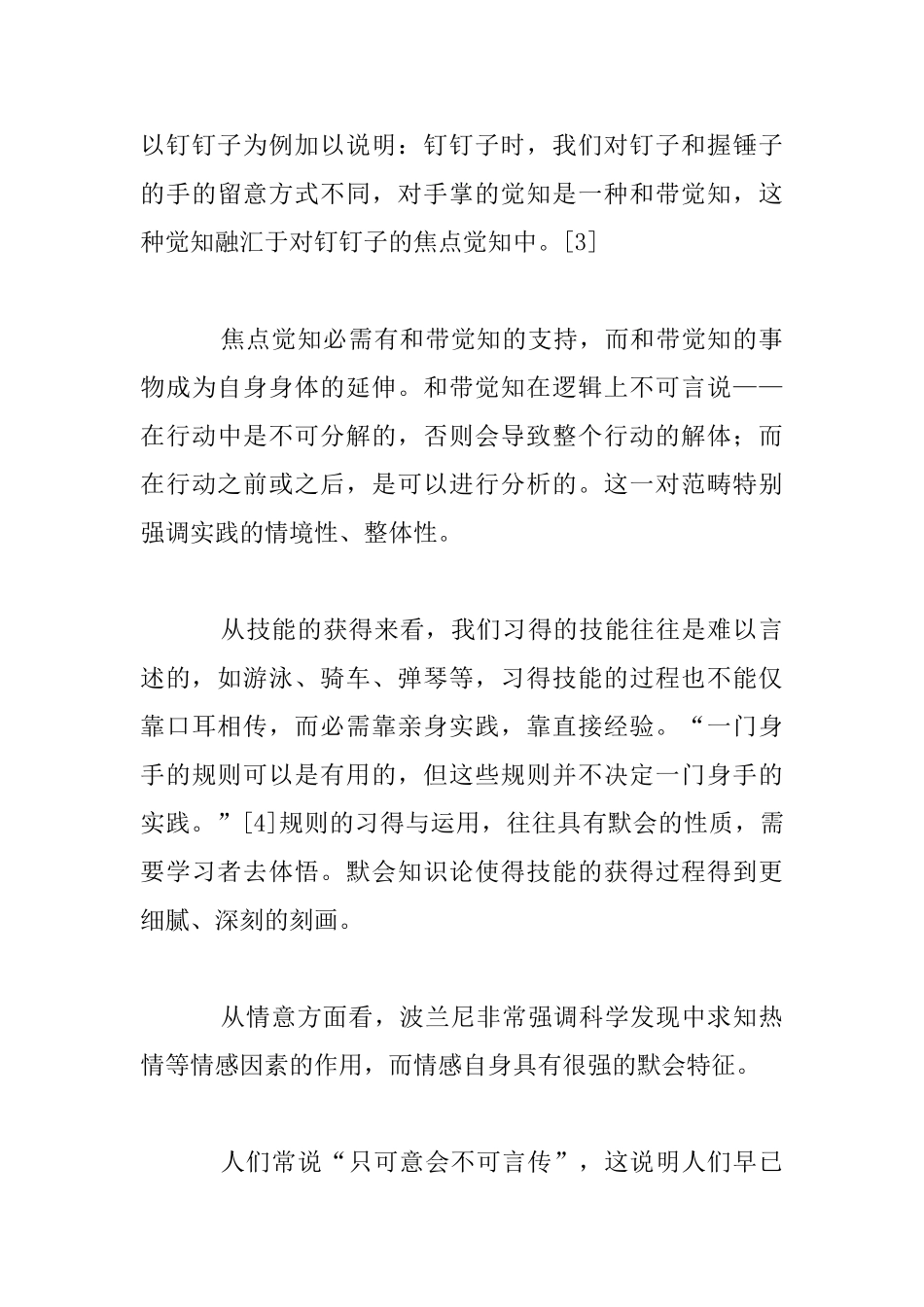老师教育有效性透视一般而言,老师教育涉和两个相互区别的教学情境:一个是在大学学校里教育理论知识的教学,口耳相传是主要方法,评价方式主要是书面的考试;一个是在中小学实践中以“师徒制”为主要方式,学徒老师模仿指导老师的可观察的行为,考核方式主要是面试——听课、评课。老师教育的这两种情境和模式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对教育理论教学的最突出的批判是关于其与教育实践相脱离的问题,老师往往觉得许多先前在大学里学的理论似乎与课堂实践没有什么关系;而在教育实际情境中进行的师徒制的效果也不象人们预期的那么好。造成老师教育效果不佳的原因可能有许多,人们也在从制度、观念、方式等方面加以研讨和改进,而默会知识论为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契机。 一、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论和修正 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又译缄默知识,隐性知识) 这一术语来自 Michael Polany(1891 - 1976),他认为“人类有两种知识。通常所说的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地图、公式来表述的,这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例如我们有关自身行为的某种知识。假如我们将前一种知识称为显性知识(explicite knowledge) 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后一种知识称为缄默知识。”[1]显然,通常我们所说的“知识”都是指的显性知识,而非默会知识。 波兰尼从多个角度论证了人类知识中默会成分的存在和其特性。 从发生学来讲,与黑猩猩相比“人类的求知优势几乎完全出自语言的运用,而人类的语言禀赋自身却不可能出自语言的应用,所以必需归因于他的语言前优势言述总是不完全的; 我们的言述行为绝不能完全取代而是必需继续依赖我们曾经与我们同样年龄的黑猩猩一起享有的那种静默的智力行为。”[2]波兰尼认为,从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角度看,默会知识是原始进化系统的典型例证。这种进化系统早在可言述的、外显的认知系统发生以前就进展起来了。尽管后出现的言述的认知系统从进化上看更先进但是原始的默会的认知系统并未消逝和衰退,只不过两种系统起作用的方式不同而已。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科学活动中,不可言说的默会知识是大量存在的,它与显性知识两者一起构成了人类知识的总体。从焦点觉知和和带觉知的角度看,(这是波兰尼提出的一对范畴,他曾以钉钉子为例加以说明:钉钉子时,我们对钉子和握锤子的手的留意方式不同,对手掌的觉知是一种和带觉知,这种觉知融汇于对钉钉子的焦点觉知中。[3] 焦点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