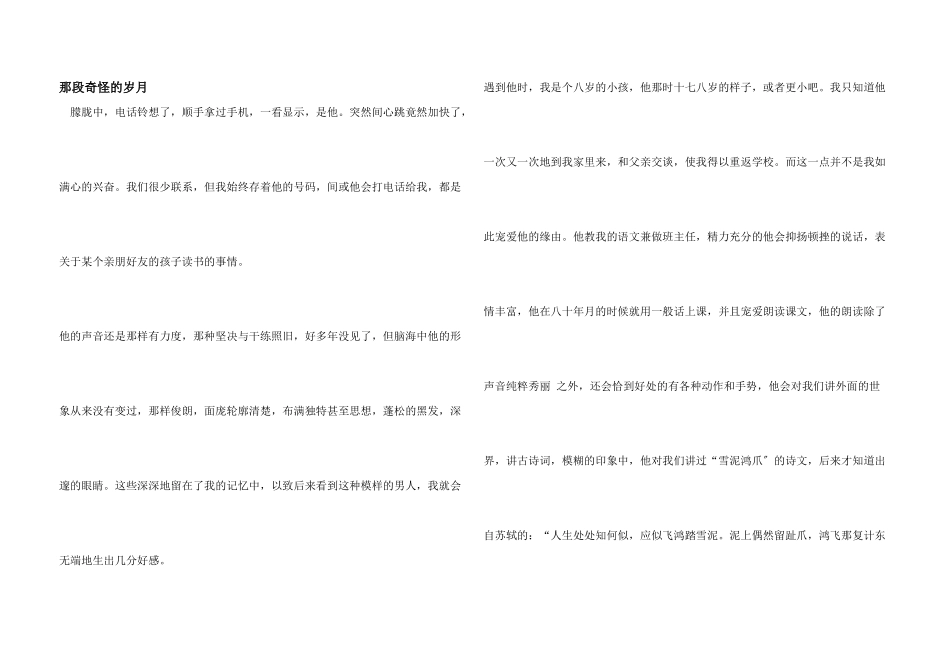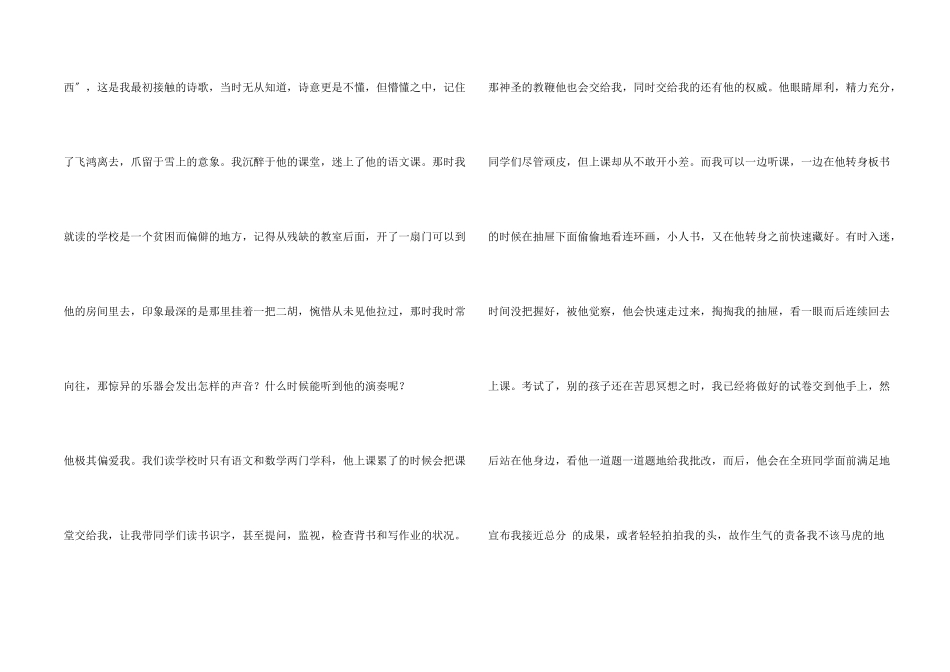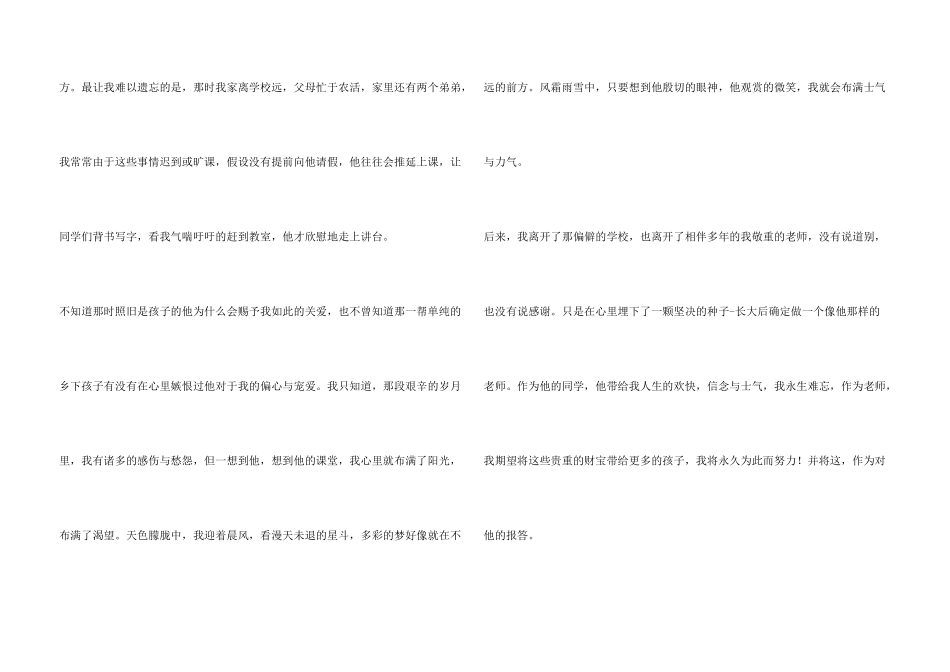那段奇怪的岁月朦胧中,电话铃想了,顺手拿过手机,一看显示,是他。突然间心跳竟然加快了,满心的兴奋。我们很少联系,但我始终存着他的号码,间或他会打电话给我,都是关于某个亲朋好友的孩子读书的事情。他的声音还是那样有力度,那种坚决与干练照旧,好多年没见了,但脑海中他的形象从来没有变过,那样俊朗,面庞轮廓清楚,布满独特甚至思想,蓬松的黑发,深邃的眼睛。这些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以致后来看到这种模样的男人,我就会无端地生出几分好感。遇到他时,我是个八岁的小孩,他那时十七八岁的样子,或者更小吧。我只知道他一次又一次地到我家里来,和父亲交谈,使我得以重返学校。而这一点并不是我如此宠爱他的缘由。他教我的语文兼做班主任,精力充分的他会抑扬顿挫的说话,表情丰富,他在八十年月的时候就用一般话上课,并且宠爱朗读课文,他的朗读除了声音纯粹秀丽 之外,还会恰到好处的有各种动作和手势,他会对我们讲外面的世界,讲古诗词,模糊的印象中,他对我们讲过“雪泥鸿爪〞的诗文,后来才知道出自苏轼的:“人生处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是我最初接触的诗歌,当时无从知道,诗意更是不懂,但懵懂之中,记住了飞鸿离去,爪留于雪上的意象。我沉醉于他的课堂,迷上了他的语文课。那时我就读的学校是一个贫困而偏僻的地方,记得从残缺的教室后面,开了一扇门可以到他的房间里去,印象最深的是那里挂着一把二胡,惋惜从未见他拉过,那时我时常向往,那惊异的乐器会发出怎样的声音?什么时候能听到他的演奏呢?他极其偏爱我。我们读学校时只有语文和数学两门学科,他上课累了的时候会把课堂交给我,让我带同学们读书识字,甚至提问,监视,检查背书和写作业的状况。那神圣的教鞭他也会交给我,同时交给我的还有他的权威。他眼睛犀利,精力充分,同学们尽管顽皮,但上课却从不敢开小差。而我可以一边听课,一边在他转身板书的时候在抽屉下面偷偷地看连环画,小人书,又在他转身之前快速藏好。有时入迷,时间没把握好,被他觉察,他会快速走过来,掏掏我的抽屉,看一眼而后连续回去上课。考试了,别的孩子还在苦思冥想之时,我已经将做好的试卷交到他手上,然后站在他身边,看他一道题一道题地给我批改,而后,他会在全班同学面前满足地宣布我接近总分 的成果,或者轻轻拍拍我的头,故作生气的责备我不该马虎的地方。最让我难以遗忘的是,那时我家离学校远,父母忙于农活,家里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