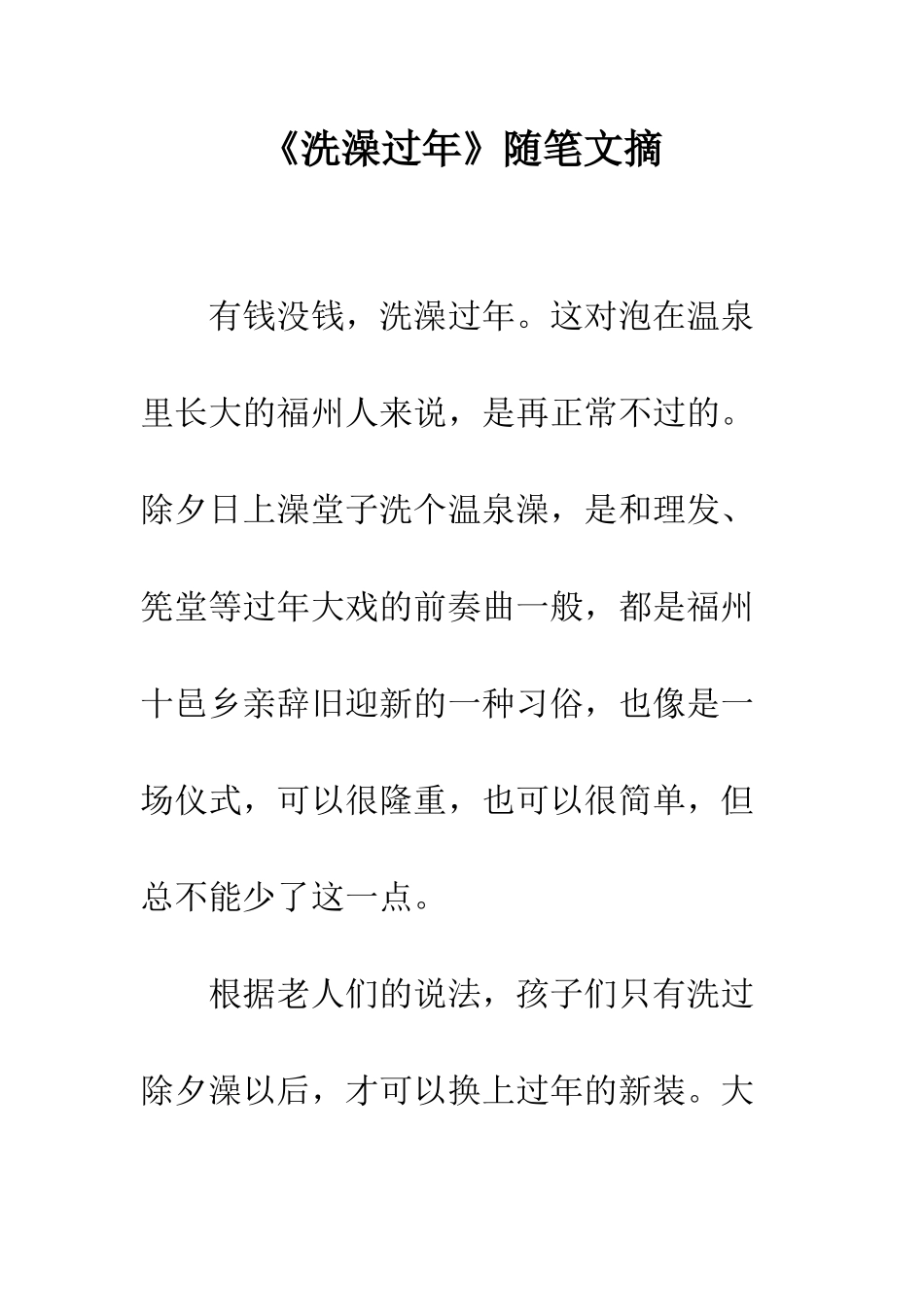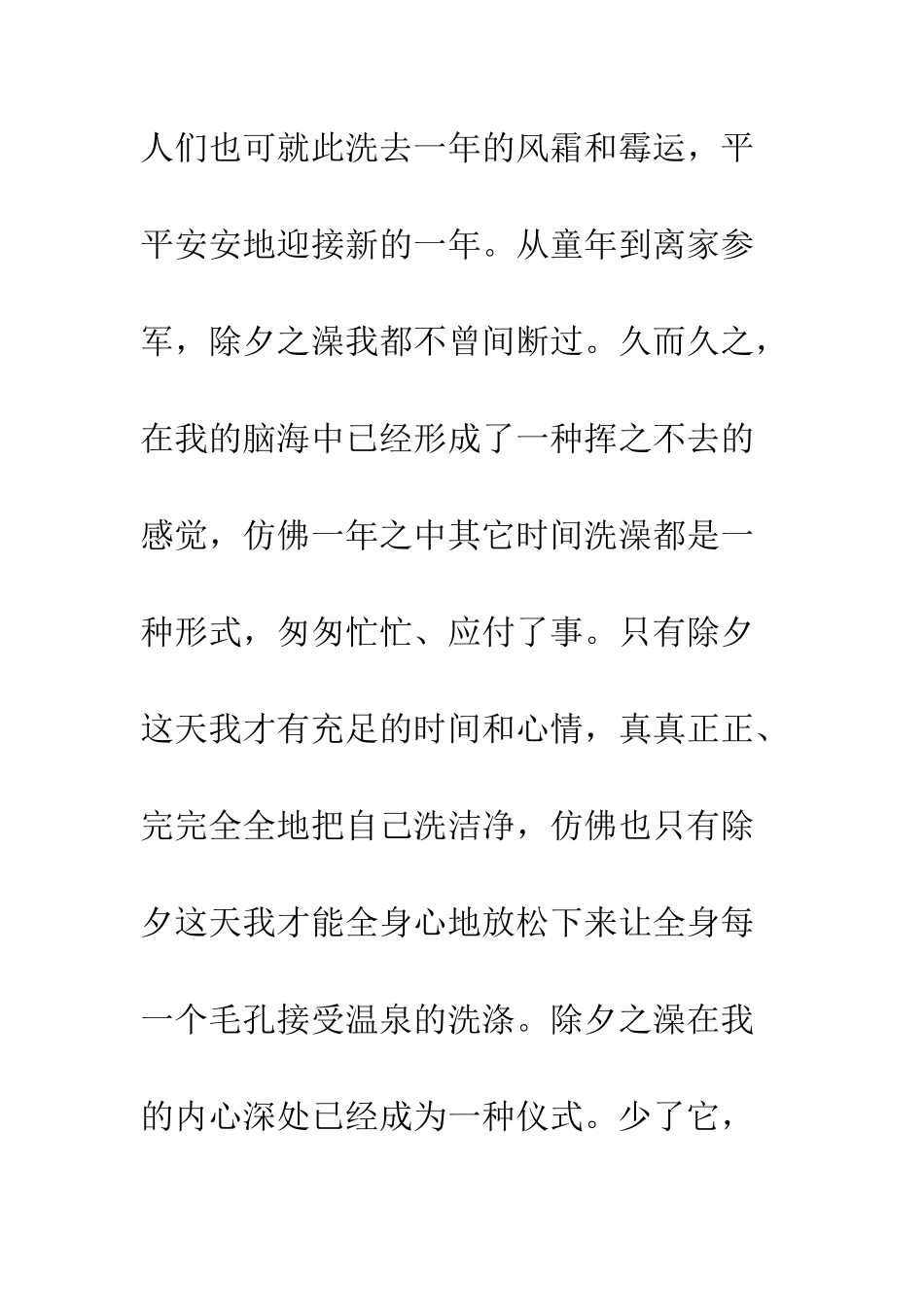《洗澡过年》随笔文摘 有钱没钱,洗澡过年。这对泡在温泉里长大的福州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除夕日上澡堂子洗个温泉澡,是和理发、筅堂等过年大戏的前奏曲一般,都是福州十邑乡亲辞旧迎新的一种习俗,也像是一场仪式,可以很隆重,也可以很简单,但总不能少了这一点。 根据老人们的说法,孩子们只有洗过除夕澡以后,才可以换上过年的新装。大人们也可就此洗去一年的风霜和霉运,平平安安地迎接新的一年。从童年到离家参军,除夕之澡我都不曾间断过。久而久之,在我的脑海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仿佛一年之中其它时间洗澡都是一种形式,匆匆忙忙、应付了事。只有除夕这天我才有充足的时间和心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洗洁净,仿佛也只有除夕这天我才能全身心地放松下来让全身每一个毛孔接受温泉的洗涤。除夕之澡在我的内心深处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少了它,也就少了些过年的味道。 小时候为了洗年澡,除夕这天照例是赖不了床的。天刚启亮便会被母亲从热被窝中拖了起来。匆匆应付几口早饭,父亲便将我扶上自行车的大杠坐好,后架载着一大包母亲为我们准备的换洗衣服,赶去家附近的小沧浪澡堂。 往往我们到时,洗过早汤的第一拨客人已经出来。正红光满面地坐在小摊前,悠闲地叫上一碗鱼丸,拌面吃着。另一边的光饼摊也摆了出来。卖光饼的是一位老人。身材枯瘦,戴着一副老花镜,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那装光饼的白铁箱子便搭在后座上,下面点着个保温的小炭炉。他的摊子就歇在澡堂口的自行车棚内,望见有人走来,便拍着箱子,大声叫卖,“卖光饼了,福清的光饼,又香又好吃的光饼夹”。每回在小沧浪洗完澡,父亲都会给我买上一块光饼夹,那切开的光饼里塞满了苔菜,再请老板浇上一勺浓香扑鼻的辣汁,咬在嘴里绝对是幸福满满的。那时一块夹满红糟肉或绿苔菜的光饼才一角钱。有时赶巧了还能买到烤得酥脆的五香紫菜饼,味道更是好极了。 走进澡堂,跟随氤氲的蒸汽,扑面而来的还有那鼎沸的人声。乡下的,街上的,老的,少的,在汤池里挤得跟插蛏似的,非常喧闹。好不容易在休息区找到一张空的竹床,脱下厚重的冬衣,我的头却被毛衣的领口卡住了,哇哇大叫着。父亲只得先帮我脱完,再用他的外套帮我围上。那时的澡堂是没有储物柜的,父亲总用澡堂里那满是茶渍的床单把衣服卷成一团。便拿上毛巾、香皂牵着我,一人趿着一双木屐,咔哒咔哒往汤池走去。 临近大池,一股熏热的白雾朝脸上扑来,顿时迷了双眼,白雾中隐约望见一条条赤溜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