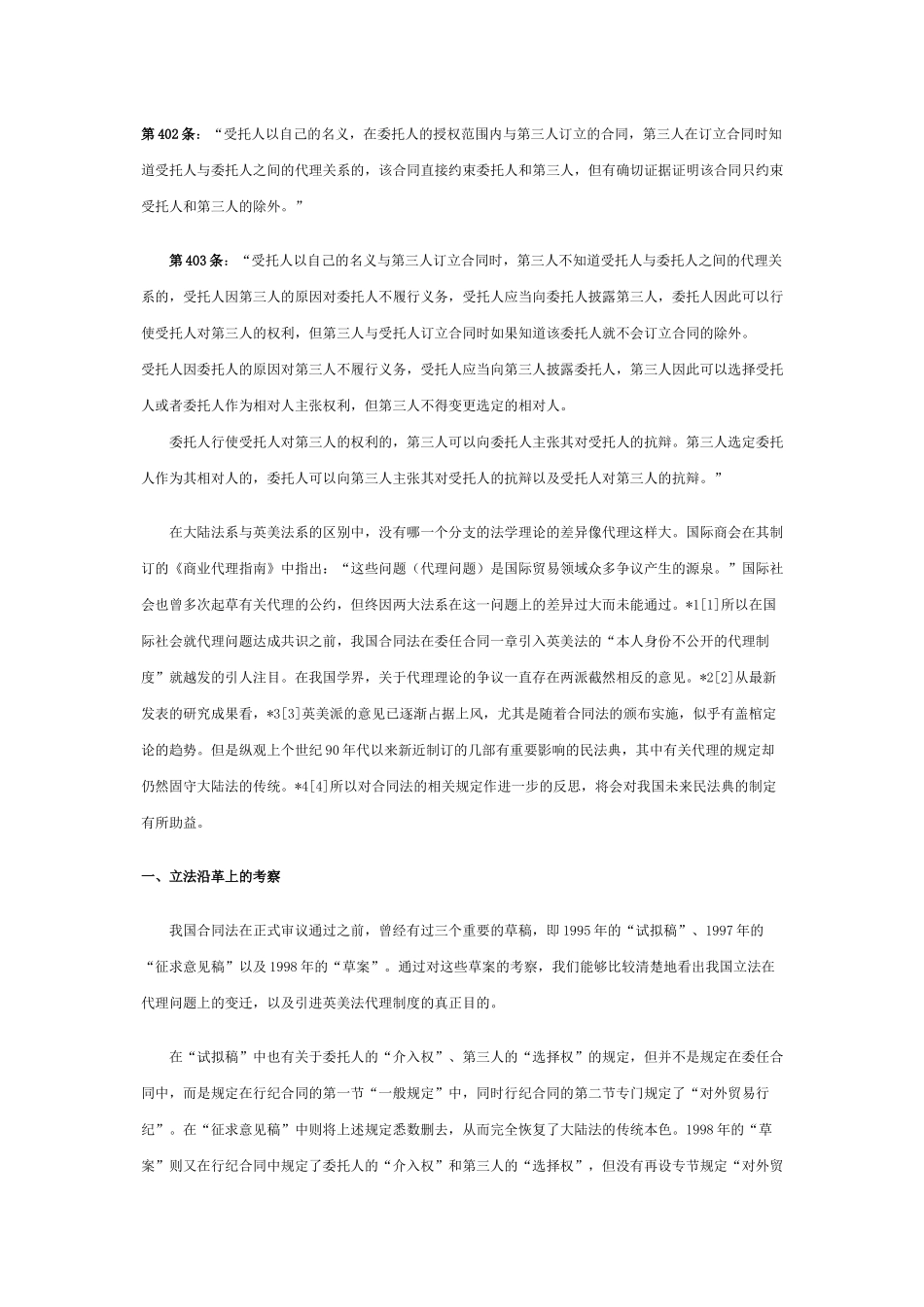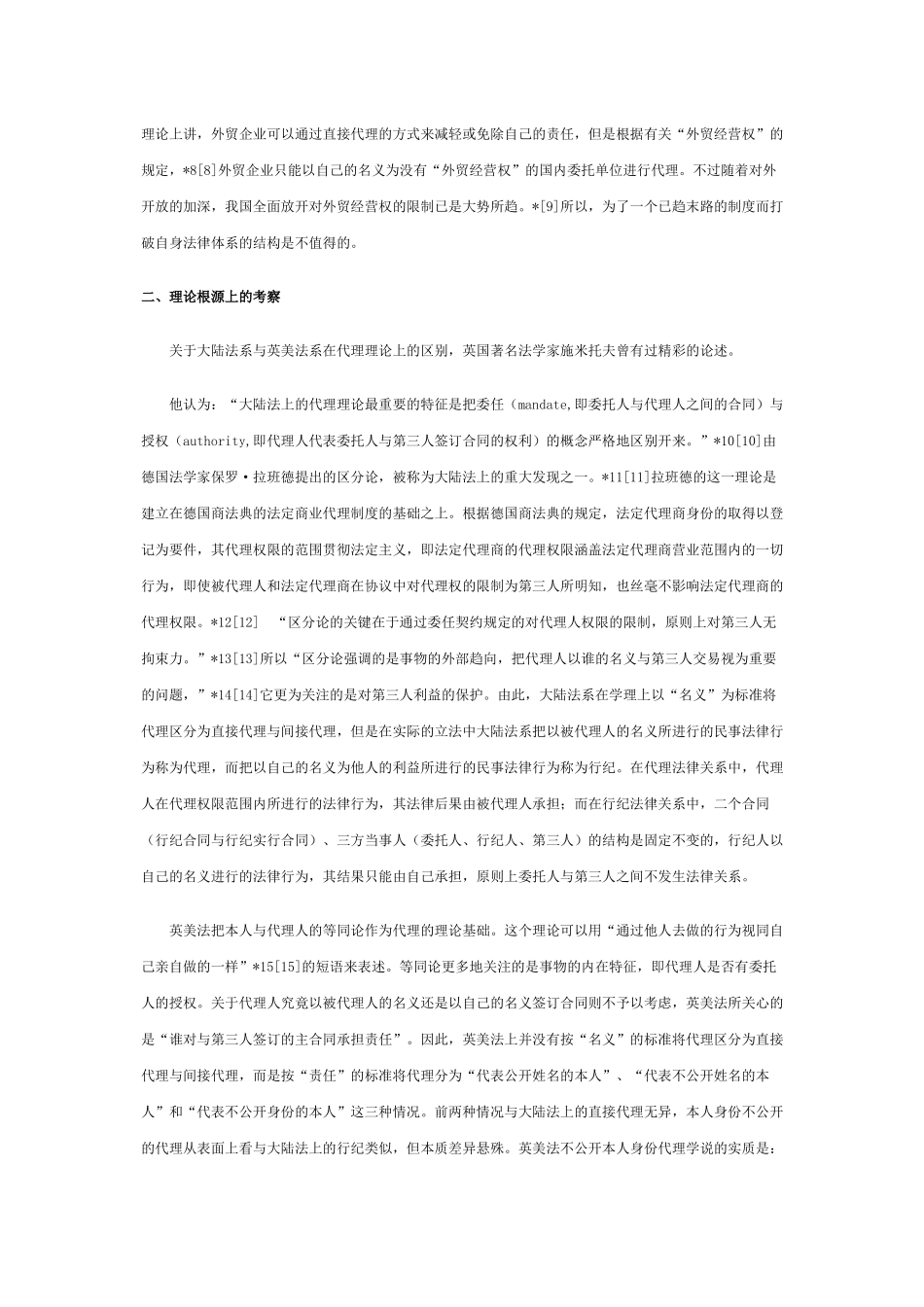第 402 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第 403 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中,没有哪一个分支的法学理论的差异像代理这样大。国际商会在其制订的《商业代理指南》中指出:“这些问题(代理问题)是国际贸易领域众多争议产生的源泉。”国际社会也曾多次起草有关代理的公约,但终因两大法系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异过大而未能通过。*1[1]所以在国际社会就代理问题达成共识之前,我国合同法在委任合同一章引入英美法的“本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制度”就越发的引人注目。在我国学界,关于代理理论的争议一直存在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2[2]从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看,*3[3]英美派的意见已逐渐占据上风,尤其是随着合同法的颁布实施,似乎有盖棺定论的趋势。但是纵观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近制订的几部有重要影响的民法典,其中有关代理的规定却仍然固守大陆法的传统。*4[4]所以对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作进一步的反思,将会对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有所助益。一、立法沿革上的考察 我国合同法在正式审议通过之前,曾经有过三个重要的草稿,即 1995 年的“试拟稿”、1997 年的“征求意见稿”以及 1998 年的“草案”。通过对这些草案的考察,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我国立法在代理问题上的变迁,以及引进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真正目的。 在“试拟稿”中也有关于委托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的规定,但并不是规定在委任合同中,而是规定在行纪合同的第一节“一般规定”中,同时行纪合同的第二节专门规定了“对外贸易行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