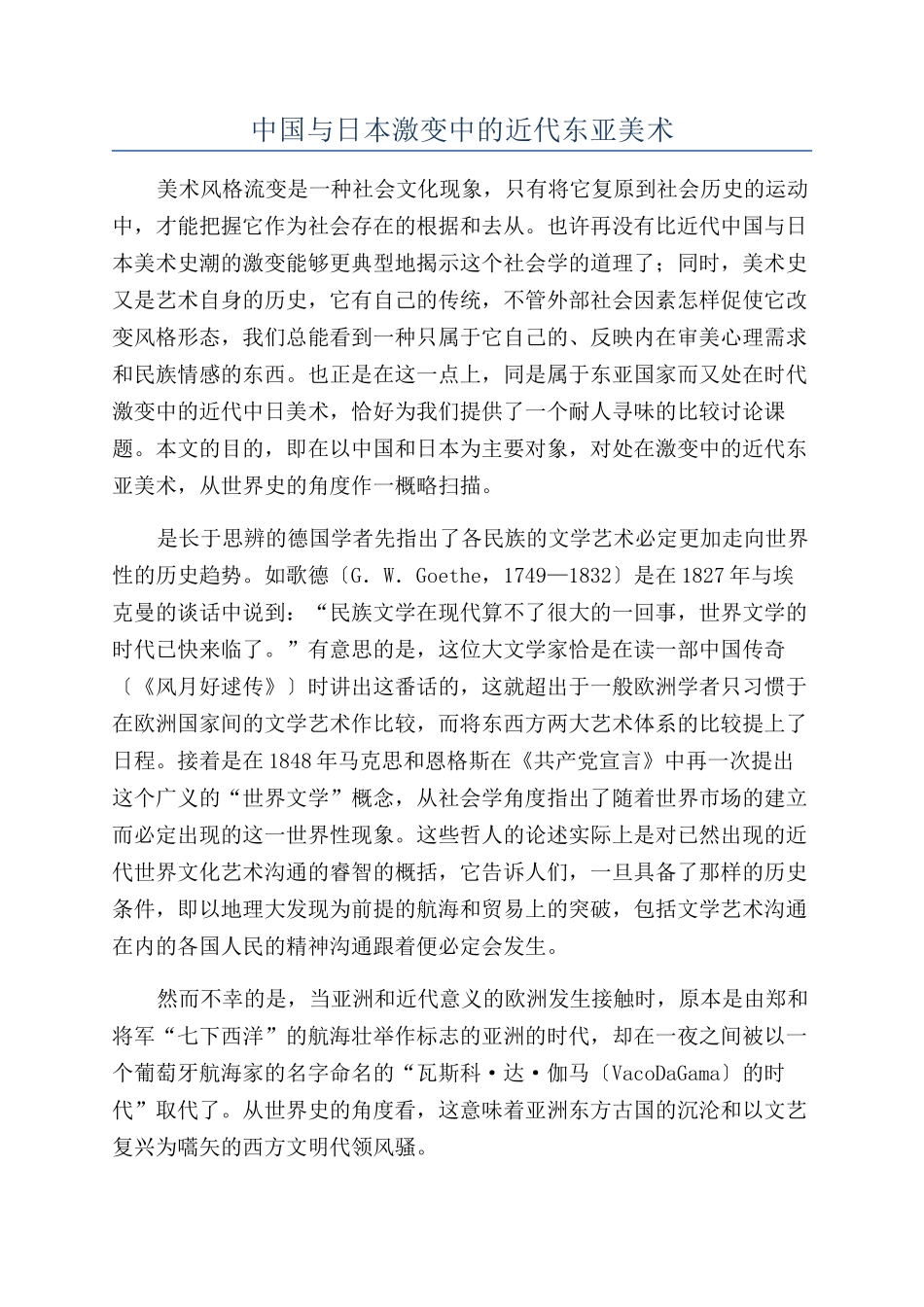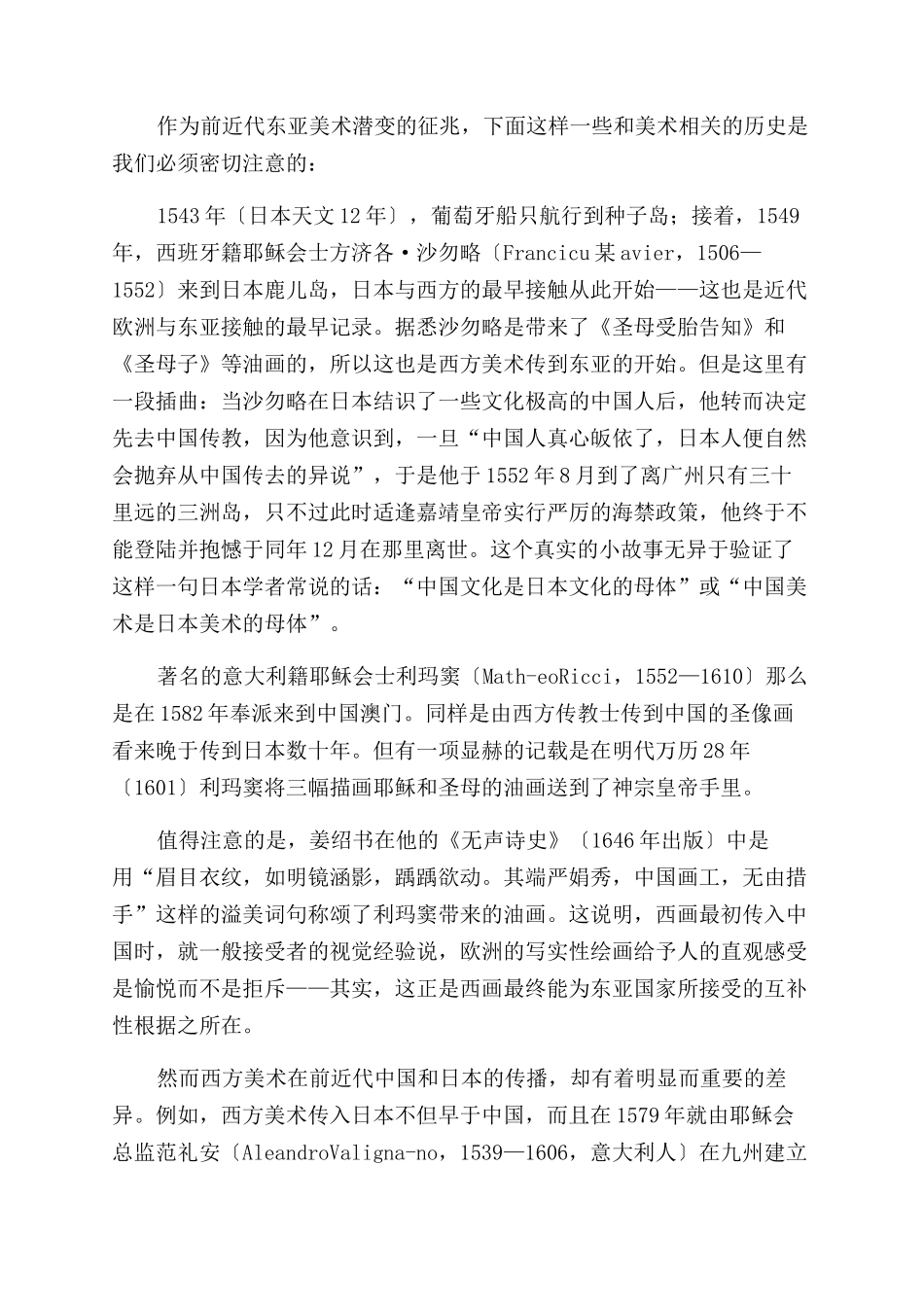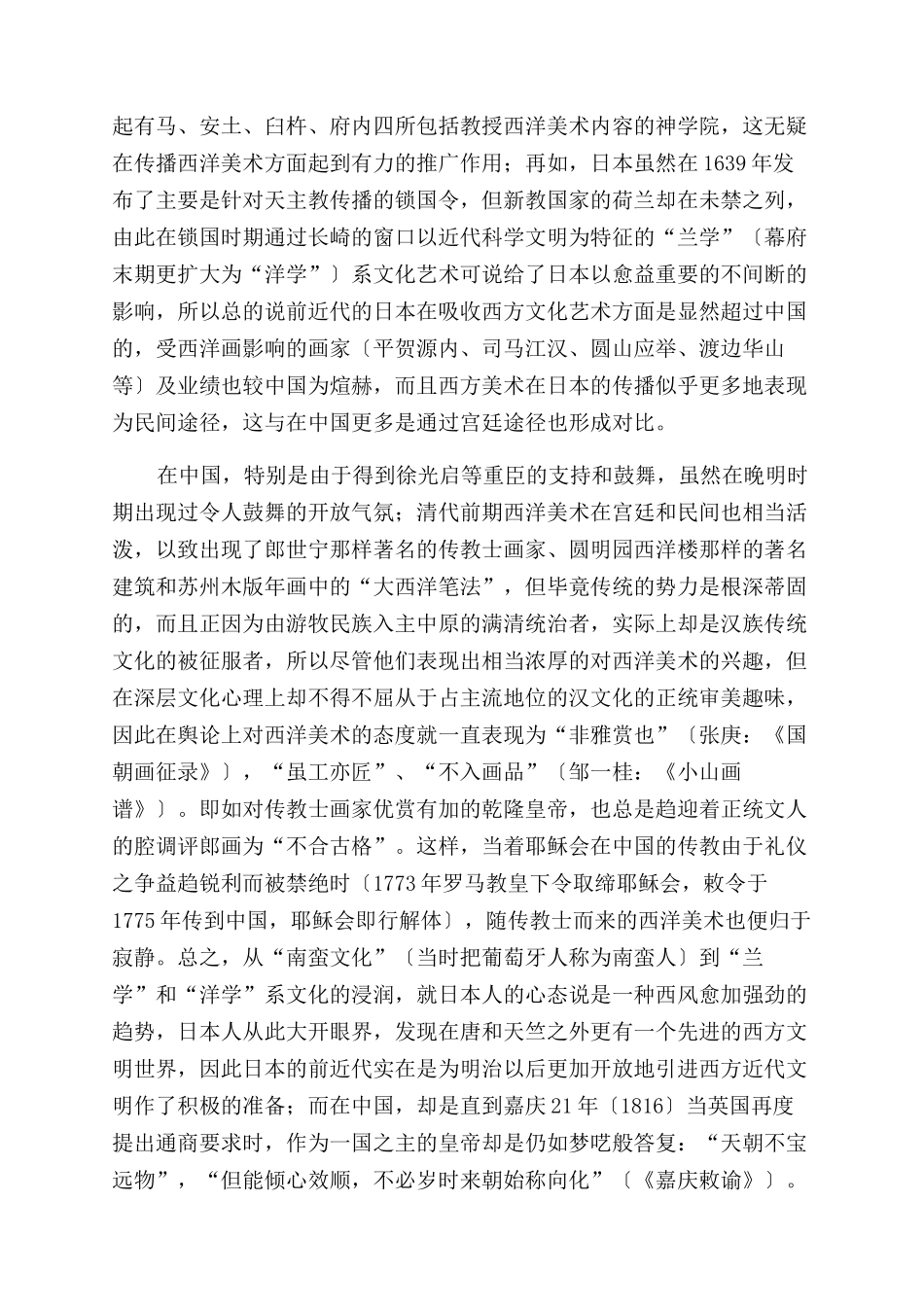中国与日本激变中的近代东亚美术美术风格流变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只有将它复原到社会历史的运动中,才能把握它作为社会存在的根据和去从。也许再没有比近代中国与日本美术史潮的激变能够更典型地揭示这个社会学的道理了;同时,美术史又是艺术自身的历史,它有自己的传统,不管外部社会因素怎样促使它改变风格形态,我们总能看到一种只属于它自己的、反映内在审美心理需求和民族情感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同是属于东亚国家而又处在时代激变中的近代中日美术,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比较讨论课题。本文的目的,即在以中国和日本为主要对象,对处在激变中的近代东亚美术,从世界史的角度作一概略扫描。是长于思辨的德国学者先指出了各民族的文学艺术必定更加走向世界性的历史趋势。如歌德〔G.W.Goethe,1749—1832〕是在 1827 年与埃克曼的谈话中说到:“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有意思的是,这位大文学家恰是在读一部中国传奇〔《风月好逑传》〕时讲出这番话的,这就超出于一般欧洲学者只习惯于在欧洲国家间的文学艺术作比较,而将东西方两大艺术体系的比较提上了日程。接着是在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再一次提出这个广义的“世界文学”概念,从社会学角度指出了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而必定出现的这一世界性现象。这些哲人的论述实际上是对已然出现的近代世界文化艺术沟通的睿智的概括,它告诉人们,一旦具备了那样的历史条件,即以地理大发现为前提的航海和贸易上的突破,包括文学艺术沟通在内的各国人民的精神沟通跟着便必定会发生。然而不幸的是,当亚洲和近代意义的欧洲发生接触时,原本是由郑和将军“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作标志的亚洲的时代,却在一夜之间被以一个葡萄牙航海家的名字命名的“瓦斯科·达·伽马〔VacoDaGama〕的时代”取代了。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亚洲东方古国的沉沦和以文艺复兴为嚆矢的西方文明代领风骚。作为前近代东亚美术潜变的征兆,下面这样一些和美术相关的历史是我们必须密切注意的:1543 年〔日本天文 12 年〕,葡萄牙船只航行到种子岛;接着,1549年,西班牙籍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cu 某 avier,1506—1552〕来到日本鹿儿岛,日本与西方的最早接触从此开始——这也是近代欧洲与东亚接触的最早记录。据悉沙勿略是带来了《圣母受胎告知》和《圣母子》等油画的,所以这也是西方美术传到东亚的开始。但是这里有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