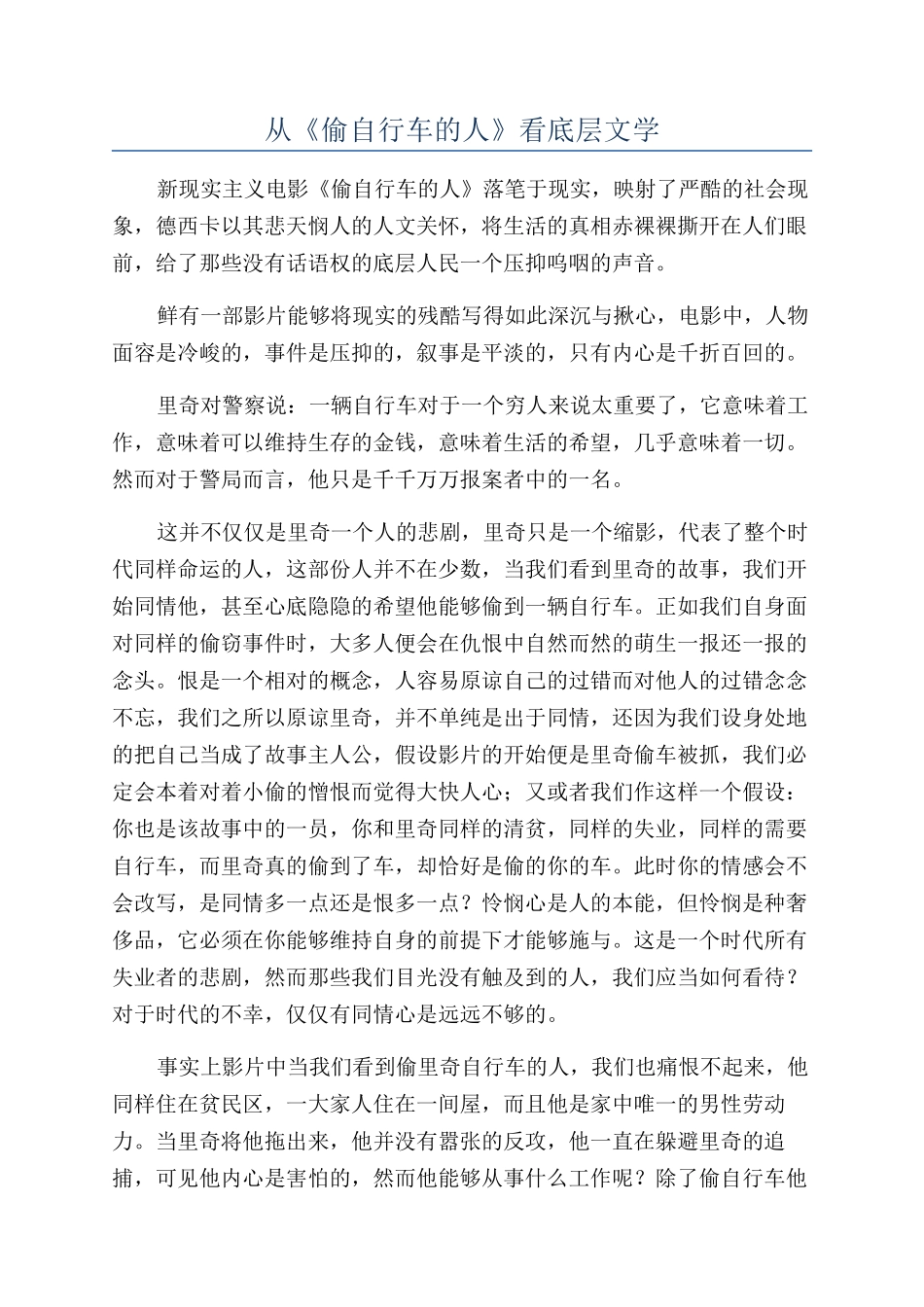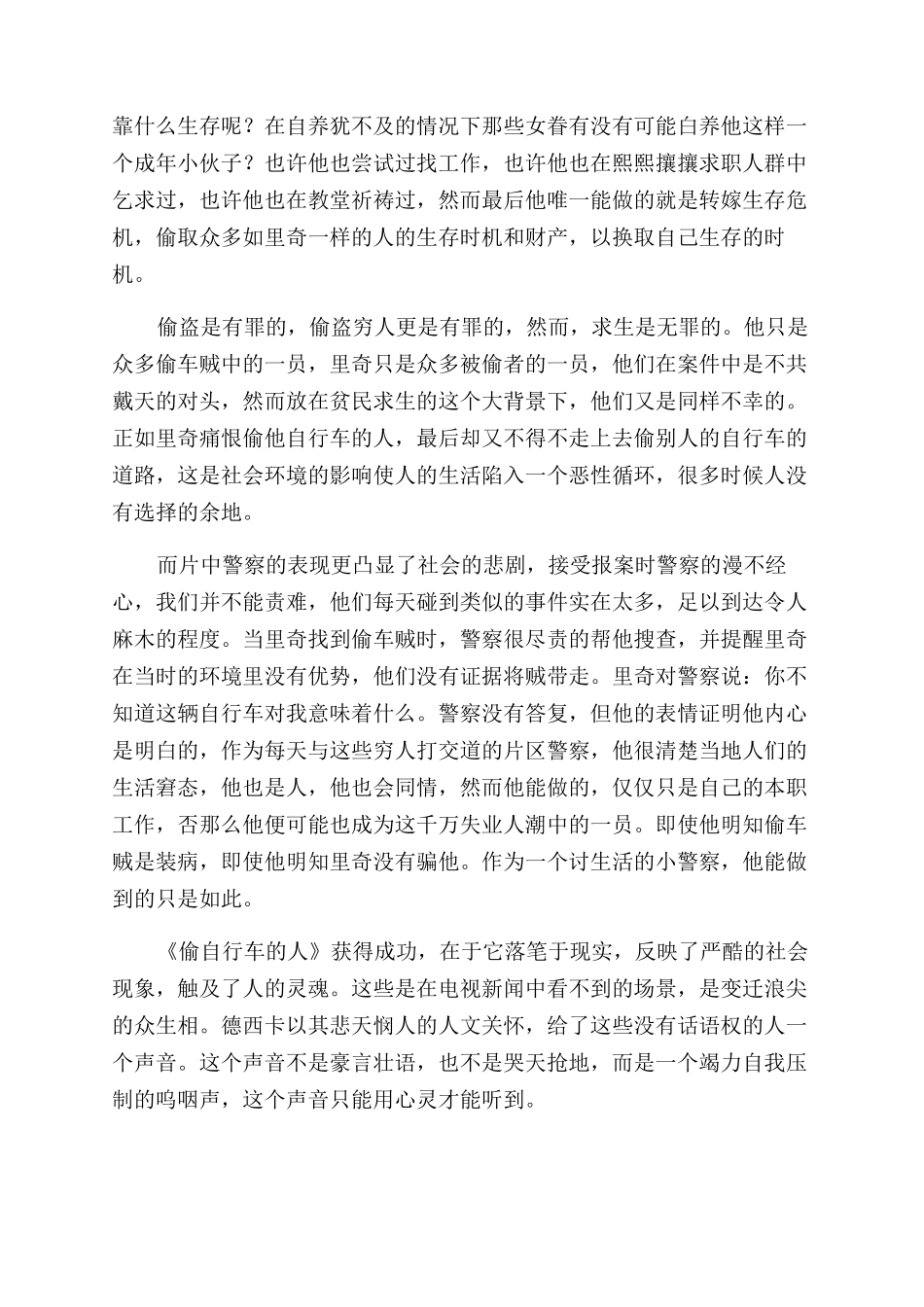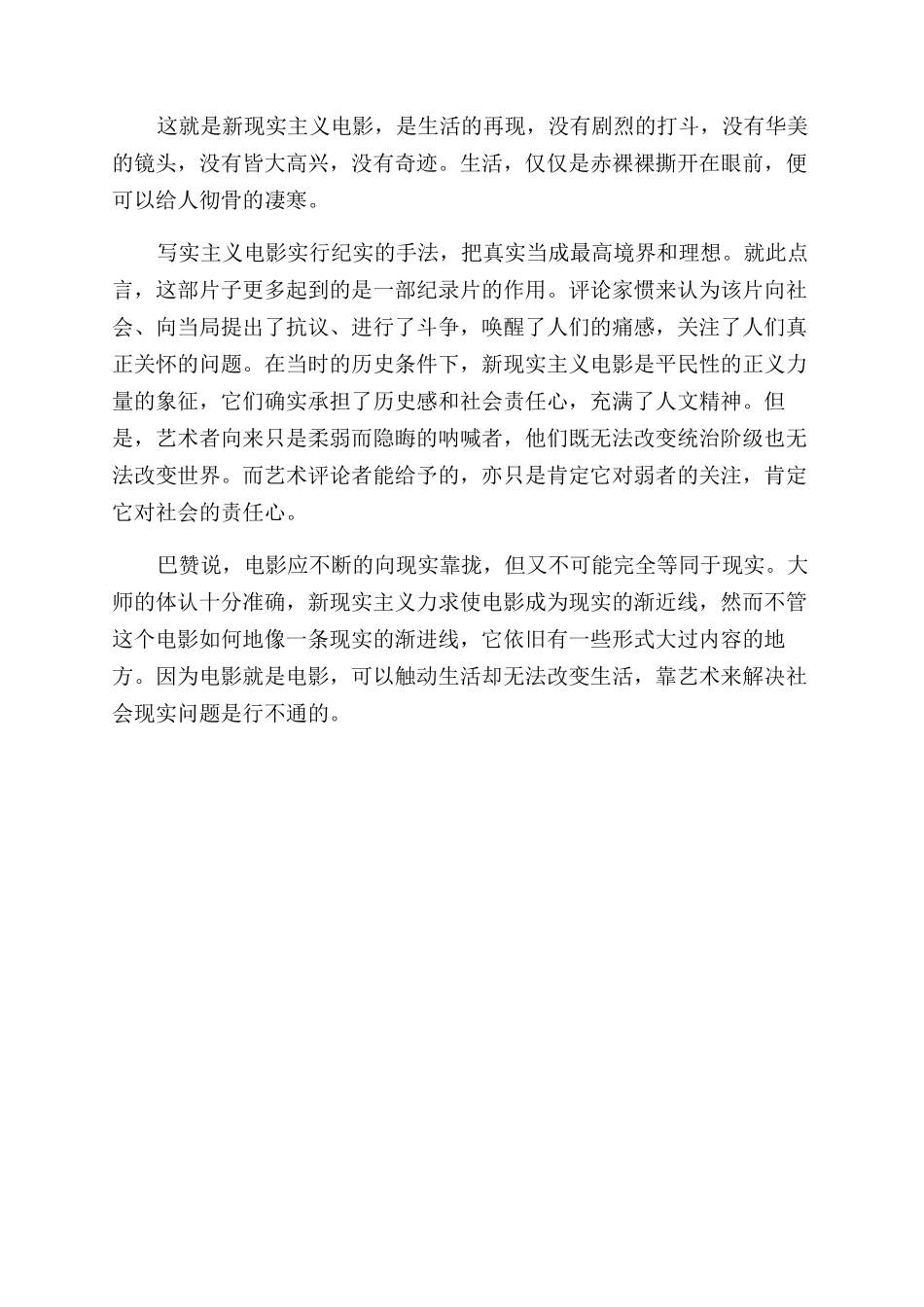从《偷自行车的人》看底层文学新现实主义电影《偷自行车的人》落笔于现实,映射了严酷的社会现象,德西卡以其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将生活的真相赤裸裸撕开在人们眼前,给了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底层人民一个压抑呜咽的声音。鲜有一部影片能够将现实的残酷写得如此深沉与揪心,电影中,人物面容是冷峻的,事件是压抑的,叙事是平淡的,只有内心是千折百回的。里奇对警察说:一辆自行车对于一个穷人来说太重要了,它意味着工作,意味着可以维持生存的金钱,意味着生活的希望,几乎意味着一切。然而对于警局而言,他只是千千万万报案者中的一名。这并不仅仅是里奇一个人的悲剧,里奇只是一个缩影,代表了整个时代同样命运的人,这部份人并不在少数,当我们看到里奇的故事,我们开始同情他,甚至心底隐隐的希望他能够偷到一辆自行车。正如我们自身面对同样的偷窃事件时,大多人便会在仇恨中自然而然的萌生一报还一报的念头。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人容易原谅自己的过错而对他人的过错念念不忘,我们之所以原谅里奇,并不单纯是出于同情,还因为我们设身处地的把自己当成了故事主人公,假设影片的开始便是里奇偷车被抓,我们必定会本着对着小偷的憎恨而觉得大快人心;又或者我们作这样一个假设:你也是该故事中的一员,你和里奇同样的清贫,同样的失业,同样的需要自行车,而里奇真的偷到了车,却恰好是偷的你的车。此时你的情感会不会改写,是同情多一点还是恨多一点?怜悯心是人的本能,但怜悯是种奢侈品,它必须在你能够维持自身的前提下才能够施与。这是一个时代所有失业者的悲剧,然而那些我们目光没有触及到的人,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对于时代的不幸,仅仅有同情心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影片中当我们看到偷里奇自行车的人,我们也痛恨不起来,他同样住在贫民区,一大家人住在一间屋,而且他是家中唯一的男性劳动力。当里奇将他拖出来,他并没有嚣张的反攻,他一直在躲避里奇的追捕,可见他内心是害怕的,然而他能够从事什么工作呢?除了偷自行车他靠什么生存呢?在自养犹不及的情况下那些女眷有没有可能白养他这样一个成年小伙子?也许他也尝试过找工作,也许他也在熙熙攘攘求职人群中乞求过,也许他也在教堂祈祷过,然而最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转嫁生存危机,偷取众多如里奇一样的人的生存时机和财产,以换取自己生存的时机。偷盗是有罪的,偷盗穷人更是有罪的,然而,求生是无罪的。他只是众多偷车贼中的一员,里奇只是众多被偷者的一员,他们在案件中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