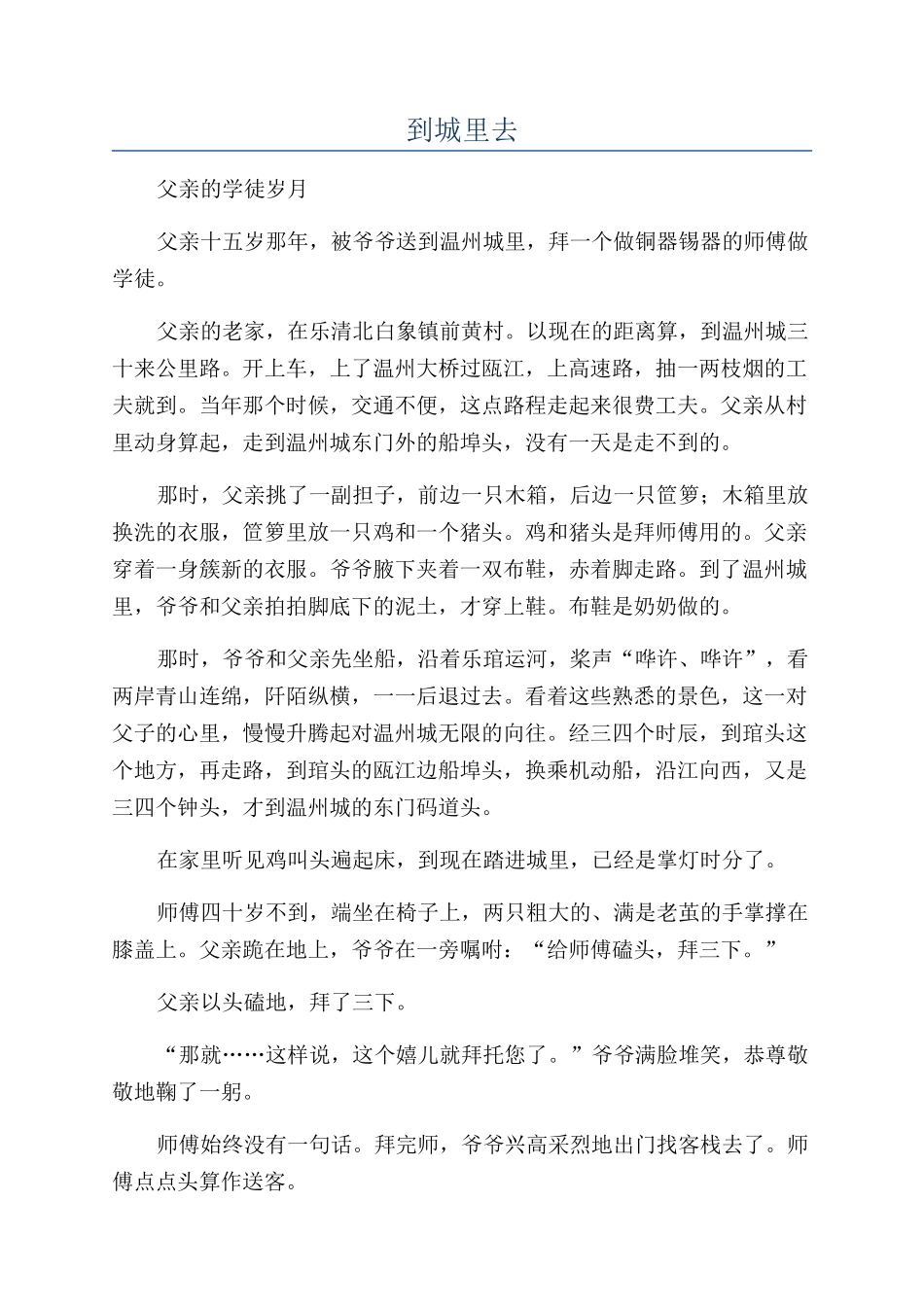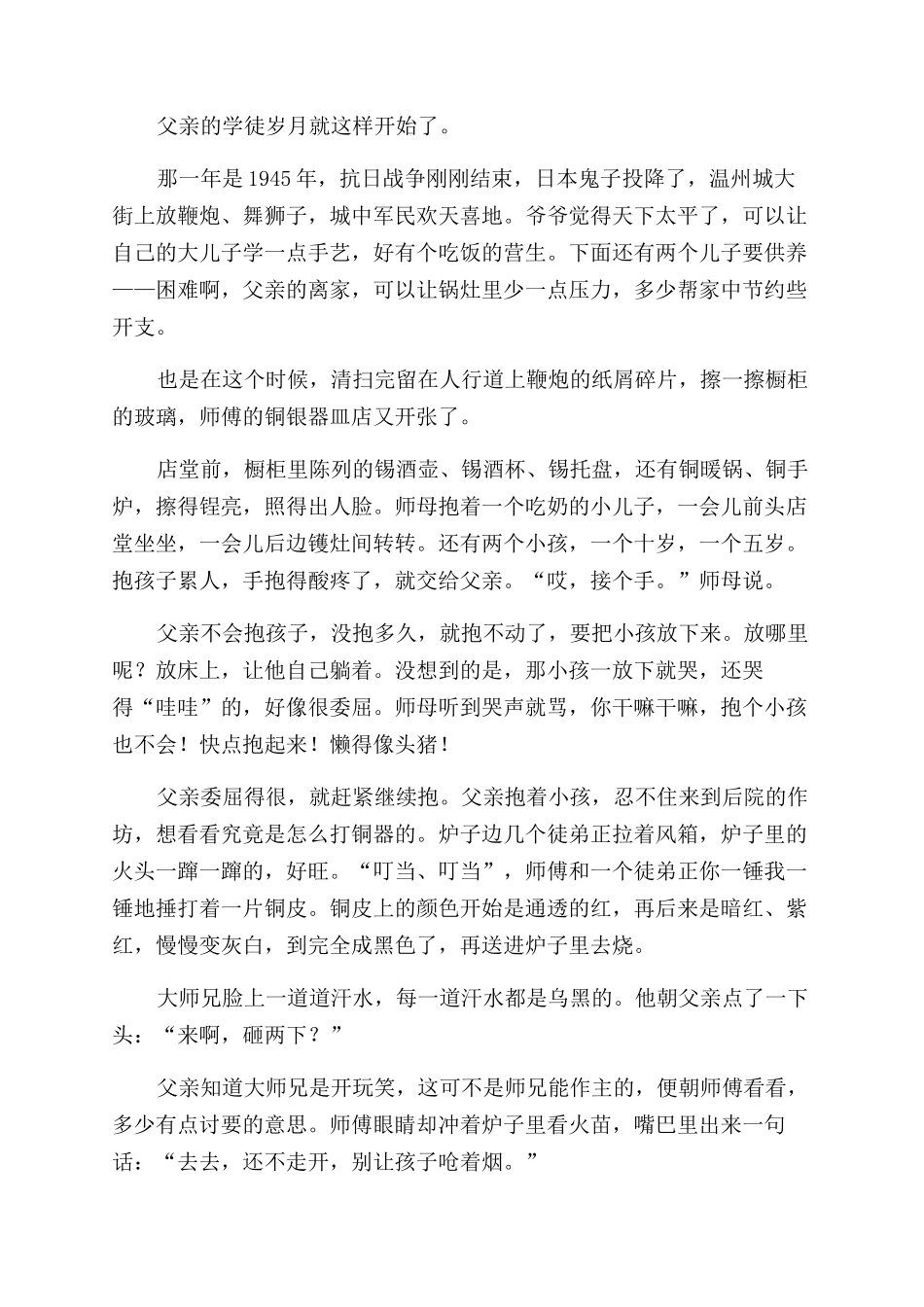到城里去父亲的学徒岁月父亲十五岁那年,被爷爷送到温州城里,拜一个做铜器锡器的师傅做学徒。父亲的老家,在乐清北白象镇前黄村。以现在的距离算,到温州城三十来公里路。开上车,上了温州大桥过瓯江,上高速路,抽一两枝烟的工夫就到。当年那个时候,交通不便,这点路程走起来很费工夫。父亲从村里动身算起,走到温州城东门外的船埠头,没有一天是走不到的。那时,父亲挑了一副担子,前边一只木箱,后边一只笸箩;木箱里放换洗的衣服,笸箩里放一只鸡和一个猪头。鸡和猪头是拜师傅用的。父亲穿着一身簇新的衣服。爷爷腋下夹着一双布鞋,赤着脚走路。到了温州城里,爷爷和父亲拍拍脚底下的泥土,才穿上鞋。布鞋是奶奶做的。那时,爷爷和父亲先坐船,沿着乐琯运河,桨声“哗许、哗许”,看两岸青山连绵,阡陌纵横,一一后退过去。看着这些熟悉的景色,这一对父子的心里,慢慢升腾起对温州城无限的向往。经三四个时辰,到琯头这个地方,再走路,到琯头的瓯江边船埠头,换乘机动船,沿江向西,又是三四个钟头,才到温州城的东门码道头。在家里听见鸡叫头遍起床,到现在踏进城里,已经是掌灯时分了。师傅四十岁不到,端坐在椅子上,两只粗大的、满是老茧的手掌撑在膝盖上。父亲跪在地上,爷爷在一旁嘱咐:“给师傅磕头,拜三下。”父亲以头磕地,拜了三下。“那就……这样说,这个嬉儿就拜托您了。”爷爷满脸堆笑,恭尊敬敬地鞠了一躬。师傅始终没有一句话。拜完师,爷爷兴高采烈地出门找客栈去了。师傅点点头算作送客。父亲的学徒岁月就这样开始了。那一年是 1945 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日本鬼子投降了,温州城大街上放鞭炮、舞狮子,城中军民欢天喜地。爷爷觉得天下太平了,可以让自己的大儿子学一点手艺,好有个吃饭的营生。下面还有两个儿子要供养——困难啊,父亲的离家,可以让锅灶里少一点压力,多少帮家中节约些开支。也是在这个时候,清扫完留在人行道上鞭炮的纸屑碎片,擦一擦橱柜的玻璃,师傅的铜银器皿店又开张了。店堂前,橱柜里陈列的锡酒壶、锡酒杯、锡托盘,还有铜暖锅、铜手炉,擦得锃亮,照得出人脸。师母抱着一个吃奶的小儿子,一会儿前头店堂坐坐,一会儿后边镬灶间转转。还有两个小孩,一个十岁,一个五岁。抱孩子累人,手抱得酸疼了,就交给父亲。“哎,接个手。”师母说。父亲不会抱孩子,没抱多久,就抱不动了,要把小孩放下来。放哪里呢?放床上,让他自己躺着。没想到的是,那小孩一放下就哭,还哭得“哇哇”的,好像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