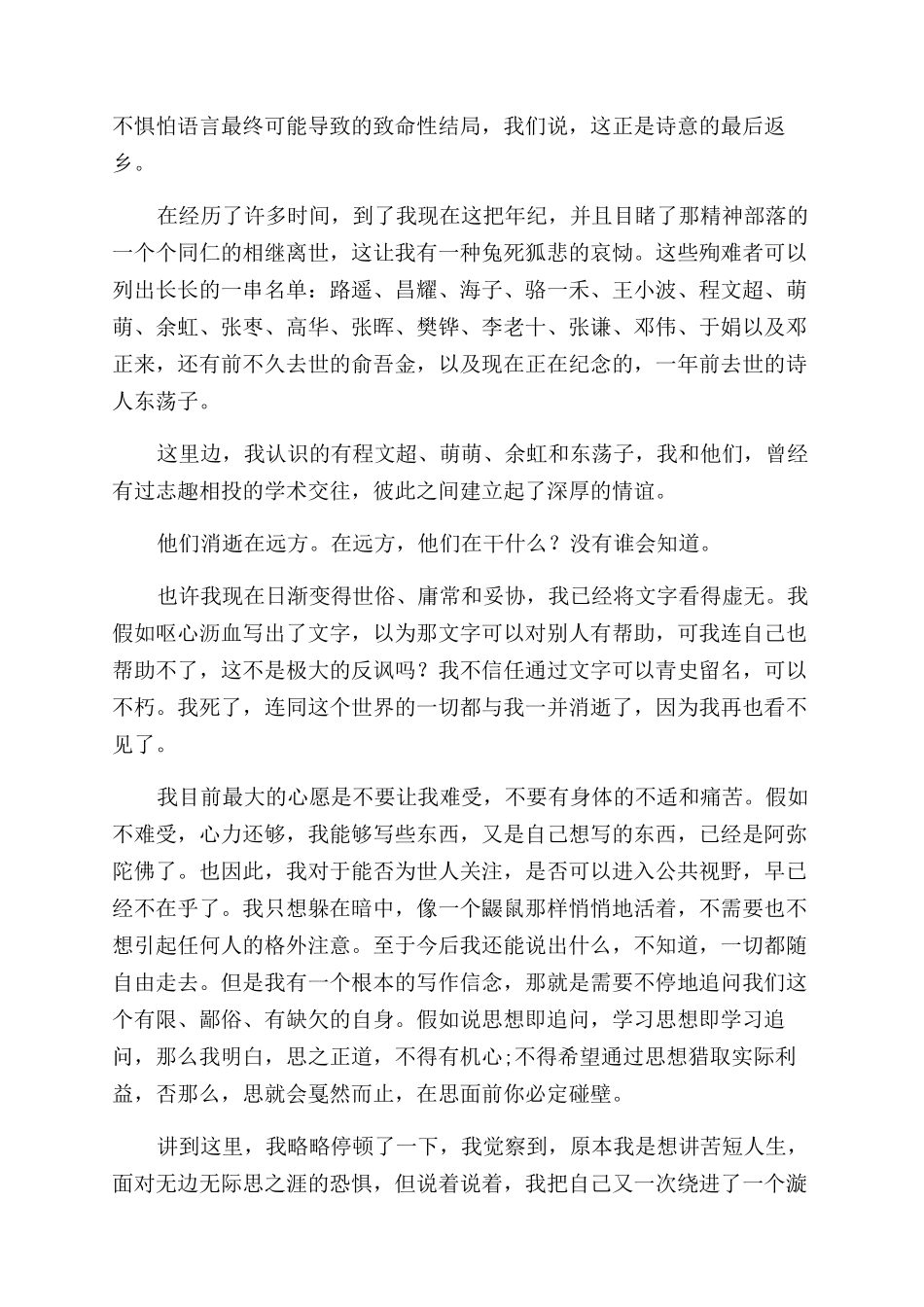学人之殇一、他们消逝在远方2024 年 10 月 11 日,我去增城参加“首届东荡子诗歌奖颁奖会”。这天下午是研讨会,会议的题目是《诗歌与个人命运》。说到个人命运与写作的关系,我是这么发言的。在我年轻的时代,我对于诗与思,语言是日常最高的生存事件,原创性书写等等词语,充满着颤栗般的迷恋。那时,我与我的朋友们,在真诚地讨论和欣赏那些伟大的天才,他们是尼采、克尔凯郭尔、叔本华、荷尔德林、诺瓦丽斯、里尔克、卡夫卡、普鲁斯特等人。这是以踬颠、趔趄地飞行于苍穹之上的天才者,电光闪过,漫天辉煌。那天才者,他们易采纳敏感孤冷之方式,甚至不惜以自戕与消灭的激情震撼一代人麻木的神经。天才总是常与孤独和焦虑为伴,这样就会常常损伤他们的身体。他们显得面孔削瘦,体弱多病,仿佛那躯体无力承担沉重而卓越的思想。这天才者的神经极其敏感,掉在地上的一根针也能让他们心惊胆战,从而触发情绪以及想象,并且绵延出瑰丽的文字。当然,在人类思想和艺术的开展史上,除了天才,还有大师级的人,这是康德、托尔斯泰、海德格尔、罗丹、伽达默尔、雅斯贝斯等人,这些大师行走于沉厚而坚实的大地,他们呼吸平稳,生活规律,致力于启蒙理性。他们在宁静与安详中活到足够的寿数。天才与大师,都以独异的荣耀,照亮了人类混暝的暗夜。当年的我们,却更执拗地欣赏和追慕天才的足迹。我们动情地说,残破的肉身,正好成为了语言的传送地。我们说,是身体的病理学特征,在腐殖之地,孕育和浇灌了诗与语言的璀璨奇葩。那时,我们年轻,身体还没有真正的痛苦,疾病还没来得及发生,因此我们才敢于奢侈地谈论有限以及死亡。死亡的黑色似乎经由语言的描述而笼罩上一层金色。我们全然不惧怕语言最终可能导致的致命性结局,我们说,这正是诗意的最后返乡。在经历了许多时间,到了我现在这把年纪,并且目睹了那精神部落的一个个同仁的相继离世,这让我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哀恸。这些殉难者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单:路遥、昌耀、海子、骆一禾、王小波、程文超、萌萌、余虹、张枣、高华、张晖、樊铧、李老十、张谦、邓伟、于娟以及邓正来,还有前不久去世的俞吾金,以及现在正在纪念的,一年前去世的诗人东荡子。这里边,我认识的有程文超、萌萌、余虹和东荡子,我和他们,曾经有过志趣相投的学术交往,彼此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他们消逝在远方。在远方,他们在干什么?没有谁会知道。也许我现在日渐变得世俗、庸常和妥协,我已经将文字看得虚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