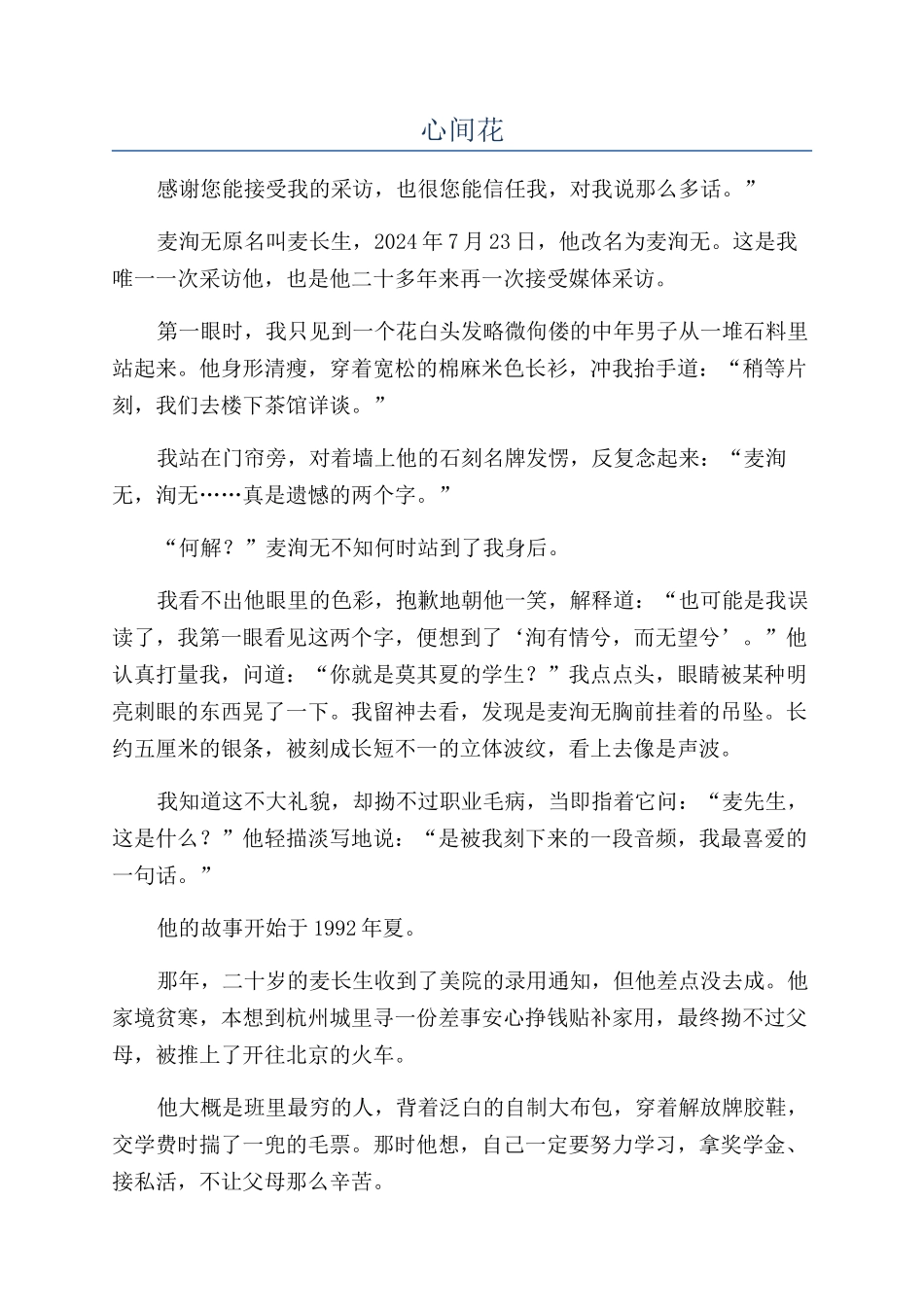心间花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也很您能信任我,对我说那么多话。”麦洵无原名叫麦长生,2024 年 7 月 23 日,他改名为麦洵无。这是我唯一一次采访他,也是他二十多年来再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第一眼时,我只见到一个花白头发略微佝偻的中年男子从一堆石料里站起来。他身形清瘦,穿着宽松的棉麻米色长衫,冲我抬手道:“稍等片刻,我们去楼下茶馆详谈。”我站在门帘旁,对着墙上他的石刻名牌发愣,反复念起来:“麦洵无,洵无……真是遗憾的两个字。”“何解?”麦洵无不知何时站到了我身后。我看不出他眼里的色彩,抱歉地朝他一笑,解释道:“也可能是我误读了,我第一眼看见这两个字,便想到了‘洵有情兮,而无望兮’。”他认真打量我,问道:“你就是莫其夏的学生?”我点点头,眼睛被某种明亮刺眼的东西晃了一下。我留神去看,发现是麦洵无胸前挂着的吊坠。长约五厘米的银条,被刻成长短不一的立体波纹,看上去像是声波。我知道这不大礼貌,却拗不过职业毛病,当即指着它问:“麦先生,这是什么?”他轻描淡写地说:“是被我刻下来的一段音频,我最喜爱的一句话。”他的故事开始于 1992 年夏。那年,二十岁的麦长生收到了美院的录用通知,但他差点没去成。他家境贫寒,本想到杭州城里寻一份差事安心挣钱贴补家用,最终拗不过父母,被推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他大概是班里最穷的人,背着泛白的自制大布包,穿着解放牌胶鞋,交学费时揣了一兜的毛票。那时他想,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拿奖学金、接私活,不让父母那么辛苦。莫其夏也是那年被录用的,不过他们专业不同,麦长生学雕塑,莫其夏是学美术史论,写文章做批判的。麦长生第一次见到莫其夏,是在一年一度的校展览上。那天麦长生站在自己的作品不远处,看着一群美术史论专业的学生走来,莫其夏站在人群中间,显得尤为扎眼。她手持号码牌,喃喃念着“102 号”,低着头一个个寻找。她在麦长生的作品前停了下来。那是在展館的角落,展台上摆着一块孤零零的灰色石头,石头上开出了一朵石花。她照着展品铭牌念道:“102 号‘大石开花’,嗯……好美的花。”“谢谢。”麦长生说。莫其夏被他吓了一跳,一转身看见一个清瘦的少年,穿着最简单的白色短袖上衣,头发短得贴着头皮,一根根像刺般立着。最要紧的,是他那双眼睛,如一团墨,洁净而无欲。莫其夏飞快地回头瞥了一眼名牌,将他的名字念出来:“麦长生?”麦长生点点头,淡漠地答她:“嗯。”麦长生没有说话,而是皱起眉头,心里想着这个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