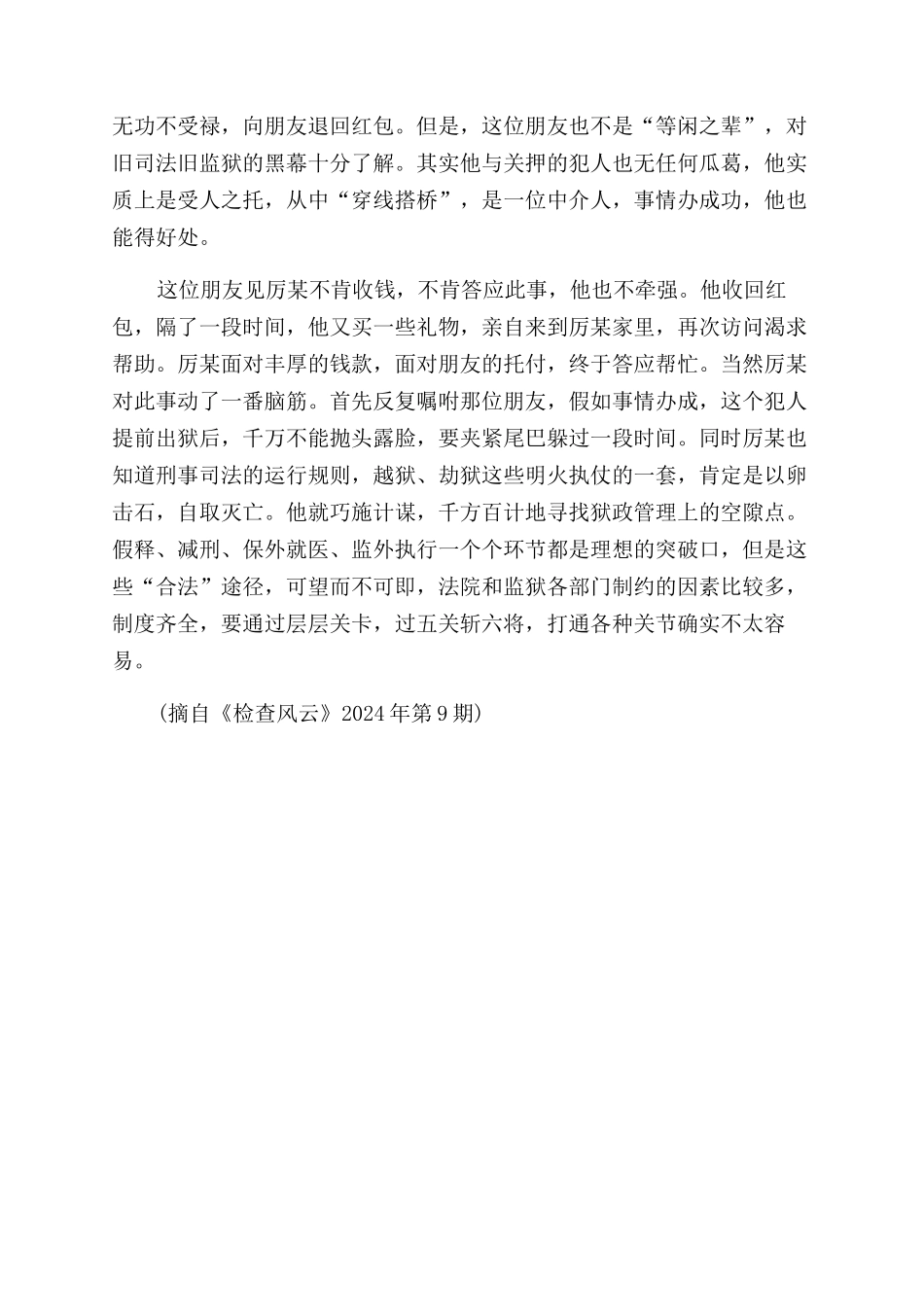提篮桥监狱60年前的一桩舞弊案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提篮桥监狱犯人进出量相当大,在押犯人最高达七八千人左右,其中短刑犯占了较大比例。为了确保监管安全,做到及时收押,准时释放,监狱里也形成了一套比较法律规范的管理措施。如新收、释放十分注重犯人指纹的验证:不让犯人知道监狱的大门和方位,在监狱新收监内设计成左一个拐弯、右一个拐弯,左一道门、右一道门地进入狱区的通道;犯人释放时,不让他们直接走出监狱大门,把他们押上棚车送出监狱;看守人员进出监狱四大门实行搜身;对看守人员作了许多禁止性的规定,如不准玩忽职守,不准另谋私人营业,不准负债,不准收受囚犯及家属的礼物,不准与囚犯串通交易、亲昵习熟,不准代囚犯携带信件、传达消息,不准外表褴褛等等。然而,再好的篱笆墙,也有漏洞可以钻。厉某当时是分管监狱犯人出入监工作的人员,家住提篮桥监狱旁边,平常交际的人员较广,朋友较多,他有文化,在监狱工作多年,对各类狱政业务也比较熟悉。有一次,厉某的一位朋友在上海一家高档饭店请他吃饭,当酒足饭饱之后,那位朋友给厉某送上一个丰厚的红包,和颜悦色地请厉某帮个小忙,请厉对关在狱内的一个犯人网开一面。开始厉某认为,这位朋友无非是给在押犯人送点板烟、酱鸭、蹄髈等一些食品,改善一下生活或者传递一些消息,看守、职员拿点好处,囚犯和家属也得到实惠,这些事虽然在旧监狱是家常便饭,但是在监狱制度上也是明文禁止的。假如被人举报,轻者扣工资,重者丢饭碗。但是在高额酬金面前,这种事情实际上是堵不住、禁不止的旧狱通病。所以,厉某借着酒兴一口答应下来。但是当那位朋友提出要把狱中的犯人提前放出来,厉某感到十分烫手,这个事情实在难做,他无能为力。这种事在旧司法界称做“得钱买放”“贪赃枉法”。假如东窗事发,当事人要坐班房吃官司的。厉某毕竟是个有头脑有文化的人,在司法界内也跌打滚爬了不少岁月。他也知道“牢头禁子”的高压线,哪些可以小弄弄,打打擦边球,哪些千万不能沾边。所以厉某赶忙推托自己能力有限,无功不受禄,向朋友退回红包。但是,这位朋友也不是“等闲之辈”,对旧司法旧监狱的黑幕十分了解。其实他与关押的犯人也无任何瓜葛,他实质上是受人之托,从中“穿线搭桥”,是一位中介人,事情办成功,他也能得好处。这位朋友见厉某不肯收钱,不肯答应此事,他也不牵强。他收回红包,隔了一段时间,他又买一些礼物,亲自来到厉某家里,再次访问渴求帮助。厉某面对丰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