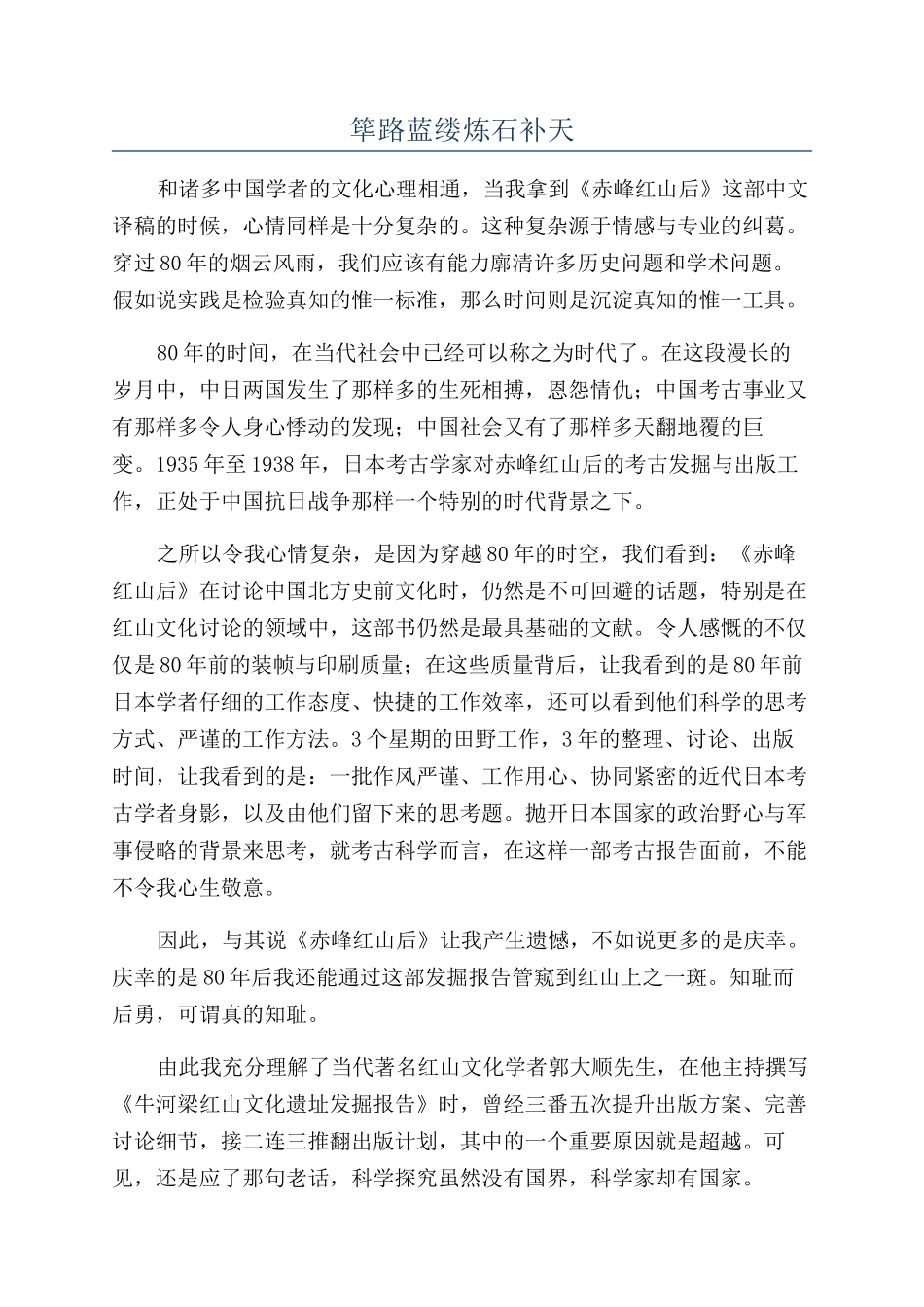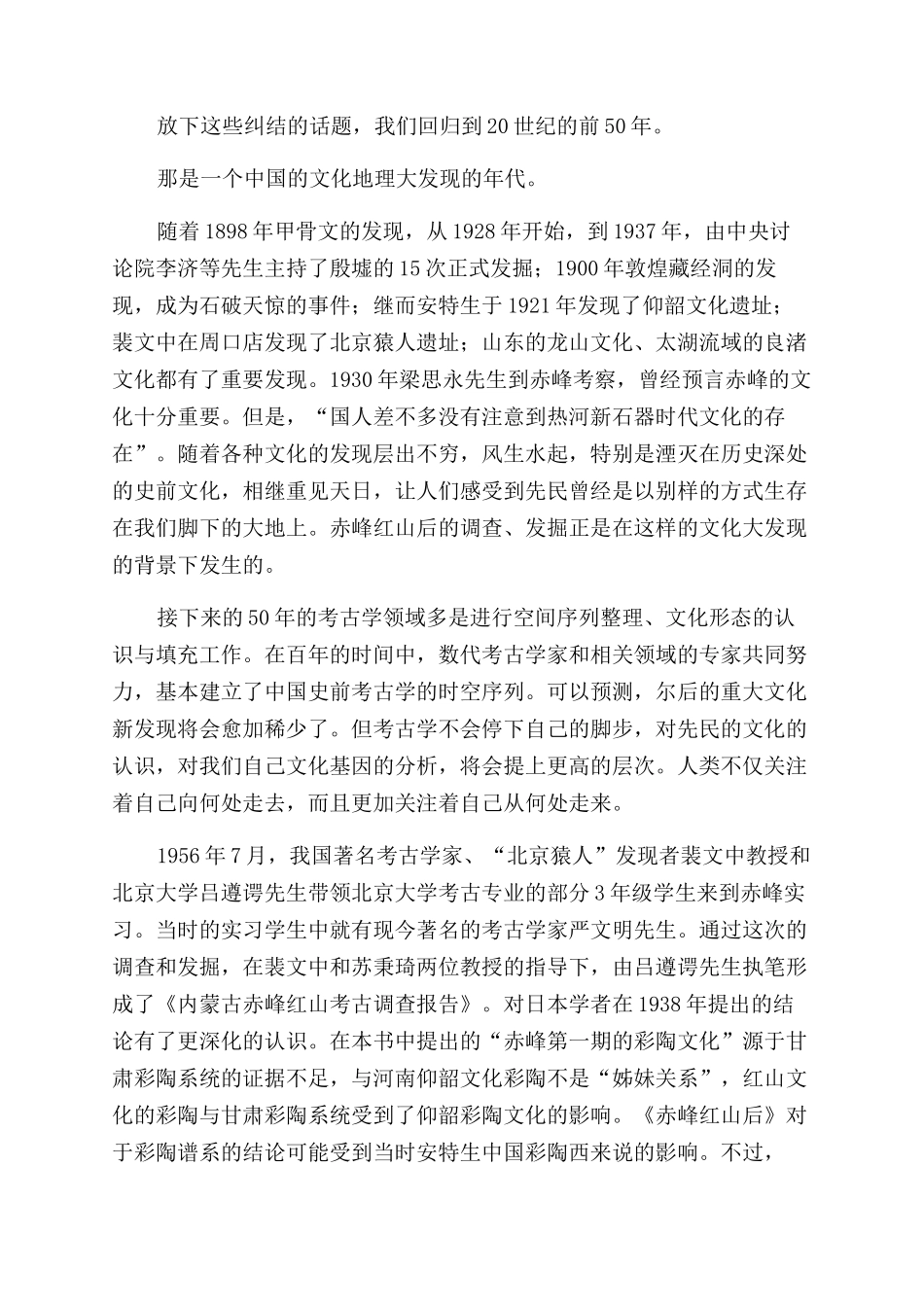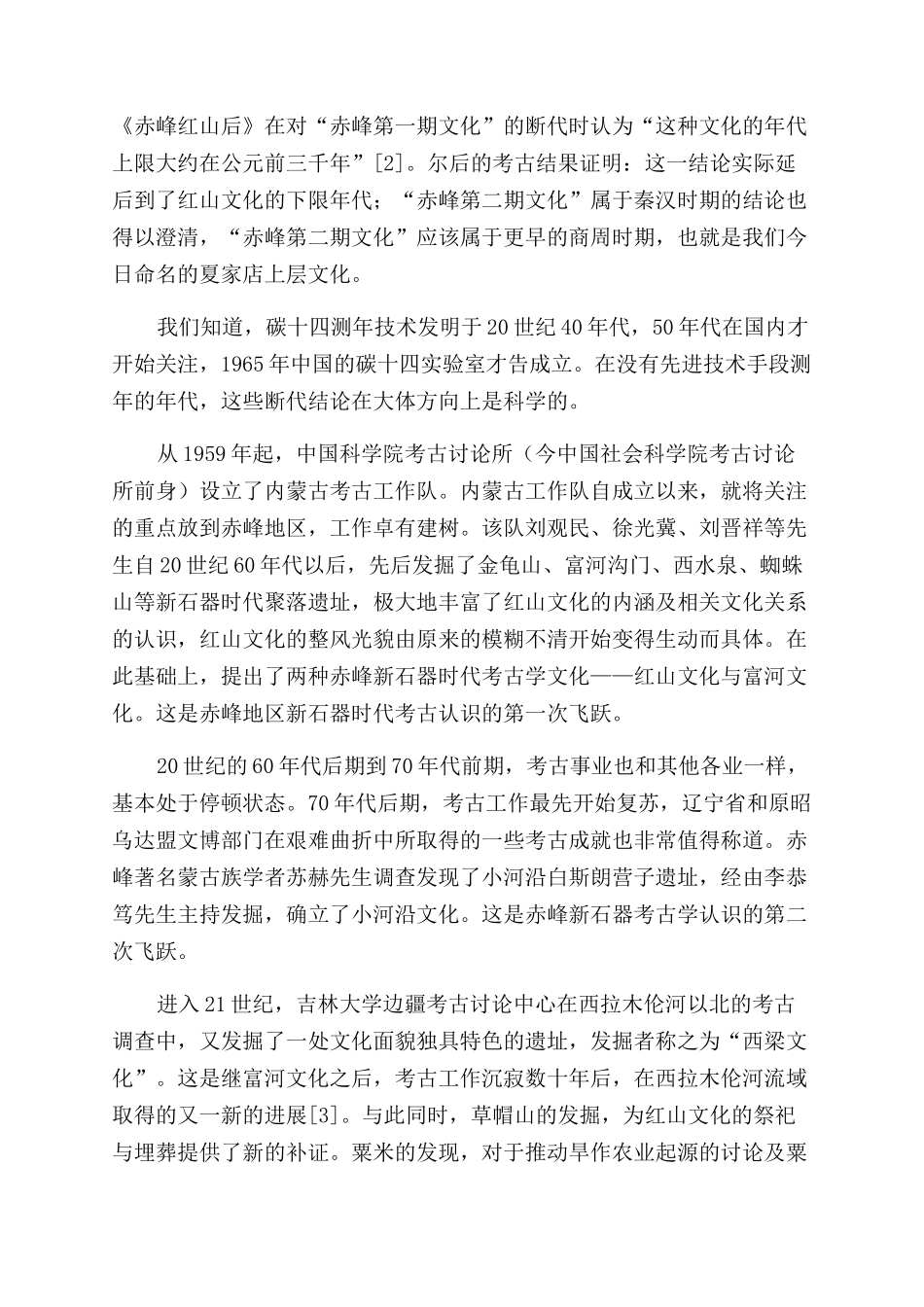筚路蓝缕炼石补天和诸多中国学者的文化心理相通,当我拿到《赤峰红山后》这部中文译稿的时候,心情同样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复杂源于情感与专业的纠葛。穿过 80 年的烟云风雨,我们应该有能力廓清许多历史问题和学术问题。假如说实践是检验真知的惟一标准,那么时间则是沉淀真知的惟一工具。80 年的时间,在当代社会中已经可以称之为时代了。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中日两国发生了那样多的生死相搏,恩怨情仇;中国考古事业又有那样多令人身心悸动的发现;中国社会又有了那样多天翻地覆的巨变。1935 年至 1938 年,日本考古学家对赤峰红山后的考古发掘与出版工作,正处于中国抗日战争那样一个特别的时代背景之下。之所以令我心情复杂,是因为穿越 80 年的时空,我们看到:《赤峰红山后》在讨论中国北方史前文化时,仍然是不可回避的话题,特别是在红山文化讨论的领域中,这部书仍然是最具基础的文献。令人感慨的不仅仅是 80 年前的装帧与印刷质量;在这些质量背后,让我看到的是 80 年前日本学者仔细的工作态度、快捷的工作效率,还可以看到他们科学的思考方式、严谨的工作方法。3 个星期的田野工作,3 年的整理、讨论、出版时间,让我看到的是:一批作风严谨、工作用心、协同紧密的近代日本考古学者身影,以及由他们留下来的思考题。抛开日本国家的政治野心与军事侵略的背景来思考,就考古科学而言,在这样一部考古报告面前,不能不令我心生敬意。因此,与其说《赤峰红山后》让我产生遗憾,不如说更多的是庆幸。庆幸的是 80 年后我还能通过这部发掘报告管窥到红山上之一斑。知耻而后勇,可谓真的知耻。由此我充分理解了当代著名红山文化学者郭大顺先生,在他主持撰写《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时,曾经三番五次提升出版方案、完善讨论细节,接二连三推翻出版计划,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超越。可见,还是应了那句老话,科学探究虽然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国家。放下这些纠结的话题,我们回归到 20 世纪的前 50 年。那是一个中国的文化地理大发现的年代。随着 1898 年甲骨文的发现,从 1928 年开始,到 1937 年,由中央讨论院李济等先生主持了殷墟的 15 次正式发掘;1900 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成为石破天惊的事件;继而安特生于 1921 年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遗址;山东的龙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都有了重要发现。1930 年梁思永先生到赤峰考察,曾经预言赤峰的文化十分重要。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