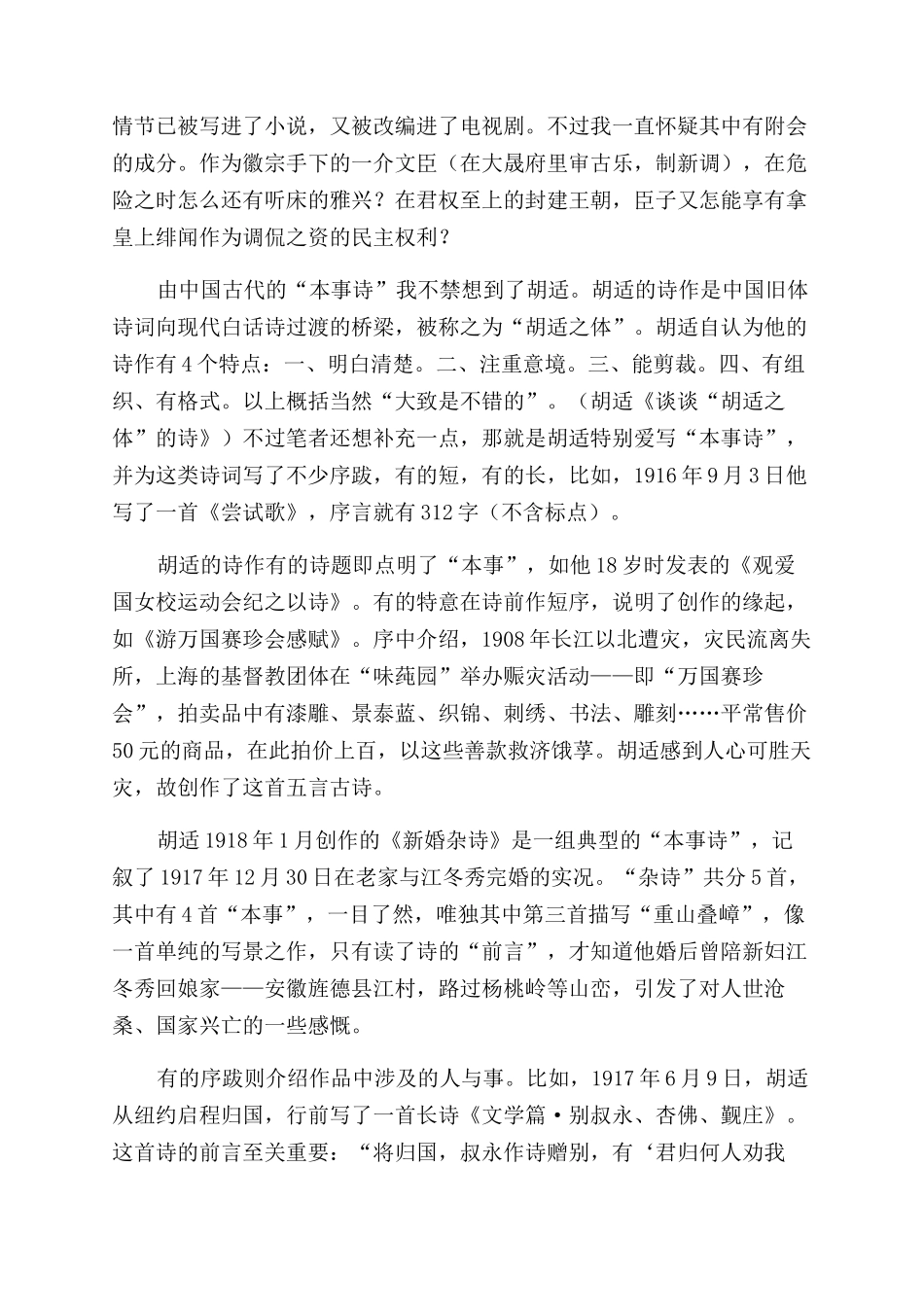胡适特别爱写“本事诗古代爱情诗中的怨妇诗和悼亡诗更多“本事”。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具体描写的是她对汉成帝的幽怨,但表达的却是封建社会中所有弃妇的心声——这些弃妇确如“合欢扇”,夏日能驱除炎热,而一到秋季就被主人“弃捐箧笥中”了。也有弃妇本人写诗的。魏文帝曹丕的弃妇甄后就写了一首《塘上行》,用一连串生动的比方抒写了遭谗见弃后的悲苦,可以说是弃妇诗中的写实之作。悼亡诗的代表作家有西晋时代的潘岳。他的《悼亡诗》三首广为流传。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唐代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因为我母亲所遇非人,故从小就教我读这组诗。这组诗写于元稹夫人韦氏逝世的当年,描写了爱妻生前的贤能艰辛,以及死后诗人的追悔和忆念。其中“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之句,更是脍炙人口,催人泪下。我至今仍清楚记得母亲教我读这首诗时那种凄茫无助的眼神。悼亡诗词的巅峰之作应该是宋代大词人苏轼的《江城子》。这首词填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 年),其时他的夫人王氏已经去世 10 年。王氏聪颖贤德,见识过人,16 岁即嫁给苏轼,不幸 27 岁英年早逝。假如不了解他们 10 年携手、相濡以沫的情感经历,对“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考,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样无限怅惘、无限感伤的句子就会体会不深。宋词中有两阕更具浪漫色彩:一阕是《鹊桥仙》,另一阕是《少年游》。词人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隐含的是关于牛郎织女的漂亮传说。自古以来,吟咏七夕的诗词数不胜数,为什么独有这首《鹊桥仙》胜出一筹呢?因为词人并没有停留在渲染“纤云”、“银河”、“飞星”、“鹊桥”的神话色彩,而是通过这个爱情悲剧悟出了一个励志的人生真谛:“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周邦彦的《少年游》一词背后,也隐含了一段风流韵事:名妓李师师与周邦彦幽会时,不巧宋徽宗私访,周邦彦狼狈中只好躲在床下,听到师师与徽宗一段私语:“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这个情节已被写进了小说,又被改编进了电视剧。不过我一直怀疑其中有附会的成分。作为徽宗手下的一介文臣(在大晟府里审古乐,制新调),在危险之时怎么还有听床的雅兴?在君权至上的封建王朝,臣子又怎能享有拿皇上绯闻作为调侃之资的民主权利?由中国古代的“本事诗”我不禁想到了胡适。胡适的诗作是中国旧体诗词向现代白话诗过渡的桥梁,被称之为“胡适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