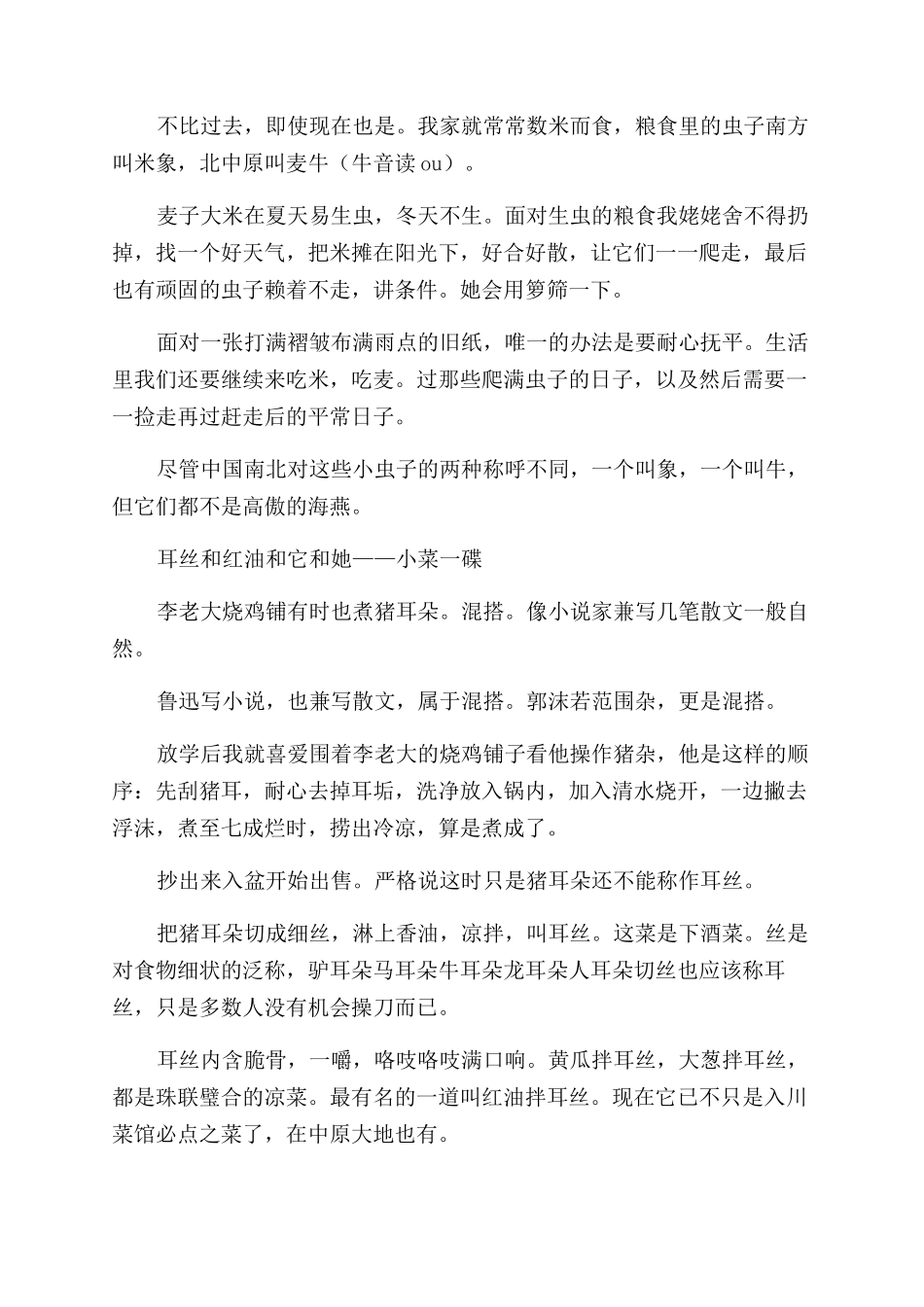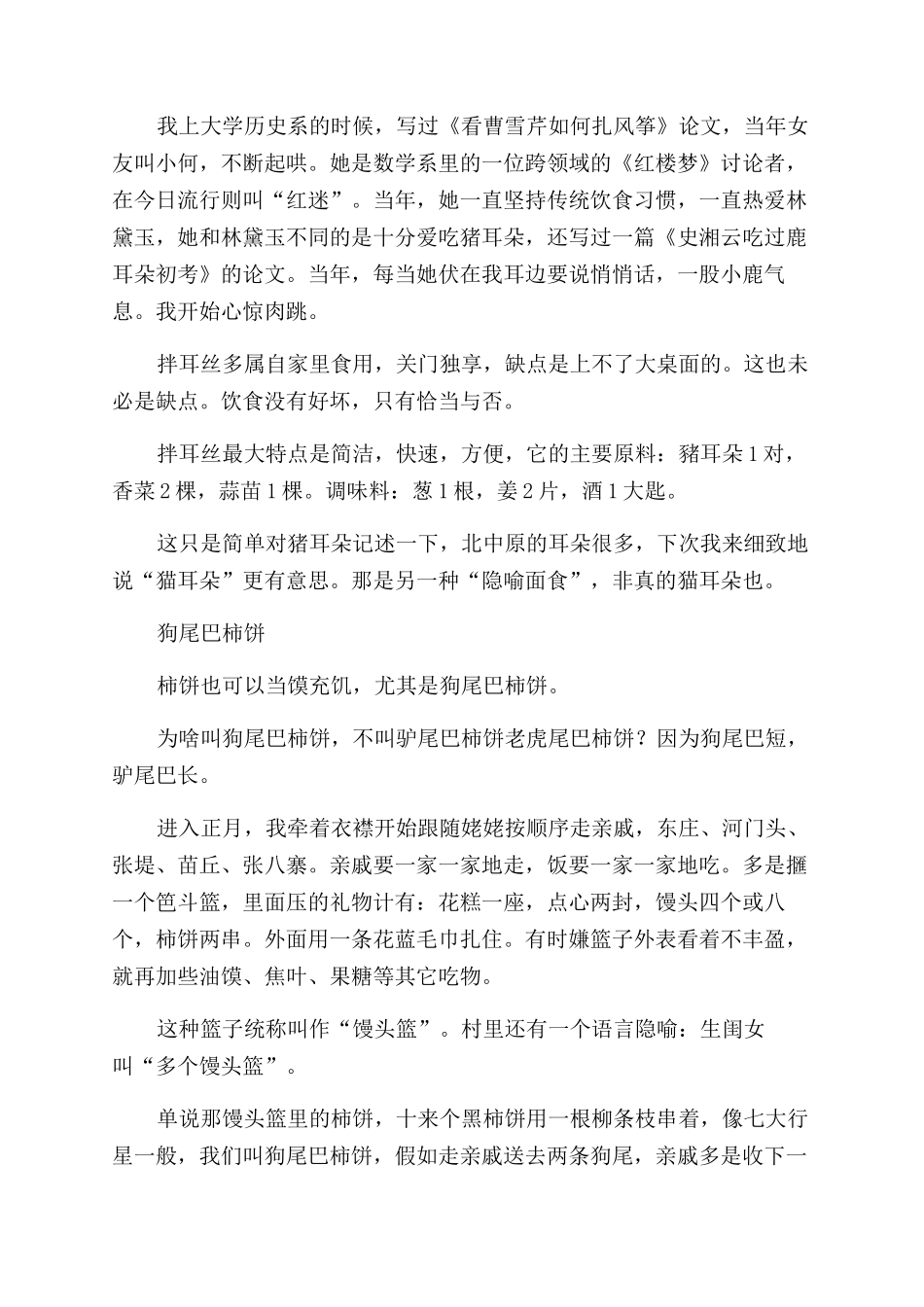草堂吃语查茶和数米——习惯记我的读书史上,费九牛二虎之力,在乡村我少年时能读到的作家如下:以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老作家们为多,1949 年以后的中国新作家次之,外国洋作家数量最是有限,高尔基算是其中一个大作家,他还是革命洋作家。我 15 岁时会背诵《语文》里他的《海燕》。“那是高傲的海燕”。乡村简陋的教室,土墙剥落,背景里有苏联的暴风雨。背诵到这时必须要高举一下手,以便助势。印象里高尔基的胡子最整齐,有鲁迅一般的造型。革命作家不只单单会写“高傲的海燕”,少年时我看高尔基三部曲之一的《童年》,一本书翻完了,里面有一个细节牢牢记住,是说他祖父祖母如何的吝啬:平常他们喝茶的时候,是要数茶叶的,一一数着来喝,一五一十的来喝。现在细想一下,在不产茶叶的俄罗斯,他们喝的茶是从东方中国运来的。茶叶们一片片坐在马背上摇摇晃晃,缓缓而来。造成这样数茶方式一点也不为过。草木提神,外国人一直好奇。当我年纪增长后,我才知道数茶是一种简朴美德。高尔基完全是以孙子之心度爷爷之腹。我家从来不一一数茶来喝,但是我家一直数米来吃。我姥爷说,以往的文人,把过日子艰难就称为“数米而食”。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他家还储存有五斗米。不折?饿也得饿趴你!不比过去,即使现在也是。我家就常常数米而食,粮食里的虫子南方叫米象,北中原叫麦牛(牛音读 ou)。麦子大米在夏天易生虫,冬天不生。面对生虫的粮食我姥姥舍不得扔掉,找一个好天气,把米摊在阳光下,好合好散,让它们一一爬走,最后也有顽固的虫子赖着不走,讲条件。她会用箩筛一下。面对一张打满褶皱布满雨点的旧纸,唯一的办法是要耐心抚平。生活里我们还要继续来吃米,吃麦。过那些爬满虫子的日子,以及然后需要一一捡走再过赶走后的平常日子。尽管中国南北对这些小虫子的两种称呼不同,一个叫象,一个叫牛,但它们都不是高傲的海燕。耳丝和红油和它和她——小菜一碟李老大烧鸡铺有时也煮猪耳朵。混搭。像小说家兼写几笔散文一般自然。鲁迅写小说,也兼写散文,属于混搭。郭沫若范围杂,更是混搭。放学后我就喜爱围着李老大的烧鸡铺子看他操作猪杂,他是这样的顺序:先刮猪耳,耐心去掉耳垢,洗净放入锅内,加入清水烧开,一边撇去浮沫,煮至七成烂时,捞出冷凉,算是煮成了。抄出来入盆开始出售。严格说这时只是猪耳朵还不能称作耳丝。把猪耳朵切成细丝,淋上香油,凉拌,叫耳丝。这菜是下酒菜。丝是对食物细状的泛称,驴耳朵马耳朵牛耳朵龙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