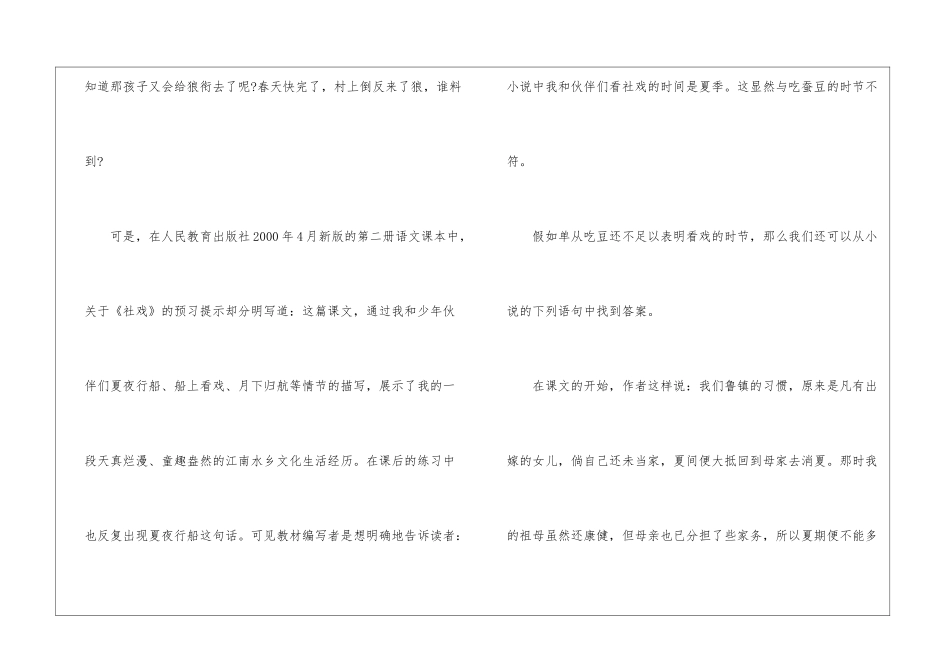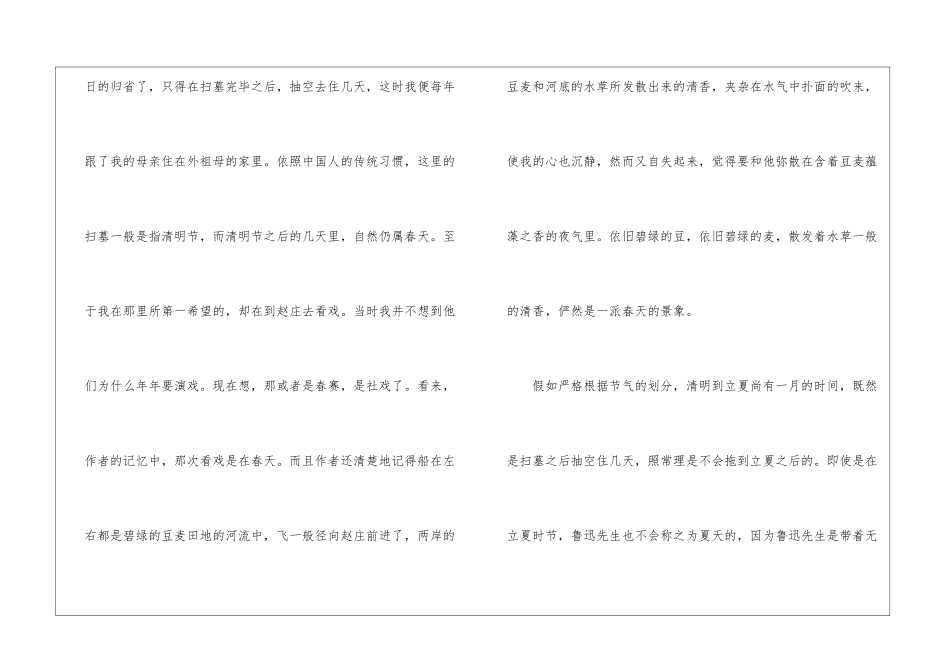关于看“社戏”的季节 对于生活在今日的孩 子来说,阅读鲁迅先生的《社戏》,他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月下归航中煮吃罗汉豆这一情节。北方的孩子,一提起用来煮着吃的豆,自然就联想起了半生不熟的黄豆──即俗称的毛豆。在自然状态下,吃毛豆的时节是在秋天,最早也不过是夏末秋初。在小说中,看戏的孩子们吃的罗汉豆不是北方的毛豆而是生长在南方的蚕豆。蚕豆收获的季节不在秋天而是在春末夏初。那么,有尚未熟透的、可以用来煮着吃的蚕豆的时节,自然不会是夏天。 在另一篇小说《祝福》里,祥林嫂家的阿毛被狼衔去时,孩子正在门口剥豆,而那时已是春天了: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要蒸豆卫老婆子也曾絮絮的对四婶说:谁知道那孩子又会给狼衔去了呢?春天快完了,村上倒反来了狼,谁料到? 可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4 月新版的第二册语文课本中,关于《社戏》的预习提示却分明写道:这篇课文,通过我和少年伙伴们夏夜行船、船上看戏、月下归航等情节的描写,展示了我的一段天真烂漫、童趣盎然的江南水乡文化生活经历。在课后的练习中也反复出现夏夜行船这句话。可见教材编写者是想明确地告诉读者:小说中我和伙伴们看社戏的时间是夏季。这显然与吃蚕豆的时节不符。 假如单从吃豆还不足以表明看戏的时节,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小说的下列语句中找到答案。 在课文的开始,作者这样说:我们鲁镇的习惯,原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依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这里的扫墓一般是指清明节,而清明节之后的几天里,自然仍属春天。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希望的,却在到赵庄去看戏。当时我并不想到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了。看来,作者的记忆中,那次看戏是在春天。而且作者还清楚地记得船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依旧碧绿的豆,依旧碧绿的麦,散发着水草一般的清香,俨然是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