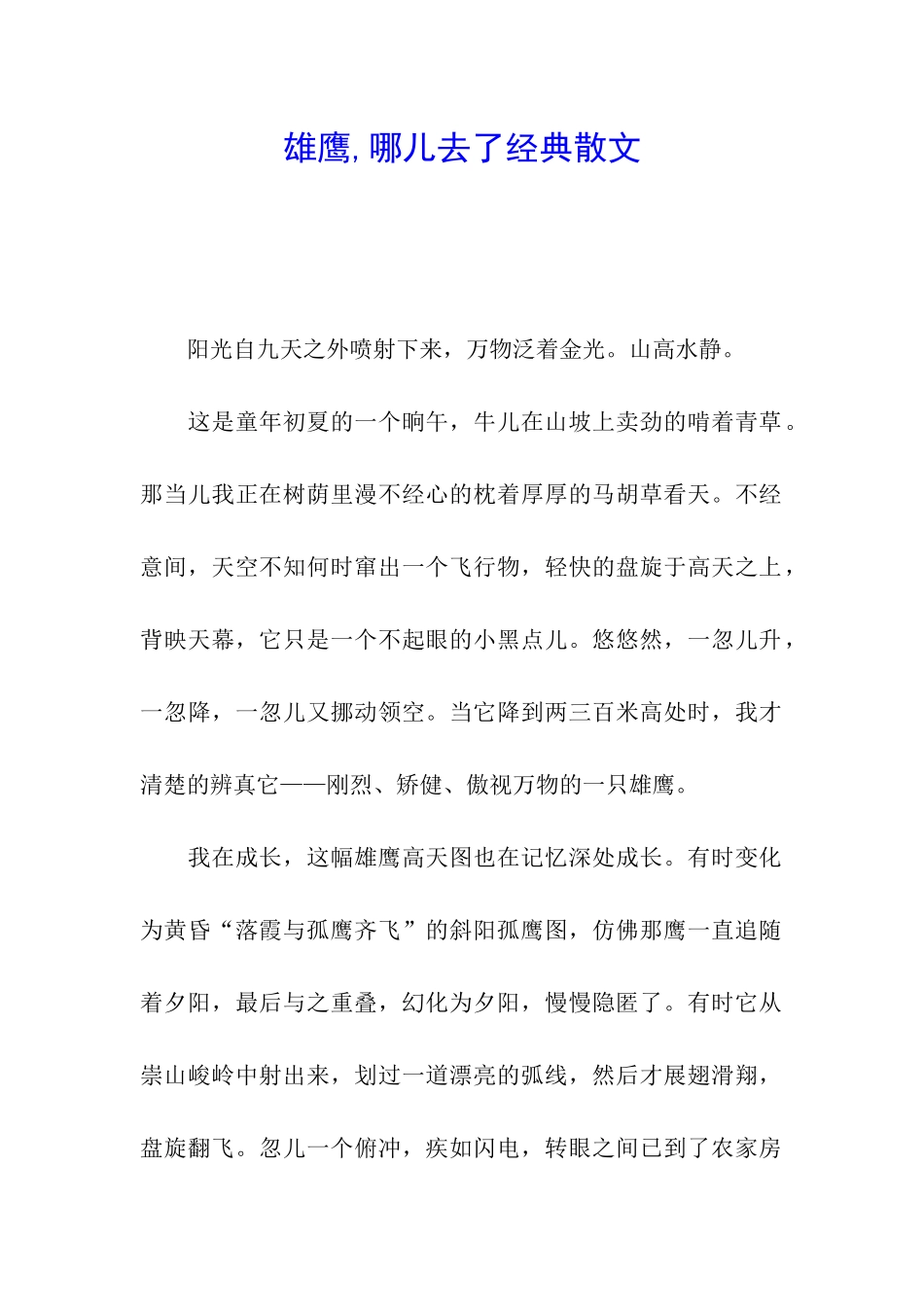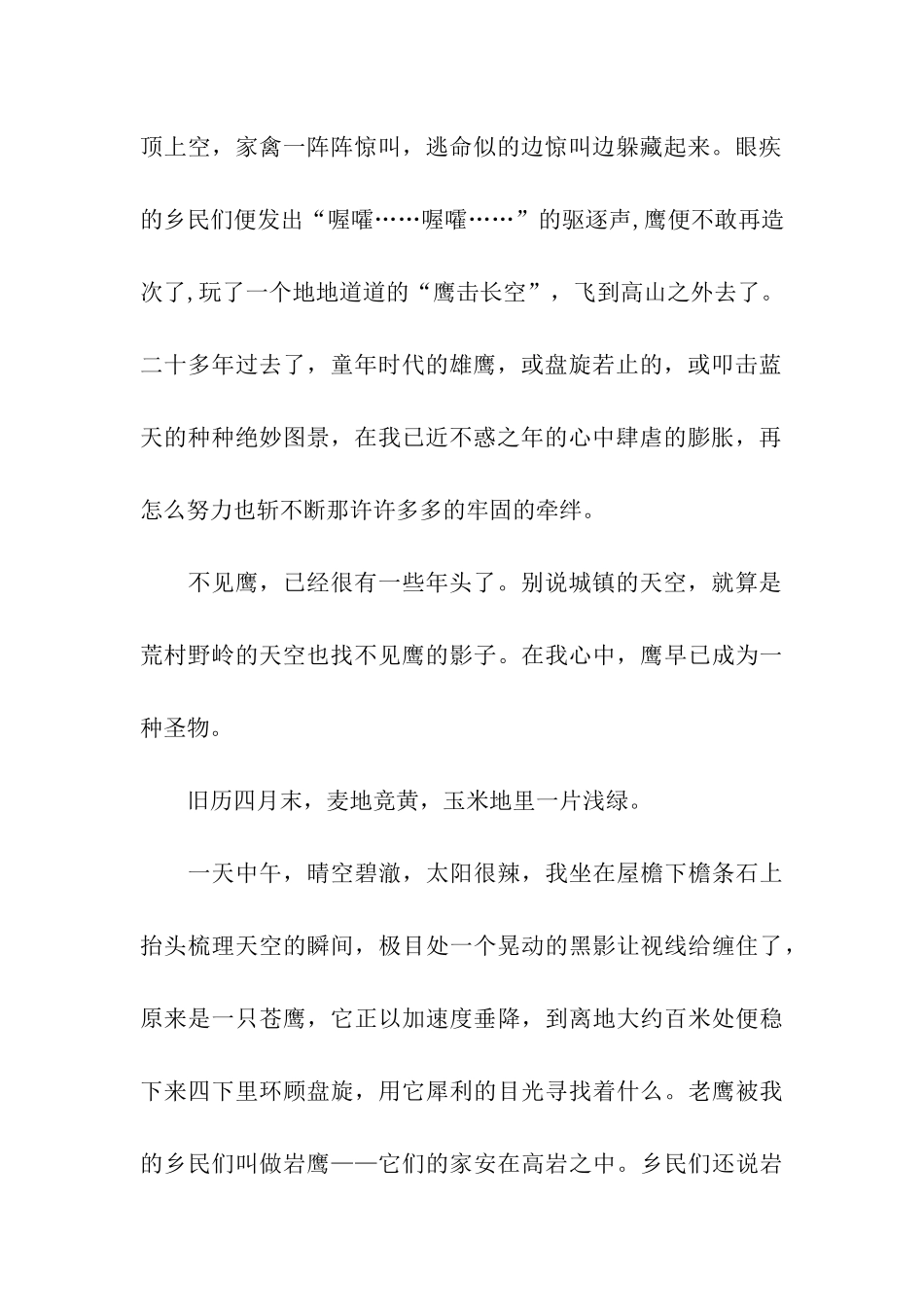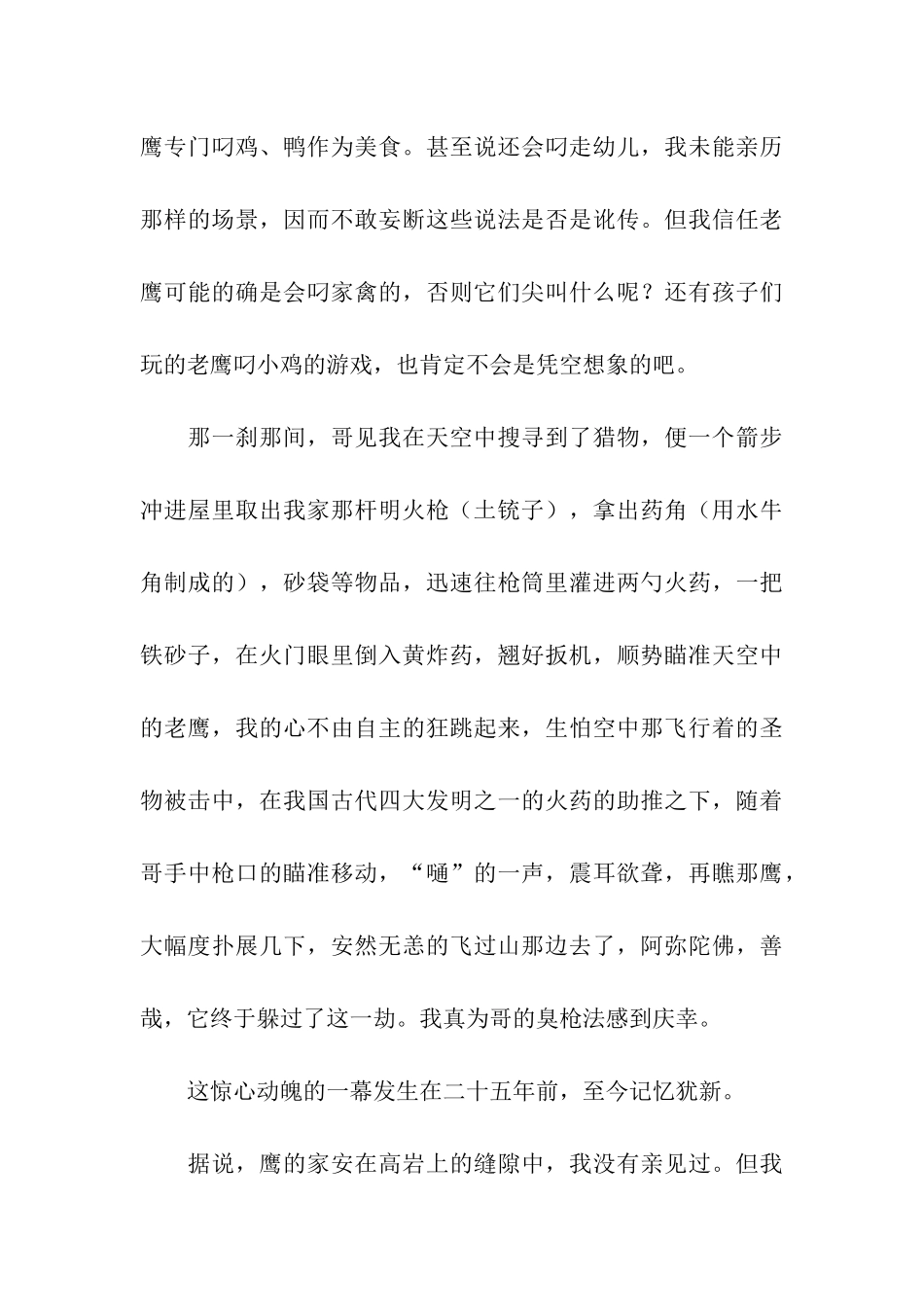雄鹰,哪儿去了经典散文 阳光自九天之外喷射下来,万物泛着金光。山高水静。 这是童年初夏的一个晌午,牛儿在山坡上卖劲的啃着青草。那当儿我正在树荫里漫不经心的枕着厚厚的马胡草看天。不经意间,天空不知何时窜出一个飞行物,轻快的盘旋于高天之上,背映天幕,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黑点儿。悠悠然,一忽儿升,一忽降,一忽儿又挪动领空。当它降到两三百米高处时,我才清楚的辨真它——刚烈、矫健、傲视万物的一只雄鹰。 我在成长,这幅雄鹰高天图也在记忆深处成长。有时变化为黄昏“落霞与孤鹰齐飞”的斜阳孤鹰图,仿佛那鹰一直追随着夕阳,最后与之重叠,幻化为夕阳,慢慢隐匿了。有时它从崇山峻岭中射出来,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然后才展翅滑翔,盘旋翻飞。忽儿一个俯冲,疾如闪电,转眼之间已到了农家房顶上空,家禽一阵阵惊叫,逃命似的边惊叫边躲藏起来。眼疾的乡民们便发出“喔嚯……喔嚯……”的驱逐声,鹰便不敢再造次了,玩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鹰击长空”,飞到高山之外去了。二十多年过去了,童年时代的雄鹰,或盘旋若止的,或叩击蓝天的种种绝妙图景,在我已近不惑之年的心中肆虐的膨胀,再怎么努力也斩不断那许许多多的牢固的牵绊。 不见鹰,已经很有一些年头了。别说城镇的天空,就算是荒村野岭的天空也找不见鹰的影子。在我心中,鹰早已成为一种圣物。 旧历四月末,麦地竞黄,玉米地里一片浅绿。 一天中午,晴空碧澈,太阳很辣,我坐在屋檐下檐条石上抬头梳理天空的瞬间,极目处一个晃动的黑影让视线给缠住了,原来是一只苍鹰,它正以加速度垂降,到离地大约百米处便稳下来四下里环顾盘旋,用它犀利的目光寻找着什么。老鹰被我的乡民们叫做岩鹰——它们的家安在高岩之中。乡民们还说岩鹰专门叼鸡、鸭作为美食。甚至说还会叼走幼儿,我未能亲历那样的场景,因而不敢妄断这些说法是否是讹传。但我信任老鹰可能的确是会叼家禽的,否则它们尖叫什么呢?还有孩子们玩的老鹰叼小鸡的游戏,也肯定不会是凭空想象的吧。 那一刹那间,哥见我在天空中搜寻到了猎物,便一个箭步冲进屋里取出我家那杆明火枪(土铳子),拿出药角(用水牛角制成的),砂袋等物品,迅速往枪筒里灌进两勺火药,一把铁砂子,在火门眼里倒入黄炸药,翘好扳机,顺势瞄准天空中的老鹰,我的心不由自主的狂跳起来,生怕空中那飞行着的圣物被击中,在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的助推之下,随着哥手中枪口的瞄准移动,“嗵”的一声,震耳欲聋,再瞧那鹰,大幅度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