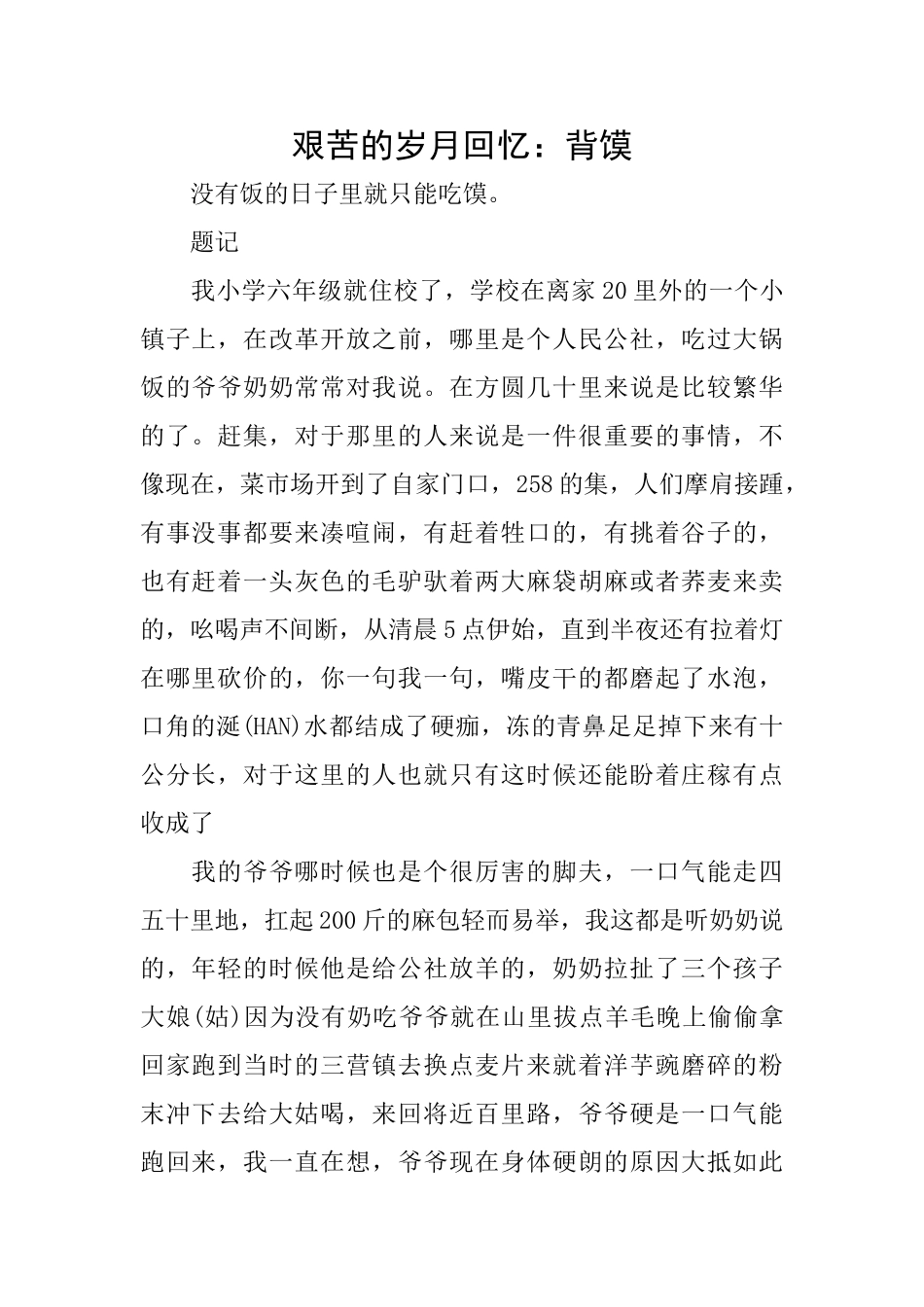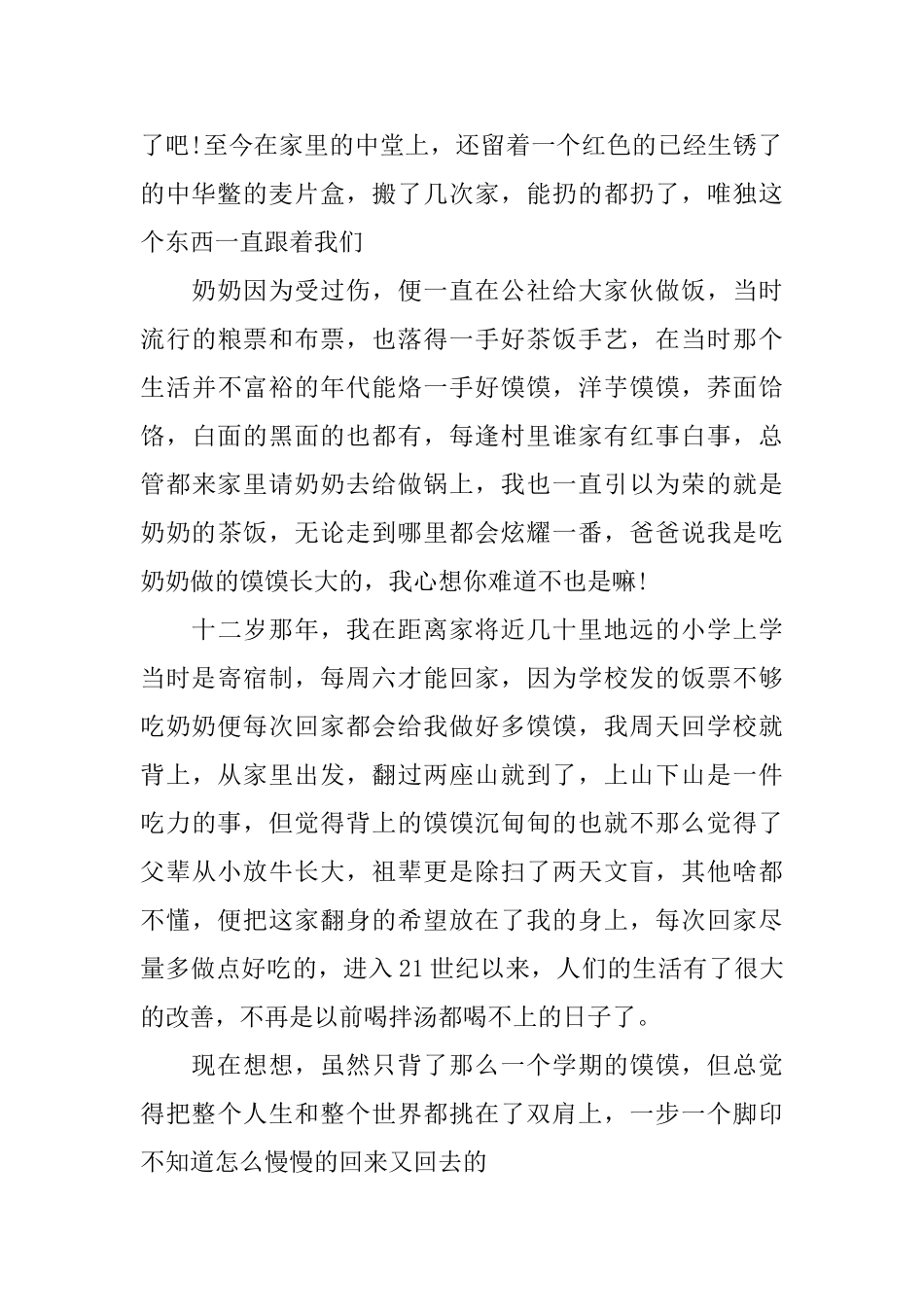艰苦的岁月回忆:背馍 没有饭的日子里就只能吃馍。 题记 我小学六年级就住校了,学校在离家 20 里外的一个小镇子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哪里是个人民公社,吃过大锅饭的爷爷奶奶常常对我说。在方圆几十里来说是比较繁华的了。赶集,对于那里的人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像现在,菜市场开到了自家门口,258 的集,人们摩肩接踵,有事没事都要来凑喧闹,有赶着牲口的,有挑着谷子的,也有赶着一头灰色的毛驴驮着两大麻袋胡麻或者荞麦来卖的,吆喝声不间断,从清晨 5 点伊始,直到半夜还有拉着灯在哪里砍价的,你一句我一句,嘴皮干的都磨起了水泡,口角的涎(HAN)水都结成了硬痂,冻的青鼻足足掉下来有十公分长,对于这里的人也就只有这时候还能盼着庄稼有点收成了 我的爷爷哪时候也是个很厉害的脚夫,一口气能走四五十里地,扛起 200 斤的麻包轻而易举,我这都是听奶奶说的,年轻的时候他是给公社放羊的,奶奶拉扯了三个孩子大娘(姑)因为没有奶吃爷爷就在山里拔点羊毛晚上偷偷拿回家跑到当时的三营镇去换点麦片来就着洋芋豌磨碎的粉末冲下去给大姑喝,来回将近百里路,爷爷硬是一口气能跑回来,我一直在想,爷爷现在身体硬朗的原因大抵如此了吧!至今在家里的中堂上,还留着一个红色的已经生锈了的中华鳖的麦片盒,搬了几次家,能扔的都扔了,唯独这个东西一直跟着我们 奶奶因为受过伤,便一直在公社给大家伙做饭,当时流行的粮票和布票,也落得一手好茶饭手艺,在当时那个生活并不富裕的年代能烙一手好馍馍,洋芋馍馍,荞面饸饹,白面的黑面的也都有,每逢村里谁家有红事白事,总管都来家里请奶奶去给做锅上,我也一直引以为荣的就是奶奶的茶饭,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炫耀一番,爸爸说我是吃奶奶做的馍馍长大的,我心想你难道不也是嘛! 十二岁那年,我在距离家将近几十里地远的小学上学当时是寄宿制,每周六才能回家,因为学校发的饭票不够吃奶奶便每次回家都会给我做好多馍馍,我周天回学校就背上,从家里出发,翻过两座山就到了,上山下山是一件吃力的事,但觉得背上的馍馍沉甸甸的也就不那么觉得了父辈从小放牛长大,祖辈更是除扫了两天文盲,其他啥都不懂,便把这家翻身的希望放在了我的身上,每次回家尽量多做点好吃的,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不再是以前喝拌汤都喝不上的日子了。 现在想想,虽然只背了那么一个学期的馍馍,但总觉得把整个人生和整个世界都挑在了双肩上,一步一个脚印不知道怎么慢慢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