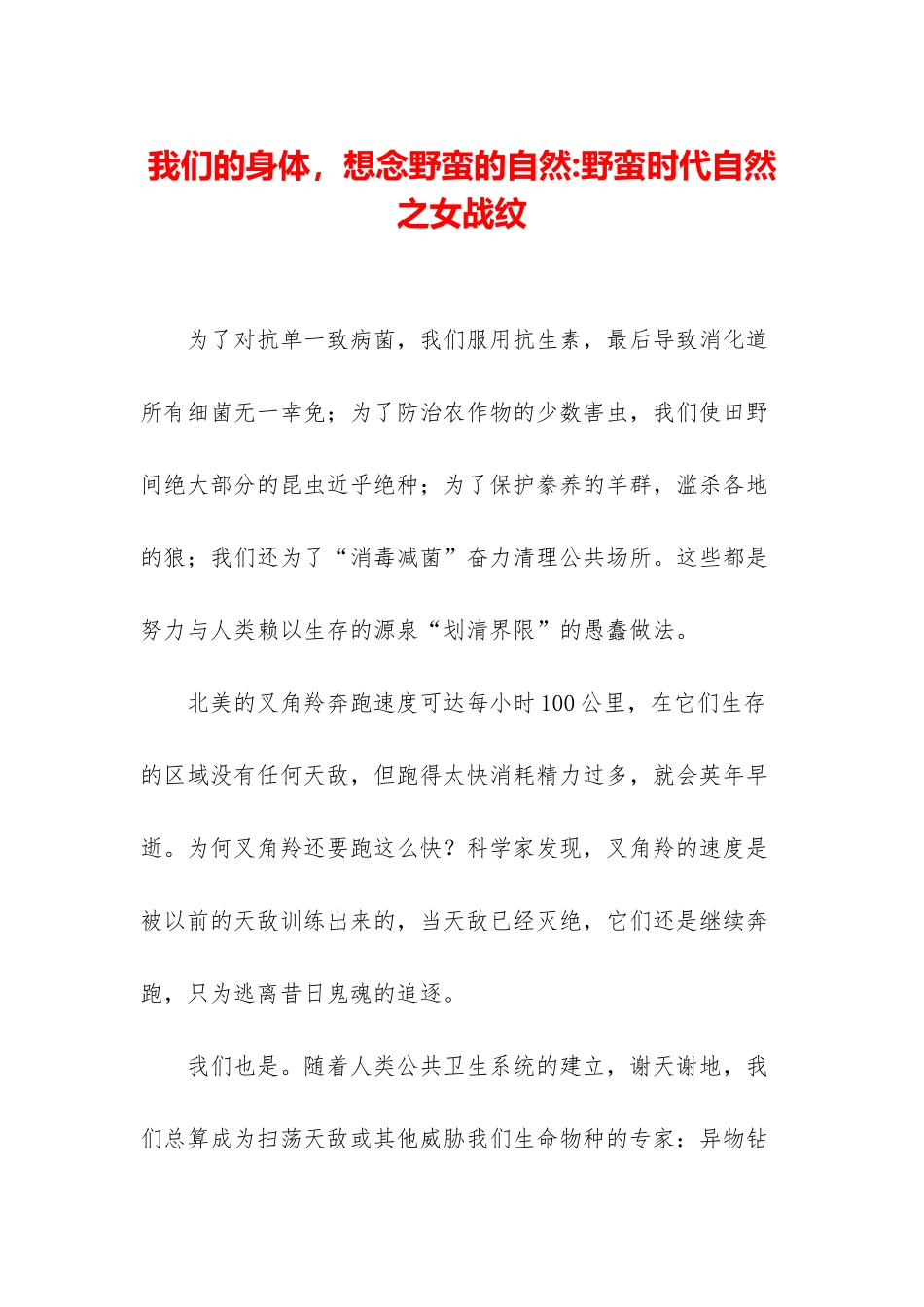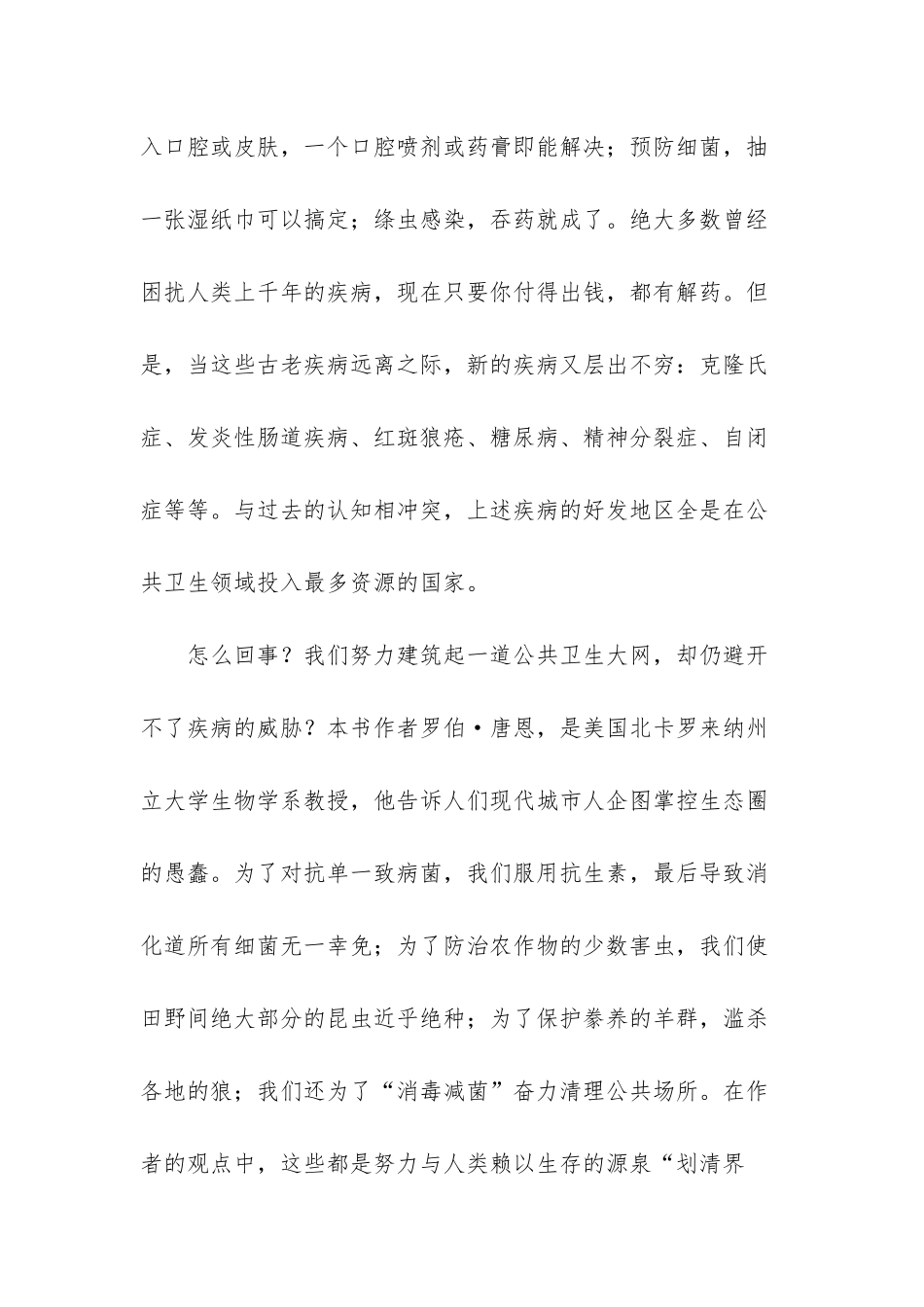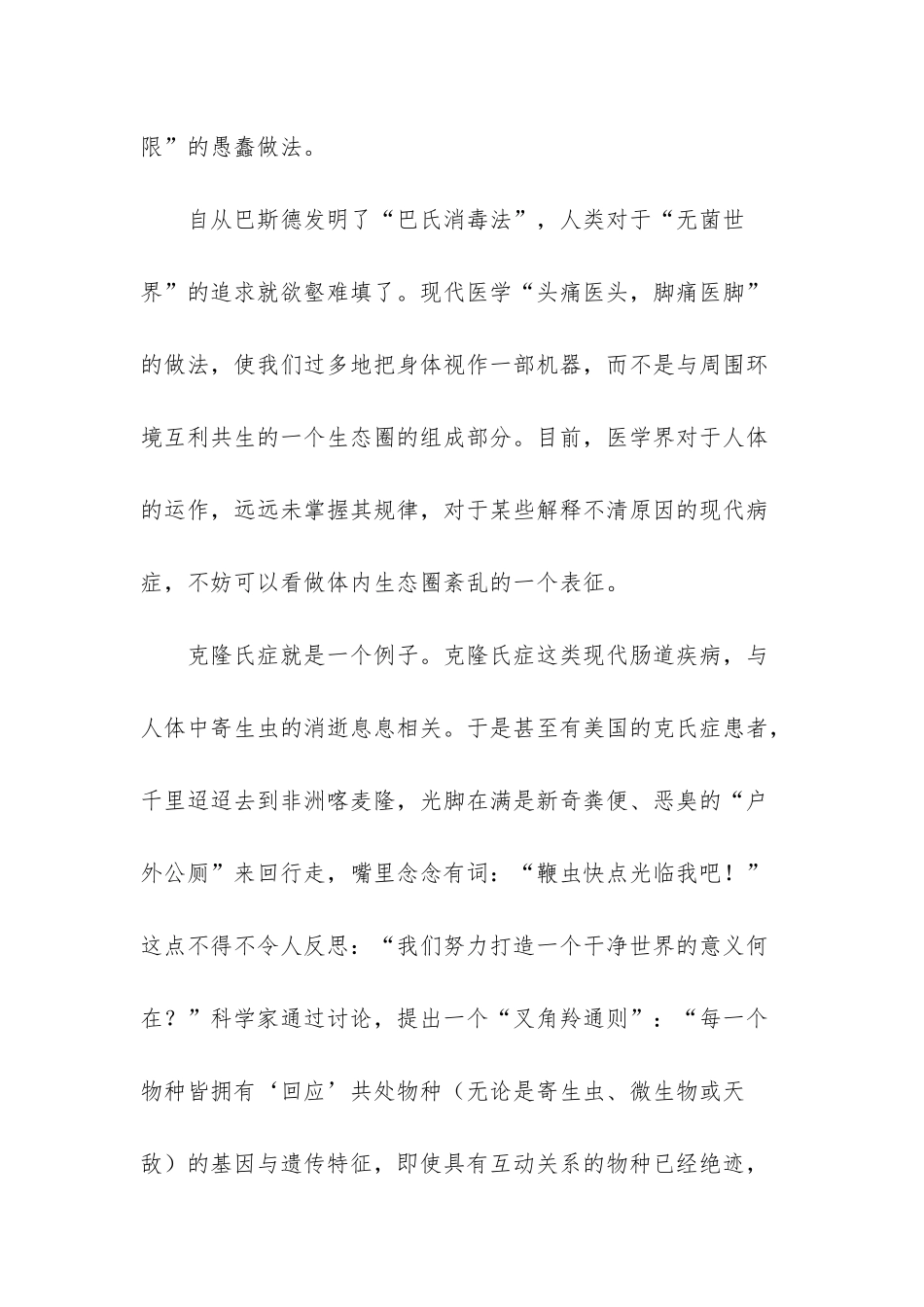我们的身体,想念野蛮的自然:野蛮时代自然之女战纹 为了对抗单一致病菌,我们服用抗生素,最后导致消化道所有细菌无一幸免;为了防治农作物的少数害虫,我们使田野间绝大部分的昆虫近乎绝种;为了保护豢养的羊群,滥杀各地的狼;我们还为了“消毒减菌”奋力清理公共场所。这些都是努力与人类赖以生存的源泉“划清界限”的愚蠢做法。 北美的叉角羚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 100 公里,在它们生存的区域没有任何天敌,但跑得太快消耗精力过多,就会英年早逝。为何叉角羚还要跑这么快?科学家发现,叉角羚的速度是被以前的天敌训练出来的,当天敌已经灭绝,它们还是继续奔跑,只为逃离昔日鬼魂的追逐。 我们也是。随着人类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谢天谢地,我们总算成为扫荡天敌或其他威胁我们生命物种的专家:异物钻入口腔或皮肤,一个口腔喷剂或药膏即能解决;预防细菌,抽一张湿纸巾可以搞定;绦虫感染,吞药就成了。绝大多数曾经困扰人类上千年的疾病,现在只要你付得出钱,都有解药。但是,当这些古老疾病远离之际,新的疾病又层出不穷:克隆氏症、发炎性肠道疾病、红斑狼疮、糖尿病、精神分裂症、自闭症等等。与过去的认知相冲突,上述疾病的好发地区全是在公共卫生领域投入最多资源的国家。 怎么回事?我们努力建筑起一道公共卫生大网,却仍避开不了疾病的威胁?本书作者罗伯·唐恩,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生物学系教授,他告诉人们现代城市人企图掌控生态圈的愚蠢。为了对抗单一致病菌,我们服用抗生素,最后导致消化道所有细菌无一幸免;为了防治农作物的少数害虫,我们使田野间绝大部分的昆虫近乎绝种;为了保护豢养的羊群,滥杀各地的狼;我们还为了“消毒减菌”奋力清理公共场所。在作者的观点中,这些都是努力与人类赖以生存的源泉“划清界限”的愚蠢做法。 自从巴斯德发明了“巴氏消毒法”,人类对于“无菌世界”的追求就欲壑难填了。现代医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使我们过多地把身体视作一部机器,而不是与周围环境互利共生的一个生态圈的组成部分。目前,医学界对于人体的运作,远远未掌握其规律,对于某些解释不清原因的现代病症,不妨可以看做体内生态圈紊乱的一个表征。 克隆氏症就是一个例子。克隆氏症这类现代肠道疾病,与人体中寄生虫的消逝息息相关。于是甚至有美国的克氏症患者,千里迢迢去到非洲喀麦隆,光脚在满是新奇粪便、恶臭的“户外公厕”来回行走,嘴里念念有词:“鞭虫快点光临我吧!”这点不得不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