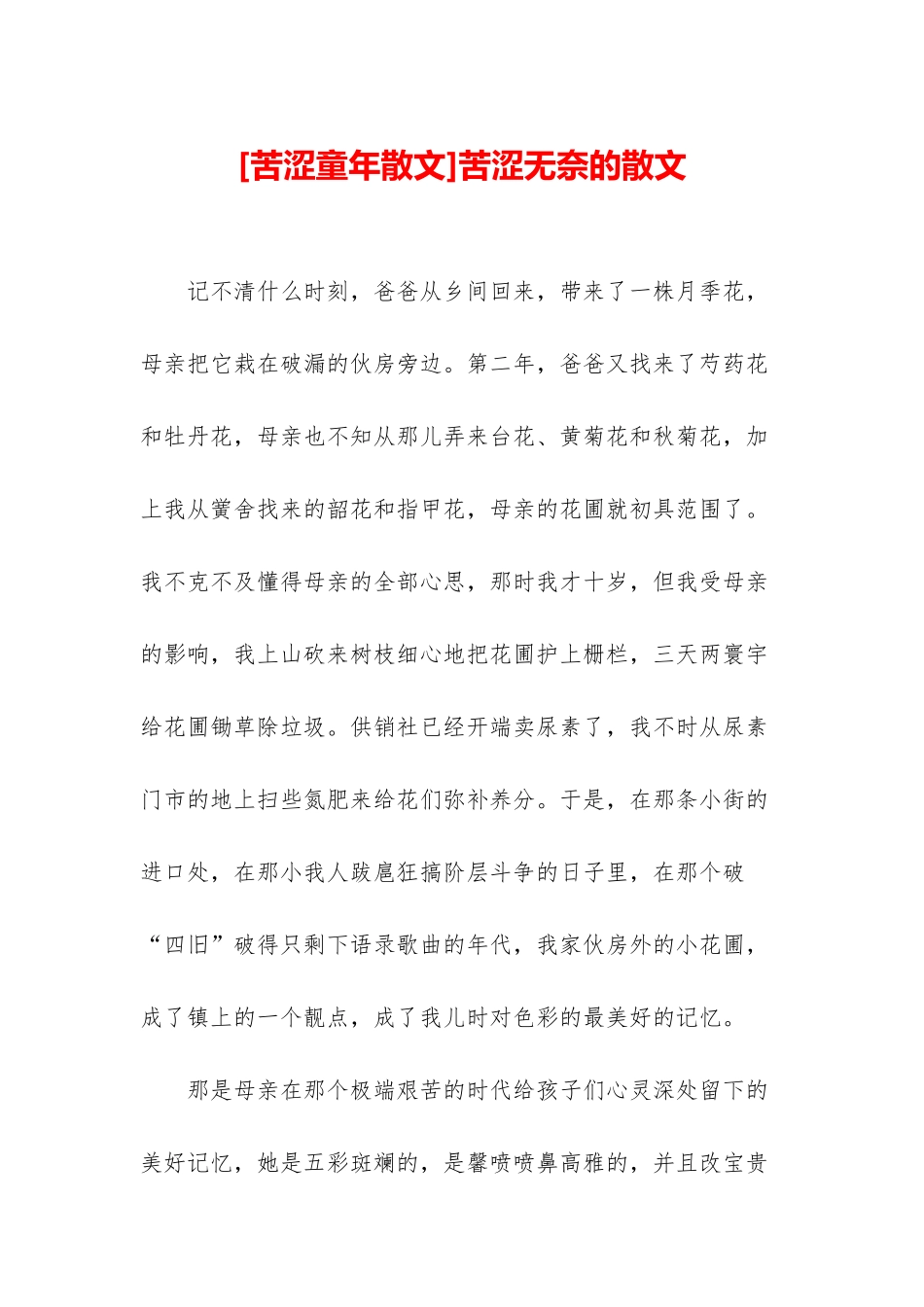[苦涩童年散文]苦涩无奈的散文 记不清什么时刻,爸爸从乡间回来,带来了一株月季花,母亲把它栽在破漏的伙房旁边。第二年,爸爸又找来了芍药花和牡丹花,母亲也不知从那儿弄来台花、黄菊花和秋菊花,加上我从黉舍找来的韶花和指甲花,母亲的花圃就初具范围了。我不克不及懂得母亲的全部心思,那时我才十岁,但我受母亲的影响,我上山砍来树枝细心地把花圃护上栅栏,三天两寰宇给花圃锄草除垃圾。供销社已经开端卖尿素了,我不时从尿素门市的地上扫些氮肥来给花们弥补养分。于是,在那条小街的进口处,在那小我人跋扈狂搞阶层斗争的日子里,在那个破“四旧”破得只剩下语录歌曲的年代,我家伙房外的小花圃,成了镇上的一个靓点,成了我儿时对色彩的最美好的记忆。 那是母亲在那个极端艰苦的时代给孩子们心灵深处留下的美好记忆,她是五彩斑斓的,是馨喷喷鼻高雅的,并且改宝贵的,她是由母亲和我们用劳动本身制造的。 最忘不了的是那株月季,一年四时,盛开不败。凌晨起来,老远就闻获得她的幽喷喷鼻。曾听得有人对母亲开打趣说,你家花开得那么艳,怪不得有那么多美丽女儿(我有五个妹妹)。而在逢集那天,常常有农村妇女来那株月季花下,偷摘花蕾,据说,月季花蕾可以治不孕不育症。 那个时刻,宝贵县城的来镇上照一次像,那年夏天,我们一家在花圃前照的合影就成了今日的传家宝了。 后来,与我家近邻的扬家,还有和母亲一路工作的田家和刘家都来我家移花,于是,供销社家眷宿舍房前就出现了一长排花圃。每到春夏二季,那种烂漫和艳丽,在那个没有音乐没有美术的文化大年夜大年夜禁锢时代,真可以说就是我和我的妹妹们还有邻居们独一的除吃饭穿衣之外的精力享受了。 文革停止后,母亲分开了那个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镇,我们七兄妹也各奔器械外出谋生。当有一天我从工作的城市还乡间看望母亲,一进大年夜大年夜院子,老远就看见院坝右边花圃里各类盛开的鲜花,我径直大年夜大年夜步走以前,叫一声“妈妈,我回来啦!”因为我知道,有鲜花的处所,就是我母亲地点的处所。 文革时代,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天天遭批斗,一家人沉醉在一种极端压抑的氛围之中,那时我们已经是九口之家了,可母亲一如她解放初期任秧歌队长时一样,从来走路都是一边走一边唱,远远地,听到歌声就知道母亲来了。那个时刻,不论心里有多苦,在我们面前,母亲都是乐不雅不雅而自负的。 母亲分开我们之前的几年,她的花圃里品种加倍多样,有些我都叫不出名字来,有海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