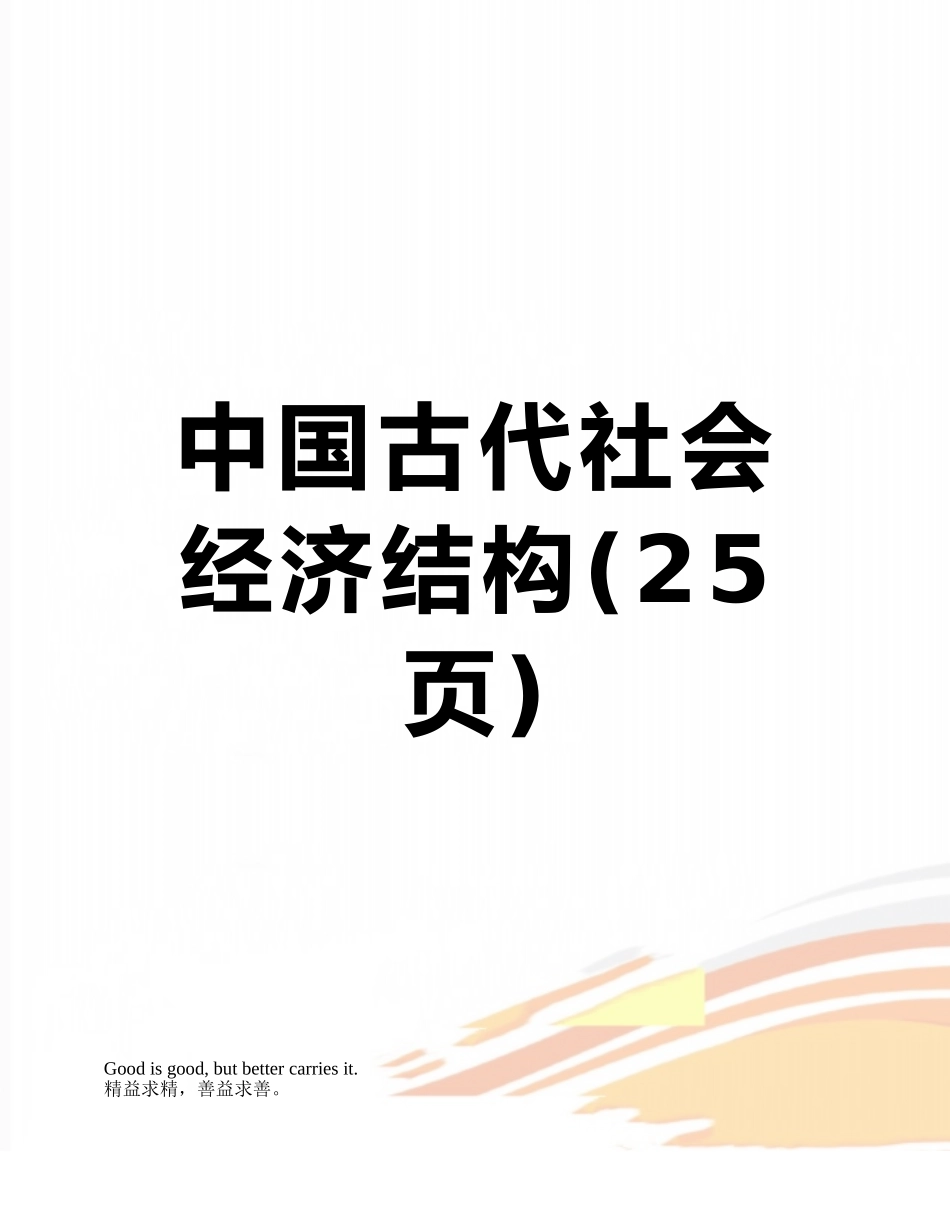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25页)Good is good, but better carries it.精益求精,善益求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 尹明耀 1 关于奴隶制与封建制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既然民族是一个文化概念;民族是文化的共同体。那末,随着文化本体的转换,民族本身则必定发生相应地分化或融合。古代的高卢人融入法兰克人之中,虽然起因于高卢人之被征服,但假如没有文化的融合,高卢人便不可能消逝在法兰克人之中;而近代法兰西民族的诞生,则完全是近代文化熔铸的结果。至于意大利民族、德意志民族、英吉利民族,莫不如此。中国由华夏民族而汉民族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根本就在于血缘文化延续了数千年,甚至直到今日,血缘本体仍在中国文化的构成要素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正是这个缘故,在历次民族融合中,各兄弟民族都只是被血缘文化所同化,而并没有形成一种新的文化。 中国的血缘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之久,根本原因便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别性。正是这种特别的社会经济结构,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起着维持和加固的作用。因此,我们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固性、持久性,便必须首先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独特性。 讨论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不能不首先涉及到奴隶制与封建制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奴隶制与封建制是社会进展的两个相继出现的阶段;而领主制与地主制则又是封建社会的两个相继出现的阶段。这一观点虽然几十年来一直被当作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实际上却并不合乎马克思本人的论断①(何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社会进展的五个阶段公式》一文作了详细论证,可参阅。)。并且,众所周知,领主制之为领主制,就在于它是以等级授职、授土而形成的军事采邑制度。这一制度的基础,它的劳动组织形式,便是农奴制。虽然奴隶的出现很早,但作为一种制度,它却较农奴制要晚。因为农奴制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中国,都是早在奴隶制盛行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恩格斯就曾指出:“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 ①(《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四卷,P672。)。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史学界、乃至于整个学术界恰恰正是以那种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历史。由于它同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事实相去太远,以致于不得不在史料的解释上做文章。其结果,不但造成了在中国古代社会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