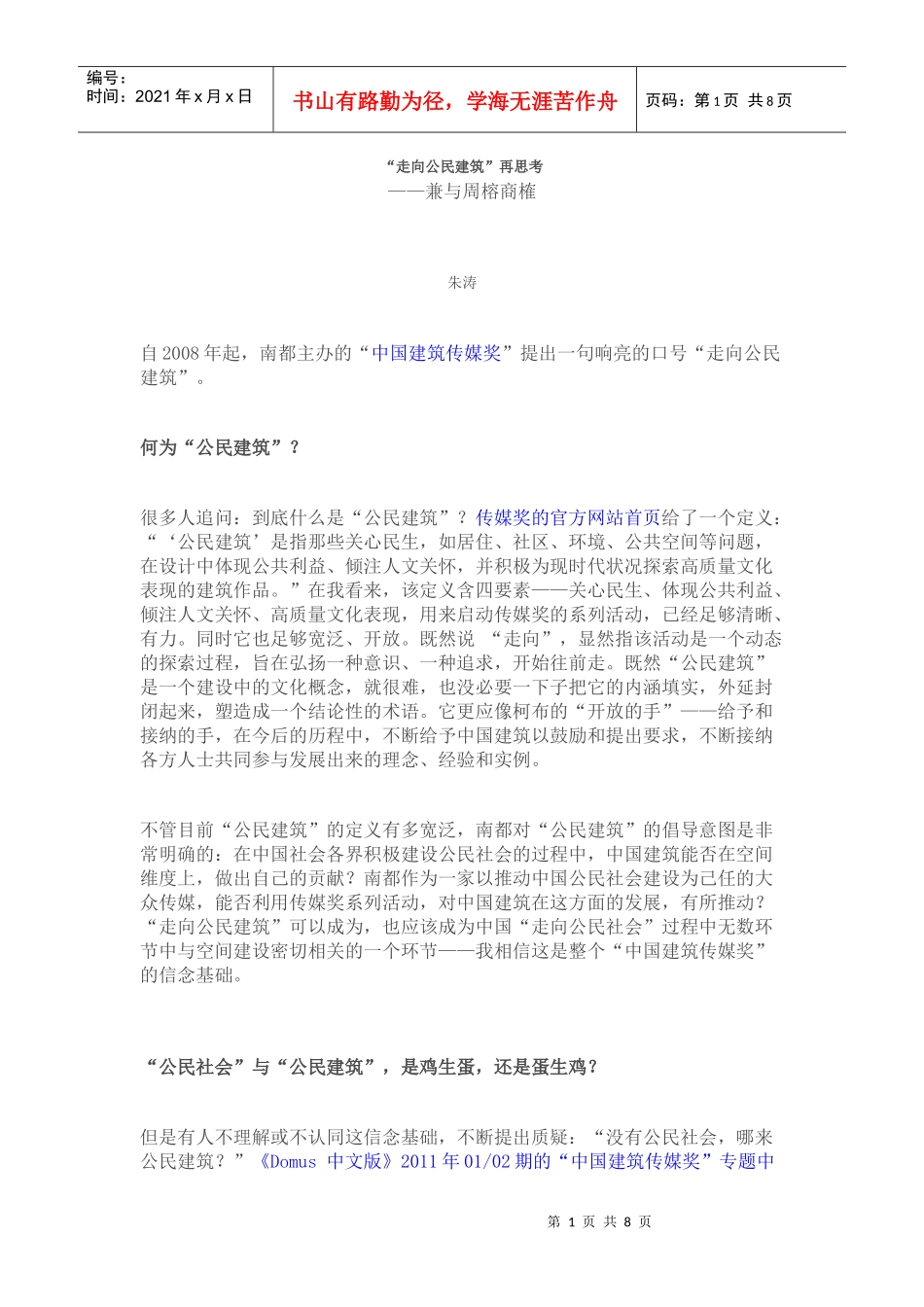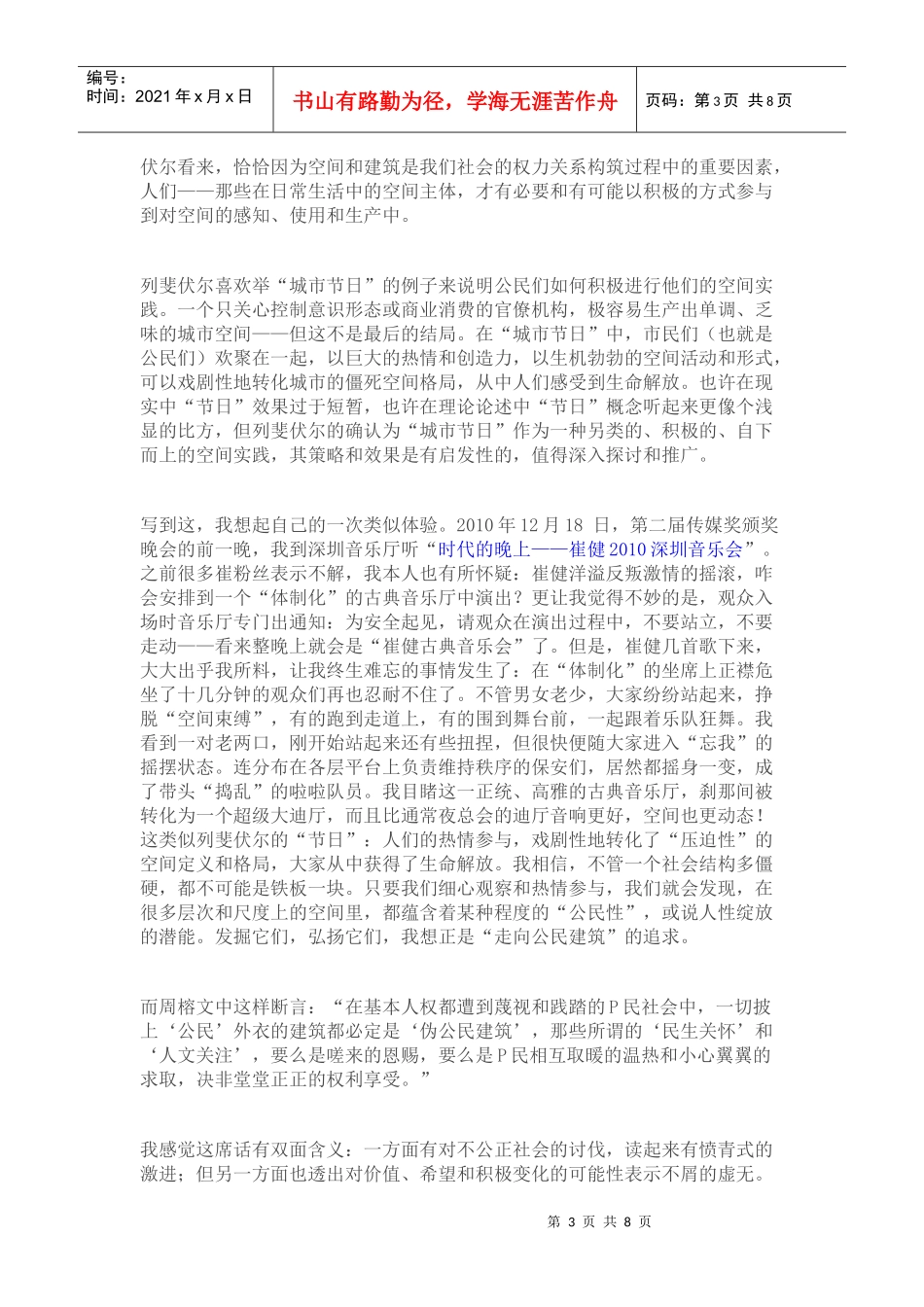第1页共8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页共8页“走向公民建筑”再思考——兼与周榕商榷朱涛自2008年起,南都主办的“中国建筑传媒奖”提出一句响亮的口号“走向公民建筑”。何为“公民建筑”?很多人追问:到底什么是“公民建筑”?传媒奖的官方网站首页给了一个定义:“‘公民建筑’是指那些关心民生,如居住、社区、环境、公共空间等问题,在设计中体现公共利益、倾注人文关怀,并积极为现时代状况探索高质量文化表现的建筑作品。”在我看来,该定义含四要素——关心民生、体现公共利益、倾注人文关怀、高质量文化表现,用来启动传媒奖的系列活动,已经足够清晰、有力。同时它也足够宽泛、开放。既然说“走向”,显然指该活动是一个动态的探索过程,旨在弘扬一种意识、一种追求,开始往前走。既然“公民建筑”是一个建设中的文化概念,就很难,也没必要一下子把它的内涵填实,外延封闭起来,塑造成一个结论性的术语。它更应像柯布的“开放的手”——给予和接纳的手,在今后的历程中,不断给予中国建筑以鼓励和提出要求,不断接纳各方人士共同参与发展出来的理念、经验和实例。不管目前“公民建筑”的定义有多宽泛,南都对“公民建筑”的倡导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在中国社会各界积极建设公民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建筑能否在空间维度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南都作为一家以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为己任的大众传媒,能否利用传媒奖系列活动,对中国建筑在这方面的发展,有所推动?“走向公民建筑”可以成为,也应该成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过程中无数环节中与空间建设密切相关的一个环节——我相信这是整个“中国建筑传媒奖”的信念基础。“公民社会”与“公民建筑”,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但是有人不理解或不认同这信念基础,不断提出质疑:“没有公民社会,哪来公民建筑?”《Domus中文版》2011年01/02期的“中国建筑传媒奖”专题中第2页共8页第1页共8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2页共8页周榕先生的批评就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在当下中国非公民社会的状况下评选“公民建筑”,实为“缘木求鱼”。周榕在文中援引了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作为其论证依据。周这样诠释该理论:“人类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生产的结果,空间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反映,空间结构必须与社会结构相匹配。”由此,他得出结论:“‘公民建筑’必然是‘公民社会’的产物而非导引。中国建筑传媒奖的尴尬在于:在没有‘公民社会’基因的大环境下试图评选出‘公民建筑’,其结果,除了让中国建筑‘被公民’之外别无它途。”周榕还进一步批评设置传媒奖的理想过于虚妄:“希冀借助‘公民建筑’这一团虚假的烛火,寻找到通向公民社会的秘径,中国知识精英‘很傻很天真’的本来面目于此可窥一斑。”首先感谢周榕提到列斐伏尔!让我本人一下子意识到列斐伏尔的理论对我们今天探讨公民建筑实在有重大意义。列斐伏尔的空间写作一贯坚持对单一空间-权力机构的批判,呼吁决策者和规划师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尊重,与艺术家、建筑师、规划师们保持密切交流,曾激发众多空间领域的知识分子和职业工作者参与1968年的社会运动,并深刻影响了八十年代法国、德国的城市规划政策。这样一位空间思想家,我会毫不犹豫地称他为一位“公民建筑理论家”!对这样一系列思想家学说的研讨,相信会为我们在中国逐渐充实“公民建筑”理念有很大帮助。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列斐伏尔对公民空间实践产生如此重大积极影响的理论,怎么会在周榕文中推导出一个如此消极,令人沮丧的“不作为”的结论!设想列斐伏尔本人仍在世,在深圳参加传媒奖活动后,会劝告大家识时务,放聪明点,回家洗洗睡了,等将来某天中国的公民社会“自己”实现了,会自然“生产”出个公民建筑吗?“空间生产”,是公民的,还是P民的?在我看来,周榕论证的一个主要症结在于他把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理解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于是城市空间是社会中主导经济力量的意识形态的反映。但就我的理解,列斐伏尔的理论贡献恰恰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