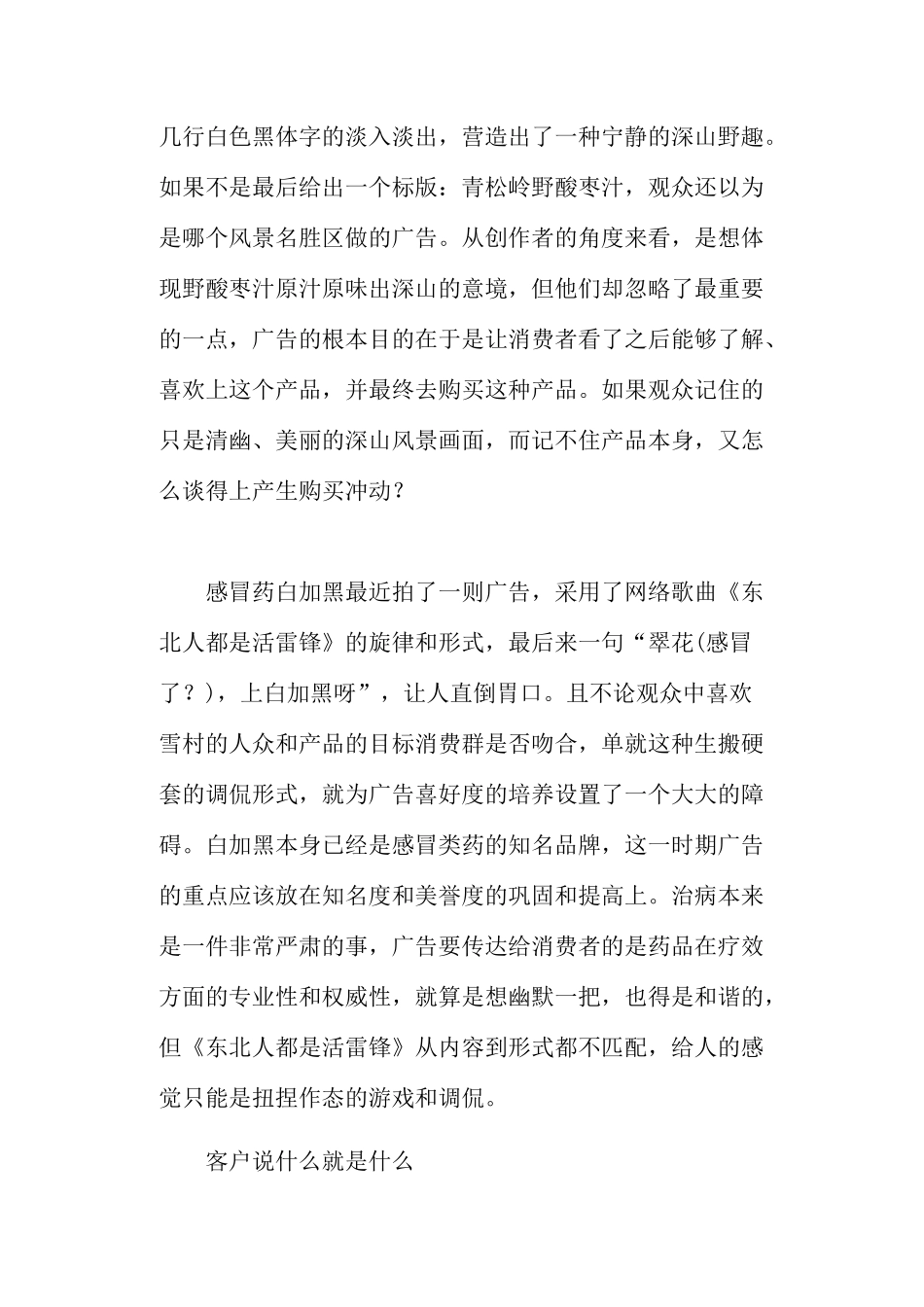中国广告病---被阉割的广告创意1996年中国首次组团参加第43届戛纳国际广告节,中国参赛作品无一入围,这在代表团中引起极大震动。大家不服气,去找广告节主席罗杰理论:“评委不懂中国文化如何评价中国作品?”罗杰反问:“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看得懂麦当劳的广告,特别是中国的孩子?”在罗杰看来,广告是一门跨国界的艺术,其创意没有潮流可言,只有好的创意和不好的创意的区别。创意简洁、贴近生活、表达人性、富于幽默、能能更好地与产品特点相结合就是好广告。如何做一则有创意的广告一直是中国广告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为了达到“意”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他们殚精竭虑,不但天马行空地放飞自己的思维,还常常和圈内人一起掀起“洗心革面”的头脑风暴。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这一切仍然无法突破中国广告的创意瓶颈。一味求新、求异、求美,为了创意而创意最近电视台播出一则“青松岭野酸枣汁”广告。广告展现的是一片幽静、安宁的山沟,充满天然纯净的意蕴,加上几行白色黑体字的淡入淡出,营造出了一种宁静的深山野趣。如果不是最后给出一个标版:青松岭野酸枣汁,观众还以为是哪个风景名胜区做的广告。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是想体现野酸枣汁原汁原味出深山的意境,但他们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广告的根本目的在于是让消费者看了之后能够了解、喜欢上这个产品,并最终去购买这种产品。如果观众记住的只是清幽、美丽的深山风景画面,而记不住产品本身,又怎么谈得上产生购买冲动?感冒药白加黑最近拍了一则广告,采用了网络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旋律和形式,最后来一句“翠花(感冒了?),上白加黑呀”,让人直倒胃口。且不论观众中喜欢雪村的人众和产品的目标消费群是否吻合,单就这种生搬硬套的调侃形式,就为广告喜好度的培养设置了一个大大的障碍。白加黑本身已经是感冒类药的知名品牌,这一时期广告的重点应该放在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巩固和提高上。治病本来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广告要传达给消费者的是药品在疗效方面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就算是想幽默一把,也得是和谐的,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匹配,给人的感觉只能是扭捏作态的游戏和调侃。客户说什么就是什么奥美广告公司老板奥格威曾经说过一句为天下广告人长气的话:“如果你(客户)只是要一条会摇尾巴而不会叫的狗,你就不要找广告公司。”话虽如此,但钱在客户的口袋里,不听他的,他能把钱给你吗?广告是一个服务行业,也是一个靠提供智力来生存和发展的行业,加上国内目前对广告效果的测评还没有一套客观有效的模式,客户的认同往往就成了广告好坏的判别标准。很多时候,广告公司为了拿到定单,不得不做出让步,唯客户的意志是从。这样一来,广告公司成了企业的下属机构,所有的专业智慧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在各种报刊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广告版面密密麻麻全是文字,毫无创意和美感可言。广告主天真地以为,文字越多,传达的信息量就越大,广告的作用发挥越充分。这种自以为是、想当然的心态让大量的广告淹没在其他的广告海洋中。一个不能为自己带来视觉冲击的广告,消费者有什么义务和兴趣去关心?一味迎合某些消费者无聊的低级“性趣”一段时间,无论是香皂、沐浴液,还是热水器广告,都可以看到一个极为相似的镜头:一位美女一边裸露着满是洗浴液(或香皂)泡沫的香肩和白生生的小腿(还好没露出大腿),一边对着镜头大做享受洗浴之乐的表情,最后来一个“某某浴液,美好生活的开始”。看得多了,观众不免心下生疑:全中国的男人们都不洗澡的吗?广告创意者的本意是想通过美人沐浴来吸引眼球,提高产品的关注率,偶一为之倒也无妨,多了就让人觉得反感。更何况,喜欢看女人洗澡的多为男士,而真正掏钱买香皂、沐浴液这些家庭用品的却大多数是家庭妇女,一旦她们发现自己的老公看广告里的美女比看自己还多时,你看她们会不会买你的产品。利用一些消费者的低级趣味大打性的擦边球是现在不少广告喜欢采用的模式。有一个文具生产厂家为自己的系列产品做广告,其中,墨水的广告词是“换个姿势再来”,铅笔的广告词是“虽然我很短,但是我很硬”,塑料文件夹的广告语是“我不是那种一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