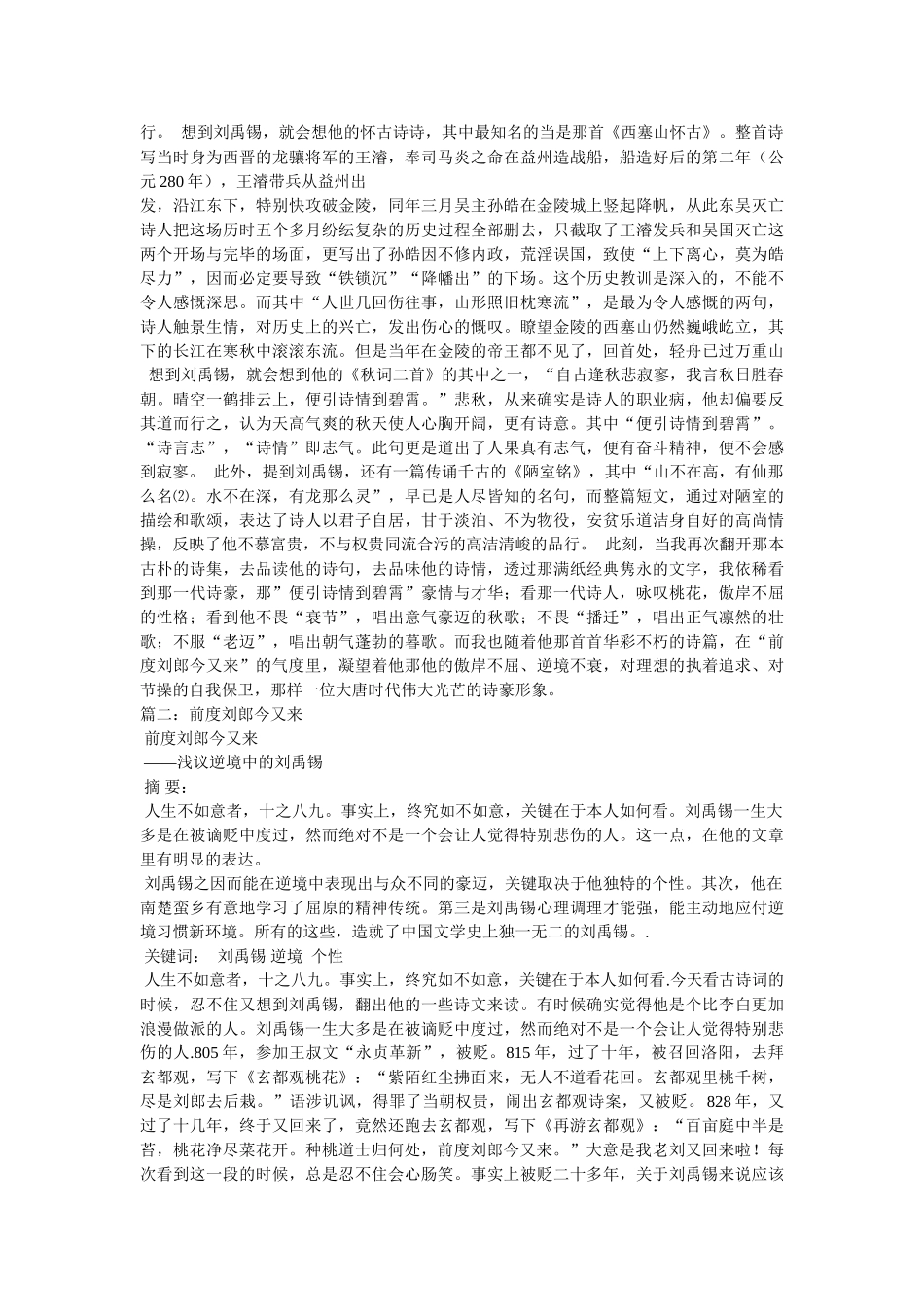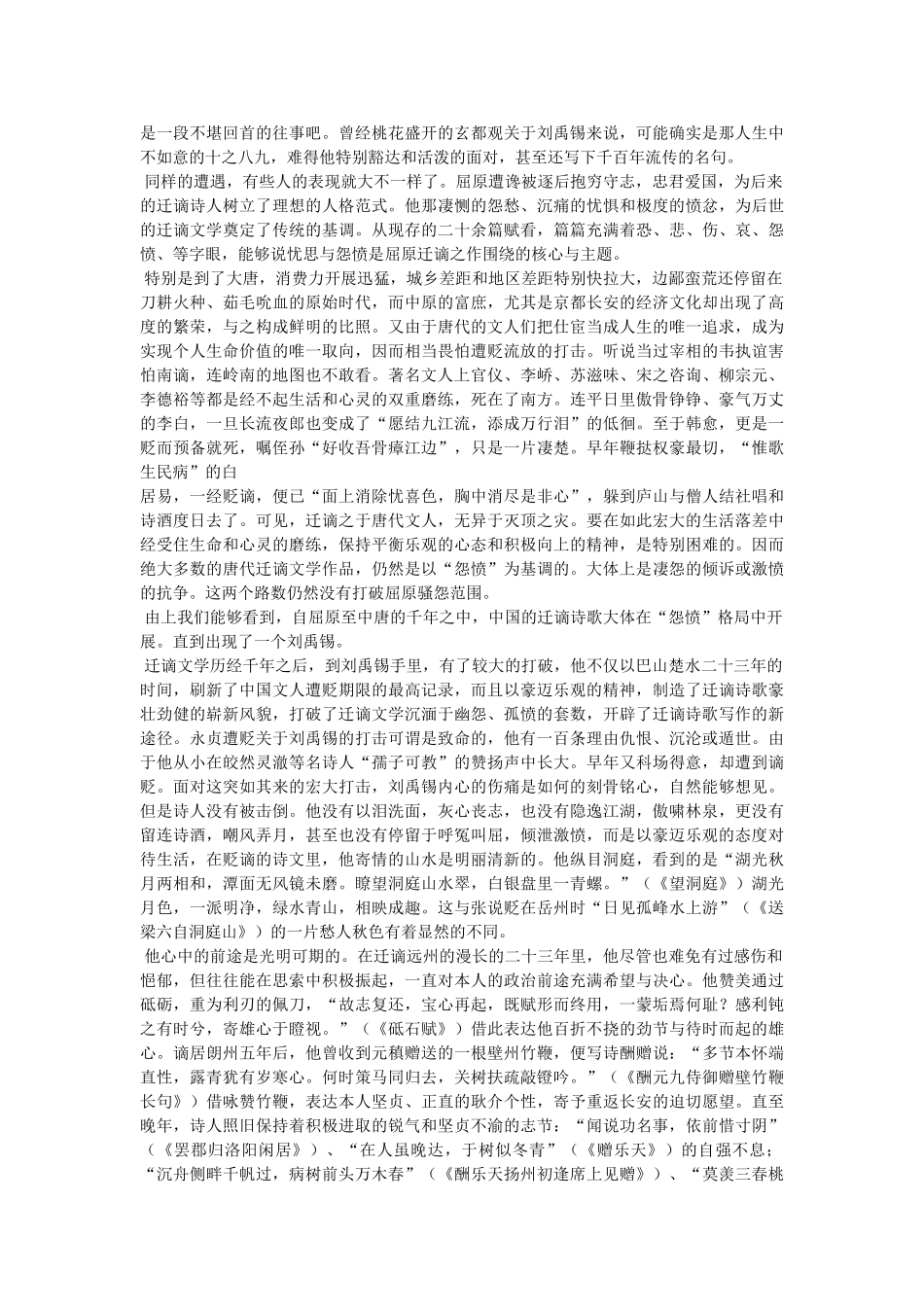“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意思篇一:刘禹锡——前度刘郎今又来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提到刘禹锡,我们就会立即背出他的《乌衣巷》;立即背出他的《竹枝词》;立即背出他的《陋室铭词》。而他也以那一首首隽永的歌,在大唐的天空里,留下了千年不朽的诗情,镌刻上千古流放的英名。刘禹锡,字梦得,号乐天,汉族,唐朝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其文章在中唐奇光异彩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可与韩愈、柳宗元媲。他的诗歌与自居易齐名,并称“刘白”;与柳宗元交好,人称“刘柳”。他的诗现存700余首,大致可分为讽喻诗、感遇诗、咏史诗和民歌体诗。刘禹锡的诗词有一种恢宏的气度,骨力豪劲,抒发了他虽屡遭贬谪,但仍傲岸不屈、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以及发奋自励的乐观精神,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想到刘禹锡,立即出如今脑海的确实是那首脍炙人口的《乌衣巷》,桥边的乌衣巷,野草野花映照着夕阳,燕子在一般百姓家里飞出飞近,这是人人都能看到眼前实景,说不上有什么新奇的,但第三句诗忽然一跌,运实入。睁开梦想的,看到了几百看到了几百年前显赫赫一时的王谢两大家话的云消雾散。事实上也是提示当时那些炙手可热的官不要得意忘形:历史无情,何必那么不可一世!是啊,当年疯狂地弹劾刘禹锡的那些官僚,都像枯叶一样凋落了。然而,“人间要好诗”,一千多年来刘禹锡的诗却永远滋养着后人的审美快感。想到刘禹锡,立即就会想到他别具风格的《竹枝词》,这青山碧水一样委婉流畅的诗歌,这巴蜀儿女的情思也被他细致描摹。人心的缺憾被他放大。那转眼即逝的情意,反复无常的人心,有情无情的扰,都在曲词之间了其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更是别出心裁的名句,“东边日出”是“有晴”,“西边雨”是“无晴”。天晴的“晴”与多情的“情”正好同音,由于借用这种双关隐语,使这首诗显得特别有情致。想到刘禹锡,就会想到与他的官场沉浮,有着亲密关系的桃花诗。那是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在那儿过了十年谪居生活后,在元和十年二月被召回长安。初回京师,游玄都观,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来表现了他的傲岸不屈:“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人用桃花比喻朝中新失权力的权贵,用看花人比喻那些趋炎附势、奔波权门之徒。于戏谑之中,暗藏讽意。一句“尽是刘郎去后栽”更是令他的政敌难以忍耐,句中之意特别明显:满朝中红极一时的权贵们,你们哪一个不是我刘禹锡被排斥后才爬上去的!此诗一传出,他立即得罪了权贵,执政者当即以“语涉讥讽”再贬刘禹锡等为远州刺史,实际是靠镇压永贞革新起家的宪宗不愿起用他们,刘禹锡以诗获罪,三月又远去连州假如说,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十年,初回京师,能写下如此富有战斗性的篇章是特别可贵的话,那么更为可贵的是,他因写《戏赠看花诸君子》被贬十四年后,重回京城,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锋芒不减当年:“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时的玄都观,已是无人游赏,那百亩庭院已半是青苔,往日那灿假设红霞的千树桃花已荡然无存,代替它的是缺乏以欣赏的菜花,那种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终,而上次因看花题诗被贬的刘禹锡却又重返长安,旧地重游!作者依然用桃花比新贵,用种桃道士比喻打击当时革新运动的当权者。这些人,通过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就连皇帝也由宪宗、穆宗、敬宗而文宗换了四个,如今有的只是“菜花”。刘禹锡作这首诗,是有意重提旧事,表示丝毫不为十四年前因诗得祸而悔恨,不会因屡遭贬谪而屈从,而为再题笔赋诗而欣喜,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傲骨。但是,这个“再游”又引起执政者的“不悦”。他又被派出长安,到东都洛阳做“太子来宾”这一闲散的官。但从游玄都观这两首诗来看,刘禹锡那么与众不同,时间上贯联诗人二十三年的被贬生活,可谓时间之长,但从诗中看出,他一直坚持本人的进步的政治思想,从未在逆境中向当权者屈从,同时不断以笔作为战斗的武器,显示了他百折不回、傲岸不屈的...